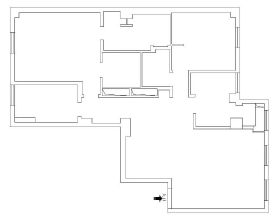北漂了二十多年,他還是一個人
轉載自人間theLivings
最後一次聯絡,四舅按照我母親說的,讓李英還錢。李英卻說,錢全花了,還不上了,也不會再來北京打工了,讓四舅忘了她。
配圖 |《暴裂無聲》劇照
月漸圓,近中秋,母親又在唸叨:“不知你四舅還能回來過節嗎?”
我知道,母親又在惦記四舅了。在每個閤家團圓的日子裡,母親為了不讓單身的四舅感到孤單,都會提前邀請他來家裡過節。每年我總要陪母親往返幾次北京,去看望四舅。
每次去北京看四舅,我心情都非常矛盾。一方面,我也惦記著四舅的狀況,另一方面,又擔心已經花甲的母親身體吃不消。每次回家後的那段日子,母親總是吃不好,睡不著,只反覆唸叨一件事:“你說你四舅,這輩子還能不能尋個媳婦?”
今年已經54歲的四舅一直沒有成家,按農村的說法,是打了半輩子光棍。姥姥去世後,他就孤身一人在北京打工,算來也有近20年了。他的終身大事,始終是母親的一塊心病,因為姥姥在臨終前曾給母親交代過,讓她無論如何“也要給四弟說上媳婦成個家”。
所以,一眾姐弟裡,母親最心疼、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四舅,也為他的婚事操碎了心。
1
母親說四舅是一個命大的人,也是個命苦的人。
1960年代的農村條件艱苦,姥姥和姥爺拉扯著七個孩子,忍飢挨餓是常事。四舅還不到兩歲時,在春天發起了高燒。那時在農村,幾乎沒有人會因為感冒發燒去看醫生(村子裡只有一個赤腳醫生),熬點薑湯,吃碗熱麵湯,再用被子捂一下,發發汗,也就挺過去了。
那次四舅燒了三天,體溫仍是沒退,還開始口吐白沫、抽搐起來了。姥爺見狀,趕緊跟鄰居借了幾毛錢,抱著他去了鄉衛生院——四舅前面曾有一個姐姐,在三歲時因為高燒夭折,姥爺怕四舅也挺不過這一關,不敢怠慢了。衛生院的醫生也沒有太多的辦法,只能給開了安乃近(1912年在德國上市的一種解熱鎮痛藥,我國於1950年後大量國產,曾是60到70年代醫生常用的一種退燒藥,因為副作用過大,已於2020年被禁用),姥姥把藥片壓成面面,就給四舅灌了下去。
醫生提醒姥姥說,孩子發燒這麼厲害,“怕不是什麼好病”,不要讓他傳染給其他孩子。回家後,姥姥就狠下心來,把四舅送進了柴房。
那時候村裡家家都是孩子成群,為了防止傳染病,幾乎每家都會把病孩子關到柴房裡單獨搭的小床上隔離起來。如果病孩子能吃東西,就喂幾口小米湯,如果不吃,就不再喂,等幾天後病孩子沒了鼻息,就把屍體埋到村裡的亂墳崗裡。村裡的風俗,未成年的孩子不能埋進祖墳,所以那片亂墳崗裡每年都要埋十幾個病孩子。母親和我絮叨起小時候的事時,曾說:“那時我就七八歲吧,常常看到野狗拖著那些病孩子的屍體亂啃,嚇得從不敢去那裡打豬草。”
灌了兩天藥,四舅的高燒總算退下來了,張著小嘴還到處找東西吃。母親感慨地說:“我尋思他都活不了呢,沒想到,他這麼命大!”
四舅頑強地活下來了,但好像因為吃藥留下了後遺症,長大後做什麼反應都比別人慢半拍,在家裡時常被三個哥哥呵斥。他鋤草時能比別人慢一壟地,揚麥子時又總會把太多的麥粒揚在地上。
轉眼到了80年代初,有一年夏天天氣酷熱,作為麥收主要勞動力的二舅和三舅都被換回家休息,留下了四舅和五舅在打麥場上看麥子。看著兩個哥哥不在,五舅轉身就溜到運河裡洗澡了,只剩下了實心眼的四舅還在那裡。沒過多久,天上突然烏雲密佈,眼看一場大雨就要傾盆而下,急得四舅連忙拿起鐵鍁去堆麥子。他心裡一急,手裡就亂了方向,等二舅他們趕到打麥場時,麥子被四舅堆得亂七八糟,氣得二舅把他臭罵了一頓,還踹了幾腳。
自那以後,四舅就有了想走出家門看看的念頭,他後來對我母親說,“如果一直在家幹農活,早晚會被哥哥們罵死”。
隔年春天縣武裝部招兵時,村裡照例動員男娃多的家長。姥姥有五個兒子,自然成為了重點的動員物件。當時大舅已經成家,二舅在學木匠手藝,五舅還小,只有滿了16週歲的三舅和四舅夠得上當兵的年齡。但姥姥並不想讓兩個兒子去——三舅幹得一手好莊稼活,是姥姥最得力的幫手,家裡和地裡都不能少了他;不想讓四舅去,純粹是因為他心眼不靈活,怕他在部隊受欺負——其實,四舅幹農活雖然慢,但幹別的事還是很利索,像洗洗涮涮、打掃衛生這樣的活計,他能幹得特別好。
四舅瞞著姥姥,在一個清晨偷偷地和村裡的夥伴們約好,一起去了鎮上報名體檢。他雖然只有小學文化,但身材高大,五官端正,濃眉大眼,身體素質很好,挑選的軍官一下子就看上了。
等他“驗兵”後回家,告訴姥姥姥爺他馬上要去入伍時,家裡人都嚇了一跳,誰都沒有想到這個平時不言不語的榆木疙瘩老四,竟然還會有自己的想法。
4年後(當時是四年制義務兵),四舅復員回家了,經過軍旅生活的磨鍊,他待人客氣、懂禮貌,講究衛生,做事也成熟了許多。
在四舅當兵期間,姥爺去世,家裡失去了頂樑柱,姥姥帶著還沒成家的四個子女,勒緊褲腰帶,省吃儉用地給二舅蓋房、結婚,幾乎把家底都掏空了。四舅從部隊回來後,又添了一張吃飯的嘴,土裡刨食的日子愈發艱難,我母親四處託人,最後為他在縣食品廠謀了份臨時工。
2
從我記事起,母親總在張羅著給四舅說媳婦。
1989年,四舅遇到了他的初戀女友王月。身材瘦小的王月和四舅是同事,是食品廠裡的正式工。
記得有一次我去四舅的宿舍玩,王月也在,正懶洋洋坐在床上,指使著四舅幹活。她一會兒讓四舅給她削蘋果,一會兒又讓四舅給她洗衣服,邊吃蘋果邊數落四舅,“上次你把我粉色的裙子都染成黑色了,這次你要賠我一件。”四舅笑呵呵地說,“放心,我再給你買一件粉色的。”
那時在我這個不到十歲的孩子眼裡,單眼皮、膚色黝黑、長得並不漂亮的王月就像個可惡的地主婆。四舅給我也遞過來一個蘋果:“丫頭,吃蘋果啊。”我氣呼呼地沒接,轉身跑出了他的宿舍,身後傳來他的喊聲:“別走,給你媽媽捎幾個蘋果!”
王月心安理得地享受著四舅的照顧,四舅也沒有任何怨言,甘之如飴地為她付出著。看著四舅這麼中意王月,我母親便託人到王月的家裡提親,沒想到卻遭到了王家的拒絕。母親覺得蹊蹺,便偷偷去打聽,才曉得原來王月腳踩兩隻船,她這邊和四舅談著戀愛,可眼看著四舅這個臨時工遲遲轉不了正,便又揹著四舅談了鄰縣一個工廠裡的正式工,最近已經跟那男人訂了婚。
實心眼的四舅被王月耍了。
為了讓四舅從初戀失敗的陰影中走出來,我母親以每月安排一次相親的頻率為他介紹女朋友,但因為各種原因,四舅卻再也沒有找到合適的物件。
1994年,母親託人在鄰村找了一戶人家,想讓四舅去當上門女婿。這戶人家只有一個女兒,條件不錯,結果,人家女孩沒有看上四舅,倒是相中了陪四舅一起去相親的五舅。五舅倒插門後,姥姥總覺得這件事實在對不起老實、孝順的四兒子,於是更加拼命地攢錢,想給四舅蓋間好房子,讓他儘快成家。
1997年我上了中學,寄宿。等到第一個暑假,回家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跟父母去姥姥家——要給四舅蓋的房子上房梁了,在我老家,這是和婚喪嫁娶一樣的大事。那天父親找來了一輛大卡車幫著拉木料,姥姥家來了二十多位親戚朋友捧場。大家議論最多的,就是姥姥這個寡婦老太太怎麼這麼能幹。
四十歲就守寡的姥姥,一生最大的心願就是為五個兒子每人蓋上一間新房子、娶上媳婦。我難以想象姥姥這個宏願實現的困難程度,只知道她幾十年省吃儉用,一分錢一分錢地攢,又欠下無數外債,榨乾了自己的每一滴血汗,終於把五個舅舅的新房全部蓋好了——除了四舅,幾個舅舅都各自娶了媳婦,有了自己的小家。
四舅當天也很高興,熱情地招呼著親戚朋友們。在噼裡啪啦的鞭炮聲中,姥姥花白的頭髮、佝僂的身體和笑盈盈的臉龐,成了四舅新房前最美麗的陪襯。我陪著姥姥在新房四周轉了一圈又一圈,她高興地指著那些磚和瓦對我說:“你看,等房子都蓋好了,你就要吃上四舅的喜糖了。”
當時,我們祖孫倆都固執地認為,蓋好了房子,四舅很快就能娶上媳婦了。
1999年的正月剛過,六十六歲的姥姥還沒有完成她給四兒子成家的心願,就離開了我們。
那天,田野還沒化凍,地裡也沒有活,姥姥就去鄰居家串門。她一邊給四舅做著布鞋,一邊跟鄰居大娘打聽著方圓的村子裡還有哪家姑娘沒有尋下婆家。鄰居大娘說,前村有一個姓姜的老姑娘,她可以替四舅上門說媒。姥姥哈哈大笑地說,“好,好”,然後身子突然往後一仰,摔倒在了地上。
姥姥是突發腦溢血,等三舅開著拖拉機把她送到鎮醫院時,人早已駕鶴西去,再搶救也沒用了。
姥姥去世後,四舅工作的縣食品廠也破產了,他找我母親商量以後的生活怎麼辦,母親便讓他來我家和我們一起生活——那時我們家已經搬進了縣城裡住,這樣平時四舅就可以去周圍的工廠打打零工。
但這個建議遭到了四舅的拒絕:“姐,孩子們還在上學,你們家也不富裕,我不能給你添麻煩。我想到外面闖一闖,農活我也不會幹,這麼大歲數還沒說上媳婦,不想再回村裡讓鄉親們天天笑話了。”
母親覺得四舅說得也有道理,姥姥不在了,四舅一個人回村裡生活,她也不放心。
於是,四舅回了趟村裡,先把姥姥住的老宅子鎖了,又把他自己的新房子也鎖了(新房子裡面還沒有安裝窗戶、屋門,也沒有裝修,只有一個大門),然後揹著一個蛇皮袋、捲了一套被褥,就和老鄉一起去北京打工了。
3
剛到北京時,四舅在一個老鄉開的醬菜廠裡工作。廠子在北京的遠郊區,開始母親還去廠子裡給四舅送東西,擔心他不能適應,“十幾個老爺們住在一個宿舍,東西擺得到處都是,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也不知道你四舅受得了嗎?他那麼愛乾淨”。
可四舅並沒有向我母親抱怨什麼,踏踏實實地工作,過春節也沒有回來。
第二年春天,我放學回家,開門卻撞見四舅正坐在客廳裡。聽他和母親聊天,才知道原來是工廠宿舍裡有人用“熱得快”,把電線線路燒了,然後整個宿舍都被火燒著了。當時四舅正好在車間上班,知道訊息後想衝進宿舍拿衣服和被褥,可已經來不及了——火勢太大,行李和日用品全被燒成了灰燼。
四舅這趟請假回家,是想讓我母親給他做幾床被褥。我見他的右手大拇指和中指的關節腫大,還微微泛著亮光,就問他怎麼回事。他說,這是長期切菜累的,冬天醬菜廠裡也沒有暖氣,蔬菜都凍成冰疙瘩,為了方便切菜,他有時會摘下橡皮手套,結果現在手指一碰涼水就腫,有時還疼。
母親從老家買來了最好的棉花,準備為四舅做四套新被褥。等著被褥做好的那幾天,四舅也沒有閒下來,他總是第一個起床,把我家裡的小院打掃乾淨,給需要上早自習的我做好早飯。每天放學回家,我總會發現四舅給我們的驚喜:他把蜂窩煤從大門挪到廚房的角落,又把小院前的一片菜地都翻了一遍,黑乎乎的廚房被他收拾得光潔明亮。
當時四舅已是三十多歲的大齡青年了。醬菜廠裡有熱心同事給他介紹物件,是一個離了婚後自己帶著孩子生活的女人,叫王麗,老家在東北。四舅和她談了半年多,王麗也覺得四舅老實、可靠,是一個值得託付的物件。
那一年年底,他們一起回到王麗的老家去見王麗的父母,可萬萬沒想到,王麗的父母竟然嫌棄四舅窮,跟女兒暴怒,還把四舅趕出了門。
從那以後,四舅再也沒有見過王麗。
四舅在醬菜廠幹了四年才離開。後面的十幾年,一直在一家貿易公司做送貨工,工作還算穩定:週一至週五白天上班,在繁華的大北京四處給超市送貨,將成箱的色拉油、醬油、各種調味料一件件地扛拉到倉庫;晚上下班後還要到出租屋附近的學校、超市門口去打爆米花,週六、日休息的時間,他就去收破爛。木訥的他靠著一雙勤勞的雙手,養活了自己,這點很讓我母親自豪。
母親也斷斷續續地又給四舅介紹過幾個物件,我記得有我父親老家的一個堂妹,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了兩個孩子。母親帶著這個堂姑子去了北京,和四舅見了一面,堂姑子提出讓四舅去她家門上過日子,四舅卻害怕到人家受氣,又擔心自己幹不好農活,無法養活人家的兩個孩子,便推脫了這番好意。
還說過一個四十歲的“王姑娘”,當時母親喜滋滋地把四舅的手機號親自送到王姑娘手上。誰知,這個王姑娘脾氣古怪,和不善言談的四舅完全找不到共同語言。於是,這門看上去年紀相當、門當戶對的親事也吹了。
4
2015年春節前,母親和四舅打電話時,聽他說找了個物件,已處了大半年時間。這下,母親在家裡再也坐不住了,第二天就命令我買車票,去北京看四舅,順便看看他的物件李英。
“快,給你四舅打電話,問問他今天晚上還去不去打爆米花?”那天到了北京郊區,剛邁進賓館的房間,母親就催促我。
臨近春節,四舅正忙著到處送貨。七點多天黑透了,外面下起了小雪,四舅來到了賓館。他比前一年春天見面時瘦了一些,凹陷的兩腮把眼睛襯托得更大了,身上那件黑色的羽絨服油膩膩地泛著白光,頭上還沾著些許沒來得及融化的雪花。他給母親拎來了一袋子蘋果,說是公司發的福利,讓我們嚐嚐。
“老四,以後下雪、下雨的,就別出門打爆米花了。別光顧著掙錢,身體做下病就晚了!”母親拉四舅坐在了賓館雪白的床上,四舅不停地在蹭自己沾滿泥巴的鞋,把地毯的一角抹得黑乎乎的,很惹眼。
“你們怎麼樣了?”
“李英說要跟我回老家訂婚。”四舅小聲地嘟囔著,“但是不能結婚,她找人算卦了,說結婚後會克我,非死即傷。”
聽四舅說,這個叫李英的女人,多年前丈夫車禍而亡,留下她和一個十九歲的兒子相依為命。她大了四舅五歲,在北京做保潔員,是經老鄉介紹認識的四舅。他倆同居已經半年,這段時間的吃穿用度,以及李英在老家的那個兒子的一切開銷,全是四舅一個人在負擔。
一聽女方遲遲不肯結婚,可把我母親急壞了,她給四舅下了最後通牒:“你和她攤牌,她要不同意結婚就分手;如果同意,就儘快把這婚事給辦了。”
四舅“嗯”了一聲,像想起來什麼似的,憨憨地笑著,從羽絨服內兜裡掏出了一張皺皺巴巴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穿著潔白的婚紗,濃妝豔抹的精緻妝容,也掩飾不住的她蒼老的年齡。
“怎麼樣?”四舅興致勃勃地問我。
“還行吧。”我含糊地回答了一句,不忍心讓他傷心。
我和母親心知肚明,這女人十有八九是在騙四舅。這麼長時間了,她不讓四舅跟她回老家見父母,更不肯訂婚,一直在找各種理由推脫著。
賓館的暖氣開得很足,母親叫四舅把羽絨服脫了。四舅拉開羽絨服拉鍊,指著裡面穿的大紅的保暖內衣說:“這是她買的。”那語氣像是找到了什麼值得誇耀的東西,讓我母親寬心。
我一時竟有些理解四舅了——偌大的北京,十幾年的孤苦無依,終於有一個女人願意關心他,知冷知熱地疼他,縱然是騙,他大概也是心甘情願的。
隔天晚上,我和母親去了四舅和李英的住處。母親的本意是想看看李英,親自盯問一下她是不是想真心和自己弟弟過日子。但是我們那晚並沒有如願,因為春節前正是保潔員們最忙的時候。
在四舅的帶領下,我們來到了他在六環外的出租房。那是一棟郊區農民的自建樓,樓右側的空地還有工人正在蓋樓,建築垃圾和生活垃圾隨意地堆在樓前。穿過一條四五米寬的過道,映入眼簾的首先是一個藍色車棚,裡面雜亂地堆放著許多三輪車、摩托車和電動車。昏暗的燈光下,車棚的最外側停著一輛鏽跡斑斑的三輪車,上面放著一個小型煤氣爐和一個爆米花用的小鍋。
“姐,這就是我花三百元錢買的三輪車。”
看著這輛三輪車,母親擔心地勸四舅:“你出門時小心點,北京車多人多,不要讓人撞了。”
“沒事兒,我騎習慣了,打爆米花騎它,收破爛也是騎它。”四舅安慰母親。
我和母親進到了四舅的住處看了看,五層的自建樓,一個一個房間出租,左右兩側分別有兩個衛生間。四舅和李英租的是一樓的房間,裡面放了兩張高低床,下面住人,上面放了一些雜物。一張藍色的布簾分隔出了臥室和廚房,“臥室”裡還有一臺電腦。
“四舅,你什麼時候學會電腦了?”我問。
“這是個二手電腦。”四舅不好意思地笑笑,“我只會QQ聊天什麼的,李英也有時和孩子聊聊天。”
一個煤氣灶佔據了“廚房”的大半空間,菜板、鍋碗瓢盆擺得錯落有致。看到廚房收拾得乾淨整潔,母親高興地說,“這才像個過日子的樣子”。
一番探視下來,母親似乎改變了判斷,在心裡認定李英應該是想和四舅好好過日子的。臨走前,她又摸了摸四舅的被子,發現有些薄,就說要給四舅和李英再做兩床家鄉的棉被寄過來。
那時,四舅每月工資兩千多元,每天出門打爆米花也能掙下幾十元,再加上週六日到處收廢紙賣,一個月大概能賺四千多元。有一個知冷知熱的女人疼他,兩人一起幹活、吃飯、攢錢,四舅的日子雖辛苦,但是有奔頭。
一眨眼到了2018年,李英對四舅說,兒子長大了,要她回老家張羅著娶媳婦。臨走前,她向四舅借錢,四舅沒有猶豫,給她取來了自己全部的五萬元積蓄。李英回到老家後,一開始還跟四舅有聯絡,說那些錢都給兒子說媳婦用了,沒法還他,後來又說讓四舅好好工作,等她回北京就結婚。
可說歸說,半年過去了,李英遲遲沒有回來的意思。最後一次聯絡,四舅按照我母親說的,讓李英還錢。李英卻說,錢全花了,還不上了,也不會再來北京打工了,讓四舅忘了她。
後來我母親氣得在電話裡不停地罵四舅:“老四啊老四,咱在女人身上吃的虧還少嗎?再也不許給女人花錢了,自己歲數也不小了,給自己留點養老錢吧!”
四舅沒有去李英的家鄉討要借債,只是更賣力地工作,下班後,還去附近打爆米花,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有時晚上十點半,我母親給他打電話,他說還在外面打爆米花沒有回家。
5
禍不單行,2019年,四舅在一次公司組織的體檢中查出了甲狀腺瘤。
這十幾年,他一直在這家貿易公司工作,每次見我和母親,從不對我們喊苦喊累。他說的更多的是公司待遇好,很照顧他,還給他這個十年多的老員工簽訂了合同,繳納了醫保和社保,每年還組織他們去附近的景點旅遊。有時,我帶著孩子陪同母親去看他,他還會拿出準備好的兩百或三百元錢,非要塞給我,說給孩子買零食。
體檢時查出了這個病後,貿易公司給我母親打來電話,說要家裡人陪他檢查、做手術。此時大舅也已去世,剩下的幾個舅舅都是當了爺爺的人,平時要照顧孫子孫女,和四舅聯絡很少。只有母親還時常記掛四舅,堅持每年到北京看他。如今,六十多歲的母親和父親,只好再一次來到北京。
父親找到公司的工會主席、經理,把四舅的情況和他們說了一下。好在公司的領導們都很同情四舅,保證在他手術後公司還會和他籤合同,並把他調到工作更輕鬆的倉庫工作。
四舅在檢查時,我父母一直陪著他。在他手術前,父親把老家的二舅、三舅和小舅全部叫到了北京,他害怕四舅有個三長兩短,他承擔不起這個責任。
四舅挨個問了侄子侄女們的情況,又特意問了問姥姥給他置下的那棟房子。在老家的三舅說,房子院牆早已坍塌,大門也被鄉親們當作廢品收走了,房頂的磚瓦都沒有了,成了露天的房框子。
“算了,等退休後再收拾吧。”四舅並沒有表現得特別傷心。
我知道,他本來希望退休後,能有個老伴一起和他搬進農村的老宅子裡養老。
活檢結果顯示四舅的甲狀腺瘤是良性,沒有癌變。只是需要定期檢查、按時吃藥。好在公司給他入了醫保,醫藥費都能報銷。
休息半年後,四舅又回到了貿易公司上班。領導們兌現了承諾,把他分配到了倉庫,他的新工作就是清點貨物,貼貼標籤,輕鬆多了。
尾聲
“有了醫保和社保,你四舅養老不成問題了。”母親和四舅通完電話,又和我念叨,“只是不知道,這輩子他還能不能說上個老伴。”
這時,我的手機顯示,四舅在微信轉來了一千元,還發來一段語音:“給你媽買點東西過節吧!”
我眼裡一熱,不想去接母親的話頭,也沒有去收四舅的紅包。我望著被各種燈光襯托下並不明亮的月亮,想起了十歲時,四舅追在我身後喊:“丫頭別跑,給你媽媽捎幾個蘋果!”
中秋節後,我一定再陪母親去北京看他。
(文中人名均為化名)
編輯 | 許智博 運營 | 嘉宇 實習 | 雅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