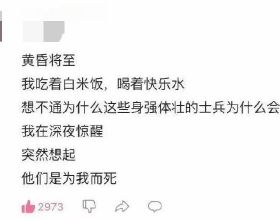已經老了,回想一生,只是後悔娶了一個比男還要男人的老婆。
這件事還得從二十多歲說起。俺姓韓,就叫韓三,也沒有什麼“國棟”呀、“國富”呀的高貴的大名。那時候家家都窮,俺家更窮,老爹在俺小的時候就抱病而亡,那個時候俺還什麼也不懂,看到殯葬儀式還小有些興奮。老爹一死,就剩下了俺娘和俺哥弟幾個了。大哥成家已另立門戶,二哥天生的就是個瘸子,找媳婦已經是無望了,甚至一年半頭的還要看病吃藥,更是沒有女人會嫁給他,誰也不傻。俺娘夏天參加生產隊勞動,收工了還不忘採收一大筐野菜,主要用來餵豬,晚飯中也可以細作一番人吃。那個時候大多數人都是吃不飽的,各家想各家的辦法。特別是俺家,沒有閨女,就是三個愣頭兒子,愣小子費飯,又就俺娘一個人勞動,生活更是出奇的緊巴,也是全村出名的窮戶,在大人小孩面前俺們都低人一頭,窮就是這樣子的。所以俺娘在俺唸書到四年級的時候也就撒手而去了。俺如今還能清楚的記得俺娘每年冬天在冰冷的屋內給們做針線活的動作:在煤油燈下,一針一針的縫,鼻尖處掛著一小點晶瑩的鼻涕,還時不時地吸幾下,似乎是怕那滴鼻液掉下來。久了,還拿針在頭上劃幾下,大概是為了讓針更鋒利一些吧,大概是認為在頭上磨幾下就鋒利了,俺至今也弄不明白。
俺娘去逝後俺就不念書了,那時候俺也不知道俺是幾歲,反正也加入了生產隊的勞動大軍,光榮地成為了一名勞動者。幾年後俺就長成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大小夥子,也就成了勞動主力隊員,而且在同齡人群中,也可以說是在全村也是出了名的大力士,沒有人敢不相信。不過力大也不是什麼好事,力大同時肚子也大,一個人一頓能吃人家二個人的飯,為此更是捱餓了,這麼能吃,姑娘們也不敢嫁你,很快就成了一個小光棍。那時候的農村人,二十三四沒有媳婦,估計就很不好娶女人了,再堅持幾年沒有戲,那就只有偷女人過日子了。男人光棍久了總得嚐嚐女人吧,不然豈不是白來人間一趟?更何況下面那個傢伙也不好管,就想偷葷。
俺自己也明白俺百分之九十九是光棍了,那家姑娘會嫁你?家窮,又能吃,連個娘也沒有,憑那一個優點嫁你?就憑力大?那是不可能的,力大也不能多掙回一口飯。那個年代的政策是按人頭分糧食的,不憑多幹活少幹活,“夠不夠三百六,吃的沒了再研究”,不論大人小孩,每年都是三百六十斤糧食,所以力大肚大並不是什麼優點。為此俺還進駐了“學習班”,這個學習班可不是讓你讀書識字的,說到底就是個“勞教所”,白天干活晚上學習政策改造你的思想。學習政策就是有人給你念報紙,完了喊一些號口就結束開飯。
進“學習班”的原因是因為俺偷了一棵大樹。怪就怪俺認識縣城裡的一個“不良之徒”,是俺孃的一個遠房親戚,他家想蓋房子,苦於買不到木枓就想到讓俺偷再花錢買俺的,俺也想掙幾個錢花,俺的村外就有很大的樹林子。也是運氣不好,就偷了一根大樹,還埋在了俺家的院子後面,第二天上午就被發現了,被叫到了大隊,還審問俺有幾個同夥。俺說就俺自己一人,大隊幹部還不相信,直待俺把贓樹給他們抗到大隊部院裡他們才信了俺,接著把俺送到了“學習班”。
就因為進了這個“學習班”才讓俺後悔了一輩子,因為在這個“學習班”俺娶到了媳婦,不漂亮。開始進“學習班”的時候根本沒想到會長久呆在“學習班”裡,因為按規定俺會在“學習班”裡改造十五天,可是因為俺力大,勞動積極肯幹很受領導的歡迎,幹了還不到十天,領導就和俺談話,讓俺長期留在學習班裡,俺說不自由,他說自由,還保證讓俺吃飽,平時幹活幹多幹少由俺,就是裝車卸糧等大力氣活俺必須積極肯幹就行,所以俺留下來了,前一段時間也很爽,那些被改造的也會稱俺領導,可是沒有多久,領導又把俺叫去了,告訴俺說有人對俺的這種活提出了反對意見,需要給俺加活。俺問還要讓俺幹什麼活,領導說:你晚上就再“下下夜”吧,也不累。“下夜”就是黑夜在田裡巡邏,防止外人偷竊莊稼,所以俺又需黑夜“下夜”了,這點事對俺來說根本就無所謂,不就是黑夜裡在田園裡走走,也沒有什麼,有好事也說不定,聽說周圍村裡的人就來這裡小偷小摸,事不大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過去了。俺心想要是有個娘們來偷就好啦,可能可以交易一番。力大精力也旺,二十幾歲的棒子誰不想發洩一下過頭的火?
可是就因為這個想法,也心急,留下了千古遺恨,娶了個醜媳婦,醜就醜吧,俺也不咋地帥,只是媳婦太男人讓俺受不了,如今六十多歲了還不著家。
那是一天夜裡,玉米地裡響起了“叭叭叭”響聲,夜靜聲音特別的大,俺偷偷的繞過去就抓住了一個女人,夜裡也看不清模樣,也不知道多大歲數。她害怕了,就求俺放過她。俺說:“不行”,她說:她夜裡睡的餓了就偷幾個玉米棒子回去吃,讓俺行行好,俺還是不行,最後她只得說:只要能放過她,什麼條件都答應俺,俺說要睡她,她說行,俺就睡了她。
這一睡不打緊,完了。第二天她就找到俺非說讓俺娶她當媳婦。夜裡沒看清楚她長什麼樣子,白天這一看一切完了,個頭還行象個女人,面板紫黑也就不說了,全身的肉卻象塊鐵,看上去就硬,那裡有一頂點兒女人該有的溫柔,俺認為那個女人都比她強。俺說:“不行”,她說:“你睡了俺就得娶俺,不然俺告你強姦”。俺說:“那是買賣交易”,她說:“不公平。俺最多改造五天,你犯強姦罪至少二年”。俺怕判刑無奈娶了她,也沒有舉辦婚禮,她只接拎了個小包住進俺家,結婚證還是大隊支部書記逼著俺們去公社辦的。她給俺生了三個娃,兩個兒子一個女兒,相貌都可以,都不隨她。
改革開放後她辦起了個包工隊,包攬工程建築,也掙了不少錢,直到現在還是個包工頭。有人說她玩小白臉,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是很少回家。俺也問過她,她說沒玩過小白臉,還說她就得俺來配,嫁給俺也是看準了這一點。
她反正是一年四季不著家,俺一個大老爺們反倒是洗鍋涮碗一輩子,俺真不甘心,她又長的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