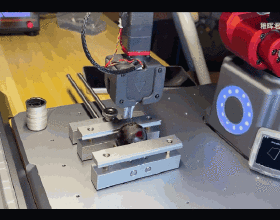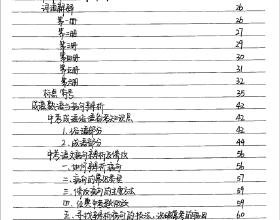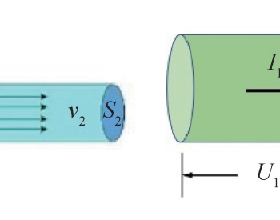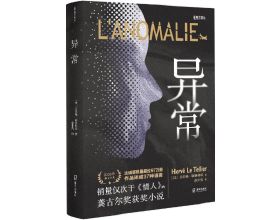機器與有機體之間存在一種深刻的相似性,它們都是由一些功能各異的部分構成的整體,都有自身的生命週期,都會不可避免地走向功能失常和組織解體。因此,一部分哲學家(如笛卡爾和維納)主張透過機器來理解有機體,形成了有機體的機器概念;另一些哲學家(如康吉萊姆和西蒙棟)則傾向於透過有機體來理解機器,發展出了機器的有機體概念。然而,當他們以不同方式將機器等同於有機體時,卻違背了我們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常識:機器與有機體之間存在差異性。因為機器的行動目的是人類設定的,而有機體的行動目的是內稟的,所以有機體具有真正的能動性,而機器只能聽從人類的意志和命令。如此一來,從上述兩種概念出發來思考機器(和有機體)的能動性,將會得出一些超出常識的結論。它們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在機器力量彷彿具有了自主性的時代裡,人類究竟應該如何與機器共存。
有機體的機器概念
笛卡爾是有機體的機器概念的始作俑者。他把心靈規定為不佔據任何物理空間的實體,並讓其從物質世界中撤出,包括身體在內的一切有機體,都成了由各種器官構成的機器,遵循著因果定律而運轉。心靈和機器因此是兩種不同的實體。在《談談方法》中,笛卡爾設想,即便一臺機器外形彷彿人類身體,甚至可以模仿人類的動作,我們也可以分辨二者。首先,人類可以靈活地使用語言,但機器只能按照設定的規則說出某些詞語;其次,人類具有通用的智慧,機器即便在某些專門功能上做得比人更好,卻無法像人類一樣可以做其他事情。人之所以具有這些獨特的能力,正在於他的理性靈魂;而機器由於欠缺理性靈魂,無法做出基於思考和推理的行動,“它們的活動所依靠的並不是認識,而只是它們的部件結構”。笛卡爾的這一設想,標誌著有機體自然觀的徹底敗北,但也意味著人本主義的發揚光大。他一方面把有機體(包括動物和身體)貶斥為機器,另一方面又賦予人類無上的優越性。人的尊嚴就在於他的心靈,心靈具有能動性;世界成為一部機器,機器遵循因果性。
機器的時代就是控制論的時代,笛卡爾之後有機體的機器概念被繼續推進,人類優越性的本體論主張卻被拋棄了。1943年,諾伯特·維納與其他控制論者合作發表了著名論文《行為、目的與目的論》。他們強化了有機體的機器概念:“動物與機器中廣泛的行為都是相似的。”他們也顛覆了人類優越性的主張:人具有的目的論行為就是負反饋機制,動物和機器同樣具有。於是,靈魂的理效能力不再為人類獨有,足夠複雜的控制論機器一樣可以掌握。在人工智慧興起的前夜,維納暢想:“隨著關於膠體和蛋白質知識的增長,未來的工程師可能會嘗試設計這樣一種機器人,它不僅在行為上,而且在結構上都類似於哺乳動物。”維納信心滿滿,在他看來智慧機器或賽博格的能動性,與有機體的能動性並無不同。這預示了不久之後圖靈在《計算機器與智慧》中對人本主義者的嘲諷:與智慧機器相比,人類並無任何先天優越性。隨著人工智慧在棋牌遊戲上戰勝人類,我們似乎不再懷疑,機器將會插上能動性的翅膀,把人類遠遠甩在身後。
然而,無論維納如何把有機體視同機器,如何抹去人類的先天優越性,他仍是一個老派的人本主義者。在控制論開始大規模應用於社會控制和軍事的時代裡,他憂心忡忡地談論著機器對人類自由和個人權利的碾壓。這種擔憂正是人本主義者的技術恐懼症的一個變體。正如蘭登·溫納所指出的,機器的巨大力量引發了人們對技術失控的擔憂,機器開始被“描繪成幾乎有生命的某種事物”,它“具備了生命特性——意識、意志和自發運動,這些特性使它與人類社會相對抗”。這種技術有靈論往往伴隨著一種頑固的人本主義,機器力量被視為人類力量的異化。我們所創造的機器的力量越是強大,我們自身就越是貧瘠和乾癟。人本主義的理想是讓人成為機器和自然的主人,但在現實面前,機器卻獲得了一種主人式的權力,人反倒失去了一切自主性。機器不再是一種純粹的工具,人類被這一異己的力量置擺、促逼。
機器的有機體概念
正是基於對機器力量的深刻感受,機器的有機體概念悄然興起,而有機體的機器概念則受到廣泛質疑。笛卡爾和維納試圖從生物學中排除目的論,但法國科學哲學家康吉萊姆針鋒相對地指出,這不過是一種錯誤的幻覺。康吉萊姆詳細解讀了笛卡爾的文字,發現他根本無法完全排除目的論,因為機械論僅能解釋已經存在的機器如何運作,卻無法解釋機器是如何被建造的。實際上,只有理解了機器的功能和目的,才能進入機器的形式與結構。如果承認了機器的目的論,就有必要用有機體的模式來理解機器。康吉萊姆引述了人類學家勒魯瓦-古蘭的觀點:技術作為有機化的物質,有著自身的演化歷史。機器就像有機體一樣,有對環境選擇的適應,有自身的目的論。我們不應該如控制論那樣把生物視為一種機械現象,而應該把機器視為一種生物現象。如此一來,機器也和動物一樣,具有某種程度的能動性。
然而,機器的能動性並非一種神秘的、難以言說的力量。勒魯瓦-古蘭用技術與人類的互補性來解釋技術的演化動力。技術演化是一個從內在環境出發,逐漸攫取外在環境的過程。內在環境就是技術所關聯的族群所共享的文化,外在環境就是一個族群的物質環境和異族文化。正是內在環境賦予了技術以意向性,並在與外部環境的碰撞中不斷地將其轉化為內部環境。與作為人類學家的勒魯瓦-古蘭不同,作為技術哲學家的西蒙棟在《論技術客體的存在方式》(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中試圖論證,技術客體憑藉著一種獨立的邏輯而不斷演化,人類文化並非技術客體的意向性根源;相反,人類僅僅是技術意向性的執行者。在西蒙棟那裡,機器具有了更強大、更獨立的能動性。
西蒙棟用個體化(individuation)或具體化(concretization)來概念化技術客體的演化過程,它呈現為一個從抽象到具體的個體發生過程。最原始的技術個體是抽象的,本質上是科學概念和原理的物質轉譯。它的每個部件都有自己獨特的和明確的功能,為了實現某種目的而機械地聚集在一起。充分演化後的機器是具體的,它更接近於生物個體的自然系統。此時,技術個體包含的技術元素之間的內部共振(internal resonance)增強了,一個技術元素往往具有多重功能,同一個功能也可以分別由幾個協同關聯的技術元素來實現。西蒙棟特別以發動機的歷史來佐證這個觀點。他認為,老式的發動機是抽象的,而當代的發動機是具體的。因為老式發動機的每個要素都有獨立的功能,它們在熱力學迴圈的某個時刻介入之後,就不再對其他元素產生作用。相反,現代發動機的各種元素之間相互影響,活塞、汽缸蓋、火花塞的各種特性與發動機的熱力迴圈之間,彼此像有機體的器官一樣相互關聯在一起。因此,技術的演化就是一個從抽象到具體的具體化過程,同時也是機器不斷個體化的過程。
西蒙棟特別思考了具體化過程中技術與環境的關係。在他看來,技術個體就像生物系統那樣具有自己的關聯環境(associated milieu)。在具體化的過程中,技術個體日益把其他自然事物和技術客體作為自我維持的條件,而不再完全依賴於人工介入和人工環境。在這個過程中,各種技術客體留下的複雜的世系,展現了一個充滿了成功與失敗的演化過程。演化成功的技術客體總是比它的祖先實現了更好的功能和結構整合,它的技術功能得到進一步完善,從而變得更加具體化和更少抽象化。因此,具體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技術個體適應、吸收和改變環境的過程。
如何與機器共存
在勾勒從有機體的機器概念到機器的有機體概念的思想史轉變軌跡之後,我們也許可以藉此機會重新反思機器能動性對人類自由的威脅。有機體的機器概念總是非常矛盾地與人本主義價值觀聯絡在一起。笛卡爾和維納在把有機體還原為機器的同時,卻又把人類價值置於一個崇高的位置。他們都持有這樣一種人本主義信念:將機器與人類對峙起來,讓人成為機器的主人,而不是被機器奴役。維納不無擔憂地指出,機械化的發展將會讓整個世界成為一部超人般的機器,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危險。為了給個人權利和自由留下空間,就必須限制機器在社會中的應用。
與之相反,機器的有機體概念則預示了一種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價值觀:機器總是與人類協同演化,人類的解放同時也是機器的解放。西蒙棟沒有全然反對人本主義,但他激烈批判了一種膚淺的人本主義。後者一方面將技術客體視為無意義的物質裝置(如笛卡爾),另一方面又將機器視為具有敵對意圖的事物(如維納)。這是因為它把文化與技術對立起來了,然而技術恰恰構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要更新人本主義,就必須把技術性帶入文化之中,從而重新思考人類的異化境況。在西蒙棟看來,異化的根源是機器的使用和建造的分離,勞動者成為機器的消極的操作者,而不再積極參與機器的建造、發明和重構。這意味著,透過參與機器的設計,把人類和生態需求整合到機器的具體化過程之中,將會克服機器與人類的異化。因此,問題的關鍵就不在於限制機器的應用,而是重新設計並加速機器的應用。
(本文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專案“延展心靈中的物質能動性問題研究”(GD16XZX0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分析哲學國際研究中心)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夏永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