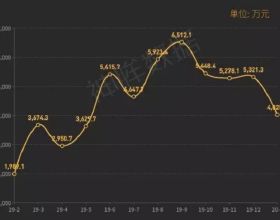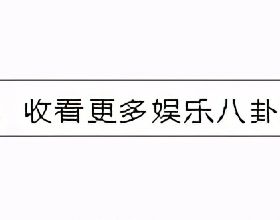我還是碎娃的時候,特別喜歡去舅舅家。他們隊上的養豬場院子裡有個大水塘,水裡漂著一種叫“水葫蘆”的草,夏天就會結出像兩個蘋果蛋蛋連在一起的葫蘆,切開后里面呈海綿狀。舅舅說,這種水葫蘆不但豬愛吃,而且長膘還快。每次去舅舅家,我們最開心的就是和舅舅家的兒子,還有她們的鄰居玉芳,一道去豬場院子參觀水葫蘆、藏貓貓、搖落樹上的桃子撿來吃。
舅舅家離我們僅隔一條千高公路,大約一公里多,叫著柳家塬大隊。大隊部就設在舅舅家所在的二隊,從大隊部圍牆上的小門出去,正好是二隊的打麥場。農閒時,這裡就會搭起一個大戲臺,舅舅帶著我在這個戲臺上看了《沙家浜》、《紅燈記》和《智取威虎山》。我經常在同學們面前模仿劇中的英雄。我們班有個叫王慧琴的女同學,他爸爸是業餘秦腔板胡愛好者。她在一年級的時候,就會唱“打不盡豺狼絕不下戰場”、“八年前”等唱段,而且唱得有滋有味。老師和同學們很羨慕,就經常以各種理由,讓王慧琴同學給我們演唱。
附近幾個大隊,哪裡有戲看,哪裡就有我舅舅。在他的耳濡目染下,我也成了戲迷。經常在附近的戲場找我舅舅,讓他給我講解自己看不懂的戲。我妗子說,只要找到戲場,就能找到我舅舅。
那時,每個生產大隊都有文藝宣傳隊,報幕的是大城市裡來的插隊知青。他們一上臺就會用播音員一樣的口音說“某某大隊文藝宣傳隊,XX演出現在開始。第一個節目秦腔《XXX》……或者眉戶《XXXX》……”從演員的演出中,我慢慢知道了樣板戲和移植的《洪湖赤衛隊》屬於秦腔;《梁秋燕》、《十二把鐮刀》等屬於眉戶,秦腔悲傷、眉戶熱鬧的特性。
我快十二歲時的秋天,聽說陝棉十二廠業餘劇團,來我舅舅他們隊的打麥場上演出。
我喜出望外的走進劇場。
劇場裡的氣氛和以前大相徑庭。首先,人數比以前多數倍,其次是一圈賣各種小吃和玩具、圖書、報紙、期刊、雜誌、小人書、農具……的小商販把觀眾團團圍在中央。而且,我在人群稀疏的地方還發現了一家照相的地攤。
人群潮水般湧流著,我真有點矮人觀場,看不見戲臺上演的是什麼。如果我舅舅在就好了,我邊想邊圍著打麥場找了一圈,仍然不見我舅舅的蹤影。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時候,看見舞臺右側,有幾個小孩爬上了一個馬頭形狀的麥草垛。那裡地勢高,可以斜視戲臺。
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爬上了麥草垛。這才看到戲臺上的桌子後面,有一個長著很長鬍子的半老漢,旁邊站著兩個像門神一樣的花臉壯漢,腰間挎著鬼頭刀。舞臺左側的椅子上綁著一個長辮子小夥;桌前右側坐著一個手扶龍頭柺杖的白髮老太婆。長鬍子半老漢對白頭髮老太婆又是搭弓又是作揖,一會笑一會兒哭。他們穿著古裡古氣的衣服,好像是在爭吵什麼,我真的看不明白。
就在這時,衝上來一個維持會場的知青,抱起我像滾木頭一樣,把我從麥草垛上滾了下去,正好滾到了一個人的腳前。我被那人一把拉了起來,我定睛一看,驚喜地叫了一聲“舅舅!”
舅舅領我去了他家。在妗子給我擀麵的當口,舅舅給我解釋說,今天唱的這戲叫“老戲”,有十一、二年不讓演了,現在又恢復了。他們小時候看得多,也很熟悉。今天這齣戲叫著《轅門斬子》。接著,舅舅給我講述了這個劇中的故事。他還說,做生意的人多,那是自由市場和老戲一塊被禁止了,今天又一塊開放了,現在做生意不犯法了。
經舅舅這麼一說,我突然想起我家炕桌最邊上的抽屜,我爹從來都不讓我動。有幾次我趁他不在,好奇地開啟後,裡面藏著一本書。封面上有兩個穿古裝的長鬍子老漢,好像下面還寫著“馬健翎”三個字。現在想來,那是我爹在六十年代收藏的陝西省戲曲研究院第一任院長——馬健翎先生所作的一個秦腔劇本。
從那以後我才知道,我們千陽縣把演戲叫著:“唱戲”;把看戲叫著“跟會”;把第一夜首場演出的開羅戲叫著“掛燈”;舞臺劇叫“大戲”;皮影戲叫“小戲”。通常,大戲和木偶戲一次演出三天四夜或者兩天三夜。首場演出都是選在晚上開始,所以叫掛燈。每天早飯後大約十點半白天戲開羅,都演全本戲。晌午過後四點半開始演下午戲,大多是摺子戲二到三折。夜戲七、八點鐘開場,也是全本戲。每天三場演出,觀眾都是滿滿登登的。最後一場戲結束的時間也必須是晚上。唱戲的季節大都選擇在農閒和節日期間。
那時秦腔發展的飛快,不到兩年,各公社都組建起了自己的業餘秦腔劇團,公開招考演員,重金聘請教練、導演、拉板胡的琴師和各種文武場面樂器的演奏者。
很快,皮影戲又走進了秦腔市場,它的演出程式在我們千陽縣是有別於大戲的。
皮影戲一般演出二到三個晚上。首場演出選在晌午後,七、八個人的演出組圍圈而坐,開始清唱,我們千陽縣叫著“自樂班”。他們不管是敲邊鼓、拍扇子、敲大羅、砸咣咣、敲小鑼的還是拉板胡、二胡、吹笛子的,都是邊操作樂器邊清唱,生旦淨醜末無不精通,頗有傳統秦腔的韻味。和皮影配合演出,需要燈光的照耀,因此選在晚間進行。
我在短期內,對秦腔有這麼深的認知,全靠我舅舅和父母親的啟迪。
八十年代是萬物復甦的時代,秦腔更像雨後的春筍蓬蓬勃勃。這時,陝西人民廣播電臺、陝西電視臺相繼推出了各地名家演唱的經典劇。方圓十里,僅文家坡公社和我舅舅他們大隊有一臺十八英寸的黑白電視機,每逢播出秦腔戲的晚上,觀眾把廣播室圍得水洩不通。但還是滿足不了村民們的慾望,多數人就選擇在十四點半,陝西人民廣播電臺對農村廣播結束後,聽高音喇叭裡的陝西地方戲曲節目。他們多麼想買一臺半導體收音機,收聽秦腔戲和農業科技、新聞和小說連播啊。
當時,千陽人看戲、說戲、學戲、唱戲就像當今的人們拍抖音一樣,誰都能來兩句,而且像模像樣。
我出於對秦腔的摯愛,把家裡的舊鞋和豬毛收拾了一荊條籃子,提到張家塬收購站去賣掉,買了一本馬健翎著的《遊西湖》劇本,封面是馬蘭漁在殺生一折裡的劇照。時隔不久,又撿了一些破爛換回幾個“銅板”,用它買了一本《白蛇傳》劇本,封面上,馬友仙和胡波的斷橋劇照栩栩如生。
被禁止的電影《三滴血》和《火焰駒》重映時,又一次引起了觀眾更大的轟動。
一個娃娃能看懂傳統秦腔劇,完全是來自長輩人的引導。
我爹一生喜歡看古書和戲曲,他早年把秦腔和古書中的故事講給我娘,我娘又講給我們聽。比如像《別窯》,我八十年代看過好多次,這幾年又在網際網路看了很多不同名家演出的版本。也經常習唱“窯門外栓戰馬將心疼爛……”這個段子。但前幾天我突然想起,八十年代我娘曾經告訴我,《別窯》裡薛平貴聽見魏虎點將時,紅鬃烈馬在窯門外一聲長嘶。薛平貴為了不耽誤了軍機,以防魏虎藉口斬他,就翻身上馬。這時三姑娘追出窯門,拽著丈夫的戰袍依依不捨,薛平貴拔劍割斷戰袍,才得以脫身,這一別就是十八年的情節。我昨天仔細對比了幾位名家演出的《別窯》,確實是有這麼一個我幾十年都沒有注意到的細節。
一九八三年九月,寶雞市秦腔劇團來文家坡鄉公演。那時我們家承包的幾十畝山地,正處於緊張的秋耕、秋播中。我爹和我娘執意讓我放下繁重的農活,往返三十里路,觀看了由崔慧芳主演的《遊西湖》,拓寬了我的秦腔視野。
一九八四年十月,我告別了舅舅和父母應徵入伍,在新疆阿克蘇某部服役。從此,秦腔和我宛如秦嶺和天山,雖天各一方,卻又一脈相連。
八八年二月份,我返鄉探親,在烏魯木齊火車站每遇到一位陝西鄉黨,就迫不及待地談論起秦腔。這時候,我彷彿已經聞到了我娘擀的臊子面味道,還有關中田野裡麥苗的馨香氣息。
在新疆生活的十五年中,我每每想起秦腔,就會想起父母親和舅舅。在我的心目中,秦腔和我的親人完全是一個整體。
或許是造化弄人,一九九九年,我終於在漢中成家,我媳婦是本地人。由於語言的差別,她不喜歡秦腔。我有一次給她泡了杯茶,她說,我給你唱一段秦腔以示謝意。說著,就聲嘶力竭的模仿著秦腔的發聲狂吼起來,聽她的唱詞,好像一個不懂英語的人冒充英語老師,教學生說,飛機的英語說法就是“比老鷹高些。”
讓人啼笑皆非的善意取笑,還遠遠不止這些。有的人看見我就說著半生不熟的秦腔:“你做啥去呀?你丈母孃身體好著呢沒?她去世了你給她唱一段秦腔,外撩咋咧……”
每逢這時,我覺得自己的尊嚴正在經受著一場嚴峻的挑戰。特別是我老婆把秦腔作為取笑我的工具時,我面頰上的溫度就會急劇升高。
二零零二年,我開始在本地開店經銷光碟,較為暢銷的有云南山歌碟、黃梅戲蝶、流行歌碟。我開業時進的秦腔丁良生的《打鎮臺》、李愛琴的《周人回府》、廣雪琴的《法門寺》、王建軍、張麗的《白玉樓》光碟,五年來都無人問津。二零零七年我娘來看我時,我們透過DVD一一播放欣賞,我們娘兩看的廢寢忘食。
網際網路誕生後,光碟羞羞答答的謝幕。這時我才透過網路真正進入了對秦腔唱、念、做、打和板式、人物性格的中心地帶。現在,我即使閉著眼睛也能分辨出某段唱腔出於哪齣戲和哪位名家。但令人不樂觀的是,我在這裡每遇到一位關中鄉黨,就問他“你愛看秦腔嗎?”回答“是”的都是五十歲以上的人,回答“不愛看”的是年輕的姑娘小夥。
去年十二月十號早上,天陰得像鍋底,大風捲著烏雲滾滾而來。我所在的小鎮上來了一隊身穿紅衣服的人,他們在滿街尋找飯館吃飯。我問他們是幹什麼的,他們說是唱戲的。我一下來了興趣,緊接著問:
“唱什麼戲?”
“秦腔”
我驚訝的問“清唱還是掛衣戲?”
他們說:“掛衣戲。”
“掛衣戲化妝、穿衣就要兩個多小時,卸妝也不會少於一個小時,演員還需要有熱水洗臉上的油彩。今天颳風天氣冷,穿戲衣要脫掉棉衣,演員穿的太單薄,會凍的堅持不住。我穿這麼厚的棉衣和保暖衣,還冷得牙齒直打架。我早上路過廣場時,吊車正在那裡裝卸排水管,秩序混亂得很。在那麼小的廣場上演出,聚集的人群可能有安全隱患。”
他們聽我這麼說,一下打開了話匣子,贊成我的說法。
“廣場離小學也很近,你們在那裡演出,高亢的秦腔音樂會影響孩子們聽課的。我老婆是這裡的人,她根本就不愛看秦腔。你們還記得石國慶的獨角戲《王木犢》嗎?就那個:‘我叫王木犢是陝西人,我老婆叫李么妹是四川人。我愛看秦腔,我老婆愛看歌舞……’兩口子還為這事打架。”
“是有這麼回事。”演員們邊笑邊和我聊著。
我接著說:“秦腔不符合這裡人的聽覺和語言習慣。他們喜歡黃梅戲的儒雅和雲南山歌的風趣,也喜愛本土山歌的鄉土氣息。年輕人愛看現代舞蹈,愛聽流行音樂和草原歌曲。這就和咱們關中人不喜歡看京劇是一樣的。”
“是啊,前幾天我們在其他地方演出,路過的人像是看稀奇,問我們是推銷什麼商品的吧?望一眼就走了。”一個四十來歲的女演員說。
“今天是星期五,住校學生放學後,家長要騎車來接,交通很擁擠,這個時候演出,不安全。如果在晚飯後或者節假日演出,人們一邊出門散步,一邊看戲,也不影響日常工作,大白天都在上班,出來看戲脫不開身呀。”我認真地說道。
幾個演員點頭“嗯,嗯。”
我又關切的問:“你們外出演戲怎麼沒有集體伙食,自己買飯吃?”
“流動演出,不方便帶炊事員,演員口味不同,自己愛吃什麼買什麼。有一次在一個偏僻鄉村演出,卸完妝早都飢腸轆轆了,可那裡沒有飯館,只好自己買了掛麵煮著吃,半生不熟的,唉!”演員們無可奈何的搖搖頭。
我說:“我們小時候在老家看戲,都是給演員搭的大灶,做客飯招待演員,一天四頓。”
“沒辦法呀,時代不同了。”
我也惆悵的說:“真沒想到會這樣。現在沒有人跑十幾里路,去看一場戲和電影了。”
“是啊,數字電影那麼高的質量,也沒人看了。”
我接著告訴他們:以我二十多年來對這裡的瞭解,秦腔的高亢讓本地人聽著太嘈雜,缺乏柔軟的彈性,道白和唱詞都聽不明白,所以他們不愛看,廣場附近的高齡居民會把這種演出當成噪音汙染。這就像漢中人不吃韭菜,關中人不吃花椒那麼簡單;如果互相都想強制給對方喂,肯定會適得其反,毫無效益。非遺的傳承,也一定要選擇適合它成長的“土壤和氣候”條件,漢中不能栽種蘋果樹,關中不適合橘子樹生長,違背了這個自然法則,結出的果子根本就沒人吃。
“對,風俗習慣只能相互尊重,不能牛不喝水強按頭。”一個五十幾歲的老演員點著頭“秦腔就是大秦的聲音,是咱關中的母語,觀中的年輕人都不愛看,這裡的老百姓不喜歡就情有可原了。”
我贊同他的說法:“你們儘可能前往關中、甘肅、青海、寧夏方面演出,那裡的市場應該比這裡廣闊”。他們聽後看法不一,其中一個演員說:“惠民義務演出,既然來了,就去試一試”邊說邊打聽去廣場演出的路線。
兩個多小時以後,廣場方向傳來高分貝的秦腔名家唱段錄音。從演出現場過來的人說,演員帶著臉譜面具,穿著戲衣在臺上做功,口型對著播放的名家唱段錄音孤零零的假唱,人們各忙各的事,沒有觀眾真心看演員的表演。一個小時後便悄無聲息了,穿紅衣服的人群也好像人間蒸發了一樣。
聽到這個訊息,我被一種失落感包圍著。心裡有個聲音不住地嘀咕著:
“這究竟是移植秦腔還是傳統秦腔?”
驀的,我想起了舅舅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留下的幾句話:“這麼多年,我哪裡唱戲就去哪裡看,吃過早飯,背上饃饃,住在戲場場,看完每天三場戲,半夜才回家。以後可再也看不成了……”說完,老淚縱橫的哭了起來。
作者簡介:武朝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