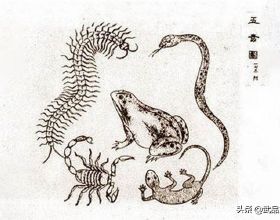一、疑古派與分子人類學圍繞夏的主要論爭
夏是否存在?
這是一個至今仍在討論的命題,現人常將二里頭遺址認為是與夏都目前最相似的遺址,如鄒恆認為是二里頭的一到四期,而許慶偉則認為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的一至四期,但由於至今仍無確證夏朝存在的實品,沒有如同記載商湯的甲骨文一樣記載夏朝的載體或可識的文獻,所以仍有不少一部人認為夏朝可能是不存在的。或將夏朝的存在懸而未決,如二里頭的發掘隊長許宏。
論爭雙方代表,一邊是質疑夏存在合理性的疑古派,一邊是利用先進科技簡介承認夏存在的分子人類學。疑古派基於禹非耕稼國家之王;禹非夏王;“夏”源無解;“夏”無實物以證之;“夏”史斷裂等原因,認為夏實為後世儒生的偽作,中國的朝代歷史始於商朝,實際並無夏朝;而分子人類學則基於Y-DNA遺傳和單倍型O,發現在高廟文化、仰韶文化和紅山文化所對應的時代,推論三皇五帝存在的合理可能,加之漢族源於華夏,分子人類學間接地承認夏存在的合理性,既然古史記載的三皇五帝成為了可能,那麼古史記載的順延著三皇五帝之後的夏朝也存在了合理的可能,畢竟那個朝代有人,有階級相對分化的人;既然漢族源於泱泱華夏成為了可能,那麼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強了夏存在的合理可能性。
關於夏朝是否存在的論爭,至今仍有許多不同的聲音,至今仍是一個持續不斷論爭下懸而未決的命題。
夏禹王立像
二、重建夏代的信史——考古學的當代使命
正如孫慶偉先生所言:“古史重建是20世紀中國史學的重要話題,並直接催生了近代科學考古學在中國的誕生。”以科學系統的考古工作來重建中國古史者,既有締造考古史語正統的傅斯年和李濟,也有開創考古學“中國學派”的徐旭生和蘇秉琦,他們皆在考古與重建之路盡己所能緩慢前行。
(一)建立科學的東方考古正統
建立科學的東方考古正統,是重建中國古史的基礎一步。因不滿於當時“教皇政治、方土宗教、陰陽學術、偈咒文學”,同時受西方科技的不斷影響,傅斯年提出應“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學問”,他建立史語所,主張“史學即是史料學”,他定出土材料和明清內閣檔案為“直接史料”,傳世文獻為“間接史料”,用一種二分法將史料分為直接和間接,主張透過科學的方法,兩種史料的相輔相成來重建中國的正統史學。依據殷墟的發掘,傅斯年將可古史建構到了殷商時代,而透過對殷墟的大量挖掘,史語所的李濟也畢其生之所學整理出《中國上古史》。
以“新獲知識”和“經典遺文”來整理古史,“擴充方法,擴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由此所建立的史語所使命,加上李濟的《中國上古史》,共同形成了初步的中國科學考古學的正統,成為考古學家重建古史的基礎性一步。
夏王啟
(二)見人見物
除了傅斯年和李濟,徐旭生和蘇秉琦則進一步建立起了考古之“物”加文獻傳說才可“見人”的重建方式。
早期徐旭生為了儘可能地減少異軍突起的疑古派對中國古史的影響,透過對古史傳說材料的通盤整理,產下《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是鞏固國人對古史的信心,二是尋找正確的古史研究方法。徐旭生曾說文獻是“故事研究中最嚴整的材料”;傳說是既口耳相傳後,多少有些失真的“最麻煩、最頭痛的問題”,但“對於古史的研究自有其重要地位,不可隨便抹殺”;而遺物作為考古學和民族學的研究物件,可“大量的充實其內容,改正其史籍記載的錯誤”。
因此,在徐旭生和蘇秉琦看來,無論是史料文獻、傳說、和歷史遺物皆有其侷限之處,但對於古史的研究和建構皆有參考的意義和價值,所以唯有將三種史料整合起來,才能相對科學而完整地重建一定的歷史。
這也是他們所推崇的“見人”思想,“單憑考古材料,只能‘見物,只有結合文獻和傳說材料,才能‘見人,建設其真正有鮮活的歷史。”
早期疑古派就是從文獻的角度幾乎完全否定了夏朝的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亦影響了考古學,使當時的考古學逐漸轉向唯實物釋古的學術研究方向,也正是基於考古學逐漸基於出土文物,而不再相信文獻和傳說,徐旭生和蘇秉琦才重新再次確證“文獻+史料+遺物”的考古研究方法,“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出現先殷古史的老材料,其可靠性,比之傳統的神話,自然大的多了。”
夏桀
三、結語
疑古派和分子人類學圍繞“夏是否存在”的跨時空、跨視角所形成的論爭,對夏存在合理性的討論增添理論依據和研究視角,一定程度上亦加重學者們從“疑古”到“釋古”的歷史使命感。重建古史任重而道遠,面對不同時期對夏代信史發出的不同挑戰,考古學家基於建立科學的東方考古正統;“文獻+傳說+遺物”方可見人見物的科學考古之法,逐漸從不同程度對夏代信史乃至古史的重建提出了自己的合理構想和付諸合理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