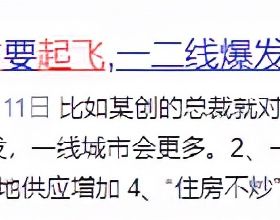我們在之前篇章中涉及的大部分時代都屬於史前時代。這些都是文獻史料未曾留下歷史記載的時代,即便史記記載涉及到該時代,習慣上也被看做是傳說。比如司馬遷編寫《史記》的時候,《殷本紀》中所涉及的年代早於司馬遷生活的年代一千年以上,《夏本紀》以及《五帝本紀》的年代則更加久遠。在《史書》成書的年代,上述歷史就已經被傳說化,其真實性變得曖昧模糊,很難加以確證。
神話是可以從神話學的角度對其進行體系上和構造上的把握,分析神話中對自然現象的描繪,社會組織的表象、神話與利益的關係等等,可以解釋明晰神話的意義。但是留存於文獻史料中的神話多為不連貫的斷片,並且包含著史料編寫者自己的理解及價值觀,或者反映著史料的侷限性。很難斷定其是否重視傳達著神話本身的形態,因為史料也是非常有限的。神話雖然很可能傳達著某種事實,但是對其能否具有歷史意義很難給予斷定。
如前所說,神話有可能反映著記述神話的當時的時代價值觀,有時是為了表述王朝和家系的正統性而產生的。特別是後者對於祖先神的記述尤其具有這種可能性。
另外,在西漢《史記》成書之時不曾出現的伏羲、女媧等“三皇”的記載,至唐代卻補寫了《三皇本紀》,這就可以看做是一個為了順應尋求自我認同的價值觀而記述神話的事例。
從影象學的角度來看,西漢初期的影象中,女媧多為單獨出現,而西漢中期以後,出現了伏羲與女媧的組合,至於兩者交合的形象則出現於西漢末期至東漢時期。由此可見伏羲、女媧的人類再生神話以及開天闢地的盤古神話的普及是在漢代之後的,出現這種世界觀的必要性也是在漢代才出現的。在此之前的世界觀是否如此宏大大則不得而知。
如果僅僅限於祖先神來看,也可能是為了證明周王朝的正統性而對這些神話進行了篩選。所以,五帝時代的世界觀很可能是侷限於包括那方的一部分在內的渭河流域於黃河中游地區的,它作為華夏系神話只是中國神話世界的一個部分。
與之相比,《山海經》等文獻中記載的自然神則很有可能是以更寬廣的世界觀為背景的。但是它們也是誕生於戰國時代至西漢初期的中國世界觀之中的鬼神形象。上溯至商周時代等史前時代的鬼神多種多樣,在各區域一定分別存在著當地的神靈,因此我們不應當只把眼光停留在只存於文獻中的華夏系神話來討論史前世界,這是不客觀的。
山海經
因此只要歷史學是作為人文科學而存在,就必須是以科學為依據,無法證明就無以謂之為科學。從十九世紀上半葉成立的考古學作為一門學問,是運用科學手法對過往曖昧模糊的時代進行系統化分析的學科。另外,對沒有文獻記載的時代所做的研究就被稱之為史前學。而我們之前眾多篇章所涉及的大部分內容就正是屬於考古學和史前學研究範圍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