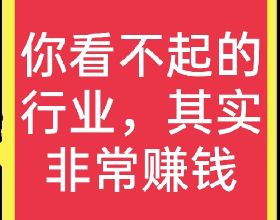來源:法治日報——法制網
● 為了維持基本生活,農村老年人在業比例較高,仍然是絕大多數農作的主力。與子女外出務工前相比,他們農作的負擔加重了,但獲得的報酬並沒有高多少
● 農村留守老人精神空虛、孤獨感嚴重成為普遍現象。由於居住分散、社會組織發育不充分,老年活動輻射有限,特別是深山區的農村獨居老年人,極易陷入自我封閉的心理狀態
□ 法治日報全媒體記者 文麗娟
晚上8點,李恩頌從口袋裡掏出新買的智慧手機,試了好幾遍後,撥通了大兒子的視訊通話。影片那頭,兒子正在加班,她趕緊說“沒啥事,掛了吧”。因為剛學會用智慧手機,一下找不到通話的結束按鈕,她用右手食指在螢幕上劃拉了幾秒鐘才把影片掛掉。
半弓著腰,用手捂著右下腹,李恩頌走出家門,來到村裡的文化廣場。廣場上有不少村民坐在馬紮上圍著圈聊天,都是些家長裡短,她抄著手聽了一會兒後也坐了下來。
李恩頌所在的村莊是山東省臨沂市一個典型的山區村。這裡的村民靠山吃山,多種植玉米、小麥等農作物。村裡的青壯年大多外出務工了,剩下的多是留守老人,除了完成農作外,他們往往還要負責照料自己乃至孫輩的生活起居、疾病就醫以及精神慰藉等。

圖為2020年4月20日,青島市西海岸新區營南頭村,一位留守老人坐在村頭曬太陽。 CFP供圖
在我國,有千千萬萬像李恩頌這樣的農村留守老人。根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生活在農村的60歲及以上人口有1.2億人。
其中留守老人佔了很大的比重。根據2016年民政部的摸底排查結果,我國有1600萬左右的農村留守老人。
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程序的加快,農二代、農三代相繼離土出村,造成農村家庭日漸“空巢化”。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原副部長劉守英從事了30多年的涉農研究,他發現,最能代表中國農業和農民的是40、50和60後,這群人有很重的鄉土情結,以鄉村為歸依,以土地作為主要生活來源,以農業作為主要職業,“即便出去了也會回來,不會離開村莊”。
種種因素之下,不少農村老人留了下來,與村莊、土地相伴。他們目前的生存狀況如何,面臨哪些困難?近日,《法治日報》記者深入多個農村進行了調查採訪。
生活
每天隨便吃一餐是常態
李恩頌今年61歲,有兩個兒子,大學畢業後都留在北京工作。以前,為了供兒子讀書,她和丈夫種植過黃煙、生薑,最多的時候兩人種了30多畝地。
“那時候,什麼賺錢種什麼。”回憶多年前的“高光時刻”,李恩頌一臉自豪:“每天起早摸黑下地,幾乎沒有正點吃過飯,趕上好年景時一年能賺10多萬元。”
常年超負荷勞作給老人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去年年底,李恩頌生了一場大病,至今尚未痊癒。兒子在家照料半年後回到北京上班,日常生活起居只能靠她自己和老伴。
從拄著柺杖緩慢行走到自由活動,李恩頌花了3個月時間。為了全身心照顧她,丈夫不再繼續租種原來的大部分田地,只留了5畝地種植農作物,農閒時便在村子裡打零工補貼家用。
“沒辦法,孩子們都不容易,能幫他們減輕一點負擔算一點。”10月4日中午,李恩頌一邊做飯一邊對記者說。
丈夫打零工的地方管午飯,李恩頌只要做她一個人的伙食。不到半個小時,飯菜上桌,一碗地瓜粥、一份鹹菜。“中午一個人吃飯,圖個方便,晚上再炒點菜。”她說。
同村的李漢林大多時候也選擇簡單對付一餐。81歲的他正忙著收割,沒有功夫吃飯。
“咚!咚!”最近每天下午3點左右便會傳來一陣敲打聲,李漢林按時出現在村子裡的文化長廊,這裡曬著他辛辛苦苦從地裡收來的紅豆,他要趕在天黑之前將豆子從殼中剝離。簡單啃了幾口饅頭,他便開始工作了。沒有專門的輾軋工具,他就蹲在地上用一根粗壯的棍棒上下敲打,打一陣挪一處,紅豆在他的反覆擊打下一粒粒蹦出來,長廊裡四處都是他的豆子。
全部打完後,李漢林扶腿起身,緩緩走到長廊一頭拾起掃帚,彎腰將地上的豆子掃攏,再用雙手一捧一捧盛起來倒入尼龍袋。他指著袋子,眼睛眯成一條縫,笑著對記者說:“今年收成大概有100斤,按照今年的售價,可以掙800元嘞。”
李漢林的兩個兒子在山東青島務工,平常會給他匯點款,但他都拒收了,因為“現在還能自給自足”。他掰著手指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種了3畝地的農作物,收成可供日常生活開支;在村裡的楊樹林裡插空種了紅豆和綠豆,額外增加一些收入,可用於支付家裡的人情往來;政府還會發放養老金和貧困金,夫婦倆差不多有小1萬元收入。
記者採訪發現,為了維持基本生活,農村老年人在業比例較高,仍然是絕大多數農作的主力。有不少留守老人告訴記者,與子女外出務工前相比,他們農作的負擔加重了,但獲得的報酬並沒有高多少。
早在2015年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就顯示,34.36%的鄉村老年人的主要收入為勞動收入;46.4%靠家庭成員供養;7.48%靠離退休養老金養老;6.81%靠最低生活保障金養老。
2016年的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資料則顯示,當年我國鄉村老年人口的人均年收入約為9510元,只及城鎮老年人口的三分之一。
就醫
“小病拖大病挨”屢見不鮮
秋天的湖南氣溫很不穩定。10月7日,溫度驟降,在冷風中,金山縮了縮脖子,膝關節又開始疼了。他去村裡的診所,花25塊錢買了一盒膏藥。
步行10多分鐘後回到家,他撕開包裝,拿出一貼膏藥貼在左腿膝蓋上,再用雙手撫平。起身去門後掛鉤上抓了一件褂子披上,開啟電視。折回來半躺在藤椅上,順手剝開幾顆剛從地裡收上來的花生丟進嘴裡,一邊嚼一邊看電視。
晚飯時間,兒子打電話回來,問他最近怎麼樣,他在電話裡高聲說:“別擔心我,好著呢!”
金山所在的村莊位於湖南省西部地區,村裡的青壯年多半去了省會長沙或者廣東、上海等地務工,留下的多是老人,有些老人要幫子女帶孩子,有些年紀稍輕點的老人還要照顧年齡更大的父母。
“小病拖大病挨”是這些老人的普遍心態:有的患風溼病多年,每逢颳風下雨腿腳疼痛難忍,卻認為“不是大病,忍忍就過去了”;有的長期偏頭疼,卻只在發作時吃點止疼藥;有的多年受哮喘折磨,卻習慣了難受時去藥店買羅漢果泡水喝……
李恩頌的病就是這樣硬生生拖出來的。去年年中,她已出現了不適的徵兆,但沒放在心上,加上農活繁重,她只去村裡的診所開過幾次止疼藥。直到去年年底,她胃疼難忍,在老伴的陪伴下去醫院,結果醫生給她開了病危通知單。
“每次打電話回家,她都是報喜不報憂,直到扛不住了去住院才告訴我,好在病情有了好轉。”李恩頌的兒子秦華每談及此,都很是懊悔,他自責自己沒有頻繁和父母保持聯絡,更沒有密切關注父母的身體。
2016年的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資料顯示,超過70%的鄉村老年人罹患不同種類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但記者近日採訪發現,很多留守老人即使明知自己患有慢性疾病,也不會輕易選擇就醫,原因是“開銷大、怕花錢”。
對此,劉守英指出原因:“雖然近年來醫保報銷比例有所提高,但一些慢性病急需的康復護理等專案尚未納入醫保,基層醫療衛生服務中心常常‘有室無人’,醫養結合有待落地,大病救助依舊杯水車薪。”
而讓人難過的是,雖然身體不適,但由於子女不在身邊,這些留守老人還要自己負責照顧自己。
劉守英在調研中發現,實際上,農村留守老人具有較強烈的日常生活照料需求。調查資料顯示,有8.57%的農村老年人需要基本日常生活照料,即需要他人幫助吃飯、穿衣、上廁所、上下樓、室內行走等,所需照料時長平均超過4年;有11.63%的農村老年人需要他人幫忙做家務,且所需照料時間超過5年。無論是基本日常生活照料還是工具性日常生活照料(做家務),農村老年人的需求皆顯著高於城市。
“然而,平均而言,約三成的子女一年內幾乎沒有幫助老年父母做過家務。其中,外出子女每週至少幫助老年父母做一次家務的比例僅為6.68%,高達50.71%的外出子女一年內幾乎沒有幫助父母做過家務。”劉守英說。
金山的兒子金輝冬對此深有體會。大學畢業後,他在長沙定居,工作地點則在廣州,一年到頭回老家的次數屈指可數,“更不用說幫父母做家務了”。
心理
情感聯絡被切斷很孤單
三五個老人蹲在牆角曬太陽、自己宅在家裡看電視……這是記者在農村採訪時看到的普遍現象。隨著土地流轉、年齡增加等,很多老人無法繼續耕種,而村莊人口又大規模減少,他們習慣的串門聊天等社交方式日漸縮減。
“傳統的中國鄉村,是一家一戶、一代一代在一起;現在,老人身邊常年沒人。以前,家裡年輕一輩出去打工,孩子還留在農村,最起碼老人還給孫子、孫女做飯,他還有存在感。現在這撥出去打工的年輕父母,小孩小的時候就帶在身邊,到小孩上初中時,有一個人回來陪讀,初中在鎮上、高中在縣城。這樣基本把老人跟傳統的血緣關係、情感聯絡切斷了。這些切斷以後,老人不是窮,而是極其孤單。”劉守英說。
這點在江兆洪夫婦身上體現得非常明顯。江兆洪有兩個女兒、1個兒子,大女兒嫁到山東棗莊、二女兒嫁到山東臨沂、兒子在山東煙臺做醫生。兒子結婚生子後,老伴便被接去煙臺幫忙照看孫子,家裡常年只剩下江兆洪一人。
10月5日下午,記者來到江兆洪家,正巧趕上他老伴回來“探親”。江兆洪樂呵呵地在廚房裡忙活,“家裡好久沒有人氣了”。他所居住的四合院門口,堆著一摞剛收的玉米,整個院子被遮陽棚覆蓋,天井上面爬滿了南瓜,旁邊搭著一個透明的露宿棚,裡面鋪滿了剛摘的花椒。
這些作物都是江兆洪為了打發時間種的。“要不然農閒時整天沒事幹,太無聊了。”江兆洪說。如果作物都打理完了,他就給自己增加一份工作——打掃衛生。四合院共有5間房子,他便挨個收拾。客廳的一面牆上,貼滿了兒子女兒和孫子孫女的照片,這些照片是他重點打理的物件,“基本隔兩天就會用抹布擦一遍,有時也會對著照片嘟囔幾句”。
“3年沒見兒子了,還是很想他們的。”江兆洪指著兒子的照片給記者看,有點不好意思,“估計都變樣了”。
老伴的心態則完全不一樣。她每天和兒子一家住在一起,要負責他們的日常生活,還要督促孫子做功課,“每天忙得腳不著地,有時還真想回來歇一歇,但沒辦法,孩子們壓力也大,能幫一點是一點”。
留守農村的李恩頌也在家裡貼滿了兒子們的照片。之前沒有智慧手機,她只能透過老人機一個月或半個月與兒子通一次電話,但太久不見人,心裡還是鬧得慌。前段時間,兒子回家探親時,給她買了一部智慧手機,下載了微信,教她使用視訊通話和檢視“朋友圈”。
她並不會輕易點開兒子的對話方塊,只是在每天臨睡前多了一個任務:先刷刷短影片,再點開兒子的“朋友圈”看看他們一天的動態,然後關閉資料流量睡覺。
“孩子不在身邊,還是會感到孤單,但沒什麼事就不要打擾他們,他們那麼忙。”李恩頌說,不過還是希望孩子能有事沒事常回家看看。
劉守英及其團隊調研時發現,農村留守老人精神空虛、孤獨感嚴重成為普遍現象。由於居住分散、社會組織發育不充分,老年活動輻射有限,特別是深山區的農村獨居老年人,極易陷入自我封閉的心理狀態。一些志願者反映,他們上門最重要的工作並不是為老年人提供做家務等照料性服務,而是陪伴。
記者也在採訪中獲悉,近年來,子女外出流動、家庭成員長期分離使得農村留守老人的孤獨感愈發強烈,抑鬱情形有所增加,甚至有的老人還出現絕望自殺傾向。
探索
大力推進“互助性養老”
山東省日照市莒縣庫山鄉解家河村黨支部書記解則江對於留守老人的心理狀態格外關注。因為早在2015年時,村裡有兩個留守老人由於強烈的孤獨感,選擇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這件事給解則江帶來了極大的衝擊。解家河村現有人口630人,60歲以上的老年人佔20%,其中又以留守老人居多。如何讓這些老人的生活需求和精神慰藉都能得到滿足?解則江一直在思考著——“互助性養老”或許是一個答案。
2017年春節後,解則江和其他村幹部利用村裡土地流轉所得收益,計劃在村子裡建設一座配有餐廳、住宿、洗漱、休閒娛樂為一體的幸福院。
從2017年6月開工建設到2018年7月投入使用,解則江和其他村幹部克服重重困難,終於讓解家河村的老人們有了屬於自己的幸福院。目前,幸福院裡共入住58人,其中70歲以上的56人。
10月6日中午,記者來到解家河村幸福院,一些老人正坐在院子裡的長廊上聊天。記者看到,院內宿舍共21間,伙房、餐廳、醫務室、文化活動室、接待室、閱覽室一應俱全。
中午12點是開餐時間,鈴聲一響,老人們拿著餐具排著隊有序進入餐廳。餐廳內,桌椅潔淨一新,桌上擺放著土豆絲、辣椒炒肉、芹菜炒肉、炒豆腐、大鍋白菜等。
“生活挺好,免費吃住,還有夥伴聊聊天。”74歲的楊德吉是入住幸福院的第一批人,談起自己在這裡生活的3年時光,老人不停地讚歎。
雖然住在幸福院,但楊德吉平常還會在村裡打打零工,一天收入70元。“老人只要身體健朗,都可以在村裡乾點活,有事幹就能讓他們覺得自己有存在感、有價值。”解則江說。
“解家河村抱團養老、自我保障、互助服務的幸福院建設,既給老年人提供了集中居住、互相照顧、快樂生活的自由空間,使老人們物質供養有保障、生活照料有人管、精神慰藉有依託,又解除了外出務工子女的後顧之憂。”庫山鄉副鄉長王德鳳說。
2019年,這種“抱團養老”的幸福院模式在庫山鄉全面鋪開。據王德鳳介紹,目前庫山鄉已建立25處幸福院,1處綜合養老服務中心,2處服務站點,同時與專業的家政服務公司合作,由各服務站對所轄各村統一配送飯菜,建成“系統+服務+老人+終端”的智慧養老服務體系。
庫山鄉小小幸福院托起“大民生”是我國近年來大力推進“互助性養老”的一個縮影。資料顯示,我國農村地區目前已有養老機構2萬多家,幸福院、頤養之家等互助養老設施10.8萬個,多層次的農村養老服務網路已初步形成。
所謂“互助性養老”,就是由低齡老年人照顧高齡老年人,由身體狀況較好的老年人照顧身體狀況較差的老年人,以此完成養老服務的代際傳遞。
據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汪三貴介紹,農村“互助性養老”可以透過志願服務、創立專門機構、長期護理險等幾種模式實現,這些模式介於居家養老和第三方社會化服務之間。
記者注意到,在農村,“吃住一體”型、“管吃不管住”型、“公共文體娛樂+上門服務”型……各種型別的“互助性養老”模式不斷落地,依託村級老年協會、依靠有威望的老人帶動組織,透過“少老人”幫“老老人”來解決“缺人”問題。
在山東省沂水縣,“關愛老人·情暖夕陽”寸草心志願服務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由農村黨支部領辦志願服務隊,發動村內50週歲以下、常年在家、有一定服務能力的黨員,帶頭開展服務,服務物件以分散供養特困人員、留守老人和居家養老人員為主。服務內容主要包括打掃衛生、料理家務、清洗衣服、幫助代購,有效滿足群眾需求。
在北京市密雲區,統籌各鎮養老服務機構和設施組建本鎮鄰里互助機構,由機構根據老年人的分佈,在本地招募鄰里互助員,組建若干鄰里互助隊,形成“鄰里互助機構、鄰里互助隊、鄰里互助員”三級組織結構,有效解決農村特別是山區獨居老人的居家養老照料難題。
……
華北電力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劉妮娜及其團隊一直在研究“互助性養老”模式,她告訴記者:“‘互助性養老’在農村的優勢,首先體現在農村具有建立在血緣、地緣、親緣關係上的鄰里守望傳統。”
劉妮娜認為,村黨委領導下的村委會、集體經濟組織、農民合作社等為開展農村互助養老提供了組織基礎;此外,低齡健康(準)老人、黨員等鄉村骨幹則提供了人力資源支撐。
“農村老年人收入相對較低,對市場服務的購買力和購買慾望都相對偏低,對‘互助性養老’服務接受度相對較高,這也是其突出優勢之一。”汪三貴說,“‘互助性養老’肯定是將來農村養老的大趨勢。”
困境
資金和管理都是掣肘
然而,面對農村人口老齡化挑戰及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推進農村養老服務仍然面臨十分嚴峻的形勢。
“不好管理。”幸福院執行3年來,解則江最大的感受就是——看到老人們樂享天年,他很欣慰、很有成就感,但現實中也存在一些困難,比如老人們各有各的小脾氣,聚集在一起難免產生摩擦,這對管理來說是一個挑戰。
資金也是一大制約因素。
據王德鳳介紹,目前庫山鄉在推進智慧養老過程中,存在的困難之一就是資金不足。為了儘量克服這一難題,庫山鄉按照“上級補一點,村裡籌一點,個人出一點,社會捐一點”的原則,由鄉黨委政府對幸福院建設資金存在困難的村,預支啟動資金進行建設;除上級補助資金外,剩餘款項按照鄉黨委政府補貼50%,村自籌50%的方式進行。同時積極透過駐村“第一書記”爭取單位幫扶資金、吸納社會捐贈。
陸詩雨是騰訊研究院高階研究員,她在調研中發現,農村留守老人更容易因為缺乏與親密家人的日常交往,造成不同程度的“社會脫節”。破解這一困境的突破口之一是鼓勵、助力其“再社會化”,即持續適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價值觀念、行為規範和社會知識技能的更新、改善、充實和提高,而各種輕便的數字連線是助力農村留守老人“再連線”“再社會化”的第一步。
但她發現,在農村,目前網際網路尚未普遍覆蓋,“數字連線點”偏少。
而對於“互助性養老”來說,雖然該模式目前在農村遍地開花,但同樣面臨一些障礙。
劉妮娜舉例說,比如農村大部分人對於“互助性養老”的認識仍不清晰;資金投入不均衡且來源單一;農村“互助性養老”相關組織功能尚待充分發揮;服務供需錯位且質量不高;組織和設施缺乏有效管理和運營等都是持續推進“互助性養老”的攔路虎。
建議
多管齊下改善老人境遇
那麼,“互助性養老”該如何進一步落地?針對農村養老問題,還有哪些“答案”?
劉妮娜給出了自己的建議:首先要弘揚農村互助文化,讓鄰里守望、互助合作成為農村的主要文化;其次由政府引導多渠道籌資,增加農村互助養老資金支援,可以推動長期照護保險試點地區購買農村互助照護服務,除政府資金以外,讓更多企業、基金會和其他社會資本參與農村互助養老試點的資金支援。
“也要因地制宜確立組織形式,做好農村互助養老組織機制建設。比如是否可以確立老年協會作為農村互助養老組織的主體地位,由農業農村部出臺相關政策鼓勵農民合作社由經濟功能向生活服務功能拓展,發揮好婦女組織等基層群團組織的作用;由民政部牽頭制定農村互助養老服務發展指導意見,最佳化村級助餐服務,抓實條件好、輻射性強的助餐點建設等。”劉妮娜說。
劉守英的建議是要多管齊下:進一步提高養老保障水平,建立農村養老金穩定增長和動態調節機制。目前,我國農村老年人的養老保險停留在“廣覆蓋、低水平”階段,與城鎮老年人的養老金水平存在較大差距。可嘗試對標城市居民養老金增長與調節機制,著力提高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金水平,增加“養命錢”的籌措渠道,輔之以精準化養老服務補貼制度。
提高健康服務水平,解決農村老年群體“就醫”問題。最佳化醫療衛生服務設施佈局,對於長期未使用的村衛生室進行整改,科學制定基層衛生服務人員的培養、晉升、補貼政策,緩解當下因缺少醫務人員造成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無法正常執行的狀況;建立農村老年人急救體系,建立山區鄉村集體配置急救車制度、增加急救站,並對鄉村“4050”人員(指處於勞動年齡段中女40歲以上、男50歲以上的人員)進行急救培訓,增加人員供給,提高急救呼叫滿足率;醫療衛生資源進一步下沉,放寬鄉村衛生室藥品供應、輸液許可權等,滿足農村老年群體的基本就醫需求。
“對於一些慢性病藥物,在保證醫療安全的基礎上,對診療規範和指南規定較為明確、安全性高的一線藥品,可嘗試開具長期處方,讓老年患者少跑路。”劉守英說。
從數字科技助力的角度,陸詩雨建議,為農村留守老人保留、創造更多“數字連線點”,“這些‘數字連線點’不侷限於社交網路,還可以透過各種充滿互動的數字內容產品,如老年人喜聞樂見的長短影片、棋牌遊戲,為老年人建立補充型的社會網路”。
這一想法得到了秦華的認同。他發現,母親有了智慧手機後,心情都明媚了不少,閒時刷刷短影片,偶爾還會和外地的親戚朋友影片聊天。
他也有一點自己的想法:能否在農村探索建立代管機構,負責資金運營、生活用品購買及資訊服務?
“給父母錢,他們不要,即便收了也捨不得花。如果有這樣一個代管機構,子女每個月打一筆錢進去,由工作人員幫忙買菜、買藥或者其他生活用品送到家裡去。等機制成熟後,從物質到資訊實現全面幫扶,為子女與父母搭建資訊橋樑,比如父母生病時可及時告知子女。”談及如何幫助留守在家的父母,秦華有點無奈,又滿懷憧憬。
(文中留守老人及其子女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