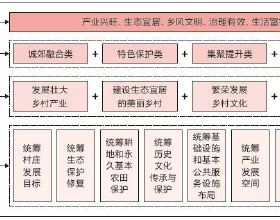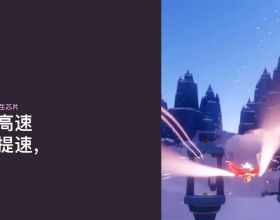新時代,新徵程,呼喚詩歌創作的新高峰。當前,我們國家的社會面貌日新月異,各個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會文化領域也是激情澎湃。現實生活給詩歌創作注入了新活力,也提出了新要求。在我看來,詩歌體裁的多樣化,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要求。
我國數千年的詩歌遺產十分豐厚。大量的詩歌作品不僅題材豐富多樣,而且體裁方面也是非常多樣,唐宋後出現諸體並行的局面。早期上古歌謠,二言體如“斷竹,續竹;飛土,逐宍”(載《吳越春秋》),三言者如《尚書·皋陶謨》所載:“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轉引自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魯迅認為:“去其助字,實止三言,與後之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同式。”)《詩經》則是西周至春秋數百年四言體集大成的總彙。戰國出現雜言的楚辭體,漢魏六朝有五言為主的樂府體(也有雜言體),東漢有七言的柏梁體,晉代陶淵明有五言古體和介於詩與賦之間的辭賦體,南齊有七言的永明體為格律詩的濫觴,唐代近體、古體多樣並行(近體以齊言的五言、七言為主,少量六言;廣義古體不僅有齊言為主的五古七古,還有自由奔放的雜言或齊言歌行體等),唐五代宋有詞牌多樣的詞體(詞也有少數齊言如《浣溪沙》等),元曲在詞的基礎上獨創新體,明清詩詞沿用以前格律詩詞為主兼及其他體裁而沒有明顯新體生成。近百年來則有打破既有一切舊體格律的自由詩新體,當然還有注重格律的新詩。綜上所述,古今詩歌體裁,格律最嚴者無疑是唐初前後形成的近體格律詩和唐宋詞、元曲(詞和曲,一個牌子往往有多種體式,其格律嚴格固定度弱於格律詩),而格律最寬鬆者無疑是新體自由詩。由此看來,在格律最嚴的格律詩(以及詞、曲)和最寬鬆的新體自由詩之間,還有多種詩歌體裁先後出現、後來同期並行使用,留下大量豐富多彩的詩歌遺產。也由此看出,幾千年詩歌發展,體裁輩出,多姿多彩,各種體裁對於表達表現各種題材內容是各得其宜、各展其長,而不能簡單地判定誰優誰劣。
如果詩歌刊物只按照既有的某些格律來決定刊登的作品,則戰國無法發表詩經體以外的楚辭,漢魏無法發表樂府體之外的五言古風和曹操《短歌行》之類的四言詩,晉代無法發表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唐代無法發表李白的《將進酒》等雜言歌行體……如果我輩不突破固守單一格律的狹隘格局,則當代詩詞欲步明清後塵而不能,遑論追步唐宋,更無法超唐邁宋。明清詩詞相比唐宋之前成績平平,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其侷限於唐宋以來已經成熟規範的格律之中,為狹隘的格律格局束縛所致。而與其相反,唐代詩歌之所以成就歷代詩歌頂峰的地位,正是其海納百川、不拘一格、縱情歌唱的結果。
有鑑於此,我們的詩歌出版工作,特別是詩歌刊物,應多開墾廣袤園地來刊登上述各代創新作品,鼓勵多樣化體裁或者突破常規的新體裁的創作,應當意識到當代詩壇的屈原、曹操、陶淵明、李白等詩藝參天大樹,要靠我們開墾的肥沃土壤來培植和造就。
在當前社會生活豐富多彩、文化藝術多元並美的新時代,我們應當一方面不要侷限於格律詩(以及詞、曲)和新體自由詩兩個大的體裁方面,而是要同時廣泛利用兩極中間各種優秀的詩歌體裁遺產,另一方面在已有體裁基礎上進行詩歌體裁的大膽創新創造。這種創造無外兩個方面:創造全新的體裁,或者對既有體裁的改造,包括既有體裁的組合運用。只有這樣,才能全面有效地記錄歷史、歌詠時代,也才能充分發揮詩人即創作主體個性表達的多樣化,以充分滿足廣大詩歌受眾閱讀趣味的多樣化。只有詩歌體裁的百花競放,才能帶來詩歌作品的萬種風情,才能全面有效地反映新時代的新氣象。
不僅格律詩詞要“求正容變”,其他體裁也必須要“求正容變”。要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讓中華先賢創造的獨特的漢字精靈在舊體格律詩與新體自由詩之間縱橫馳騁,用豐富多樣的詩歌體裁來記錄日新月異的新時代、歌詠豐富多彩的新生活。天意君須會,時代要好詩,而要不拘一格縱情歌唱,一任澎湃激情自由奔放,就必須充分利用幾千年積累的中華詩歌傳統,廣泛採用曾經創造大量優秀作品的各種體裁、體式,並大膽創造新的體裁、體式進行創作,只有這樣才能迎接當代中華詩歌新高峰的到來。(趙安民)
來源:文藝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