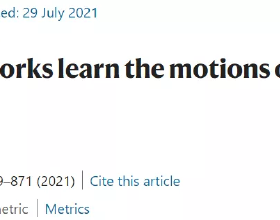兵團點滴令我永記
庫鐵軍
1969年5月16日,這是我離開天津去內蒙兵團的日子。火車站臺、車上車下擠滿了人,交談聲、呼喊聲充滿了站臺。人們臉上各種表情,憂傷、恐懼、興奮。火車開動了,一瞬間哭喊聲連成一片。車廂裡有一個男生用白毛巾捂著臉,大聲嚎哭:“媽媽啊,我再也見不到你了。”望著有哭有笑的人群,我心裡湧出一股奇怪的念頭,列車快點開吧,開到我們要去的邊疆。我渴望見到的美麗的地方。記不清路上走走停停用了多長時間,火車終於停在烏拉特前旗站。路基下到處都是卸下的行李,有的已被摔散。接站軍人大聲喊著名字,分派連隊找行李。我被分在五連,我妹妹分在六連。我要求去六連,上了六連的車。可行李被五連拉走了。到了連隊已是半夜,黑咕隆咚什麼也看不清。第二天睜開眼往屋外跑,滿眼黃土,低矮的茅屋,滿腔的熱情一下子涼了下來。
庫鐵軍兵團照
下午和同學去五連拉行李,五連連長說:“來五連吧,把你妹妹也接過來。”我想那邊已安頓好,還是去六連吧。我和同學用小車拉著行李,天色漸晚,走到六連後門水井處,對面莊稼地裡突然冒出一個人來,唱著:同志我問你,你到哪裡去?通行證兒你可帶著呢?拿過來看看、拿過來看看,你才能過去,因為情況緊張馬虎不得。我們不知對方是何人,慌忙拉車快跑,車又重人又慌一個小坡幾次才拉上去,過了水渠進入連隊心才安下來。後來才知道,那可能是比我們早來幾個月澆水看地的北京戰友。
我被分配到炊事班,從來沒做過飯的我很是怵頭,切土豆絲老是切手;發麵老記不清程式,是先放鹼還是先放麵肥。一天班長王琪讓我去洗蘿蔔,我用車拉著蘿蔔和大盆,跑到菜園的水井邊,打水換水一遍遍洗。蘿蔔上沾著泥巴很難沖掉,只能用手摳。王琪站在炊事班門口一會兒一喊,洗好了沒有,快點!他越喊我越著急,手也跟不上趟了。等我滿頭大汗的把蘿蔔拉回來早已換菜了。班長說:“等你,早就誤飯了。”炊事班除了保證正常的伙食還有病號飯。給生病的人開個小灶。每個炊事員輪流值班負責病號飯。我不會擀麵條,每次輪到我值班都和別人換工。別人也樂得換,一是輕省二是也能跟著開個小灶。病號飯在伙房裡的小套間做。有個小灶臺、一口鐵鍋。一天輪到小溫值班,熗鍋、下面,香噴噴的做了一鍋,打出幾份病號飯後,小溫也拿著碗來盛,裡間小屋,光線很暗。小溫用馬勺攪了攪鍋,發現裡面有個黑乎乎的東西,以為是抹布掉進去了,用勺子撈上來一看,竟是隻死老鼠,早已煮的面目全非,看得讓人頭皮發憷。原來灶臺上有個老鼠洞,熗鍋的香味把小老鼠吸引了過來,偷吃,不小心掉進了鍋裡當肉煮了。幸虧我沒有蹭吃病號飯的嗜好,要不這輩子都不想吃麵湯了。
半年後,我被調到了20班當班長。大田排艱苦的勞作讓人們最初的熱情逐漸冷卻,眼前的現實讓我思考,我們在做什麼?大家都是十幾歲二十來歲的青年,正是能吃要發育的年齡,物質生活匱乏。日常的伙食滿足不了身體的需要,每天勞作收工,懶散地躺在炕上聊著城裡的好吃的,來個精神會餐,我說這個好吃,她說那個更好吃。閆會勤躺在炕上喊:“連長“我想吃只雞。”有人突然說:“活寶,這有好吃的。”(活寶是閆會勤的外號)只見閆會勤騰的坐起來:“真的?”眼睛裡閃著光,賊亮賊亮。那眼神我至今難忘。別看閆會勤平時稀鬆,幹活可是把好手,從不偷懶耍滑。
開始鋤地了,八百米長壠,有頭又無頭。大家鋤著,只要遠遠有人走過,大夥會不由自主的停下來,呆呆的望著,希望他向我們走來。可他只是路過,遠遠地路過。大夥很是失望、悵惘,又悶悶地低頭鋤起來。直到有一天,有人騎馬跑過來,遠遠的喊:今天早收工,晚上看電影。大夥扔掉了鋤頭,兩隻胳膊高舉著亂揮:噢,噢,萬歲!
艱苦的勞動,眼前的生活讓我思考。看著稀疏的小苗從黃土地冒出來,一點一點慢慢地連成一片,綠色越來越濃蓋過了黃土,整個大田滿眼是綠。天涼了,收穫了。大田又變成了土黃。第二年綠色又蓋過了土黃,望著土地由黃變綠,又由綠變黃,年復一年。我不禁心裡問自己,我們在幹什麼?難道我們要在這裡像作物一樣輪迴下去嗎?不,我不願意。但你又想怎樣?我不知道。
兵團除了艱苦的勞作,偶爾也會搞一些軍訓。一天夜裡緊急集合搞拉練,裝備齊全,部隊走出營房,冬天的夜也沒覺得冷,不知部隊去哪,走在鹽鹼地裡,稀疏的枳機草迎接著我們,沒有人說話,只有腳下一片咔嚓咔嚓聲。巨大的彎月像一個金色的鉤子掛在前面,好像很近。走幾步就能摸到它,我們彷彿是進入另一個星球。望著那巨大的彎月,我想去摸它,心裡呼喊,我們要去哪?我們要去幹什麼?
1971年內蒙兵團作為北京軍區序列,參加了地方“一打三反運動”。兵團抽調一部分力量到地方去宣講檔案,六連抽掉了10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團被分配到集寧地區豐鎮一帶。支農一年,白天和老鄉一起下地,晚上向群眾宣讀檔案報紙。住在老鄉家,一家一戶吃派飯。一天一斤二兩糧票,四毛錢的伙食費。在兵團艱苦還能見個油腥,逢年過節或者麥收時還能吃上肉。在地方這一年更是艱苦,就沒吃過菜;老鄉家從不炒菜,一年到頭就是醃鹹菜漬酸菜,讓我真正體驗了農民生活的艱辛。
豐鎮,泗城窪公社,我住在一個村裡。夏根友是村裡的生產隊長。一天,夏根友問我:“你天天都洗臉嗎?”我以為他跟我說笑,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他伸出黑黢黢的雙手說:“我一星期也洗不了一次。” 看著那雙黑手,心想,這雙手不但為自己土裡刨食,還要刨出公糧,就是這雙手養活了我們啊。
夏根友四十多歲是個單身漢,幾年前收留了一個從河南逃荒過來的女人,高高瘦瘦,頭髮枯黃。看著比夏根友大,還帶著一個孩子。我見到時孩子已長成半大小子。我們在村裡那年,女人已經懷孕,挺著大肚子,看著快要生了,夏根友滿心歡喜。一天女人肚子疼,找了村裡一個郎中,紮了幾針,肚子不疼了。可是胎死腹中,小地方弄不了,送到縣城,不知怎麼又要剖腹產,大出血,情況危急。給女人輸血,村裡叫上幾個青壯男勞力一起去縣上,我正在村裡,他們又叫上我。那時起,我知道了自己是A型血。抽血的時候,不知那老護士心疼我是知青,一家一戶吃派飯,沒處進補,還是別的原因,把我往邊上一扒拉,不行,血管太細。那個死嬰兒被取出來,裝在一個臉盆裡,是個男嬰,胖胖的,頭髮很黑很密。夏根友看著孩子嚎啕大哭,孤身半生,好不容易有了孩子,轉眼又沒了,讓人落淚。
女人被推了出來,看見夏根友第一句話:"這得要花多少錢啊?"夏根友強忍住淚,撫著女人像枯草一樣的頭髮:"不咋,不咋,沒花多少。"幾十年過去了,不知夏根友是否健在,希望他過得好。
集寧地區召開知青系統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兵團戰士也是知青,領導讓我去。從內心講,我沒有太多熱情。可領導讓去,好在不發言,去聽聽就是了。大夥集中在集寧市,什麼單位記不清了,人真不少,大夥打地鋪。大會第一個安排就是讓大家去洗澡。幾年沒洗澡了,在兵團一暖水瓶熱水洗頭、洗澡全包了。在這裡能在熱水噴頭下又衝又搓真舒服,這真是最奢華的享受。
會議除了大會發言,還有小會學習。代表們集中在幾個房間,學習討論。一天我去隔壁房間找人,一推門,屋裡只有一個貧下中農大娘,她是作為熱心照顧知青好房東,選為出席會議代表的。這大娘正在翻一個錢包,這錢包一看就知道不是她的,是知青的。她看見我,一陣慌亂,嘴裡喃喃地說:“想回去時給孩子們買個油繩(油條)。” 我可憐的房東大娘,為了給孩子們買點好吃食……我沒說話,轉身出去,把門帶上。那房東大娘惶惶了兩天,見沒人追究,才稍稍安下心來。幾天後,我對那個知青說:“放好你的錢包,別亂扔。”
“怎麼了?”
.......
“我說呢,錢有點對不上。”
我說:“你不許找她。”會議結束了,聽說那個知青買了些點心,讓房東大娘帶回去給孩子們吃。
時間過得真快,一年的支農要結束了。兵團要留些人支援地方工作,領導找我談話,願不願留下來。我想自己年輕,沒有工作經驗,又學生氣太濃,說話直來直去,不適合留在地方。就跟領導說,我回兵團。那些留下來的人分在了集寧報社,集寧行政機關等處。我想,如果我留下來也會是個縣城的小幹部了;可我無意於此。
6連支農中唯一女戰友庫鐵軍(二排中)
支農回來,全連對參加支農的人呼聲很高。連裡安排我到五排擔任副排長,排長是張國英。一天,連黨支部組織委員趙醫生找我談話,問我對組織有什麼想法。換了別人會講,我現在做的很不夠,還希望組織上多多培養自己,爭取早日加入組織。可我這個人太過直率,脫口而出:“我沒想過。”弄得趙醫生很尷尬。趙醫生委婉的批評了我,當時自己卻不以為然。就是這種說話太直不講後果,得罪了人自己卻不覺得,為以後埋下隱患。日復一日的勞作又引動了我內心一直湧動的渴望,是什麼,我要什麼,我也說不清楚。直到有一天傳來訊息,大學要招生了。大家可以複習功課,參加考試。我一下子明白了,這就是我的期待,這就是我的希望。我很興奮,積極地準備著,考試那天大家去了團部,試卷發下來,答題。自我感覺不錯,該答的都答了,高二、高三的內容沒學過也答不出來。記得高二的一題是“銀鏡反應”,寫出化學反應的方程式,只知道這是道化學題,沒學過寫不出來。以後是各班各排推選上大學的人選,我過了全連推選的半數。排長張國英是大同兵團的,已結婚。孩子小家務事多。平時排裡的瑣事我都處理了,有時連裡開排長會我也大多替排長參加。這次研究上大學的名單,我心想,自己在研究名單之列,參加會議不合適。就讓排長去開會。原想自己有希望上學,沒想到會議結束,結果給我當頭一棒。雖然過了半數,可一些人認為我太想上學了,紮根邊疆思想不堅定,硬是把我刷下來!知道結果後,我半天說不出話。說我紮根邊疆思想不牢?當年支農我完全可以脫離兵團,留在地方,可我選擇了回兵團種地,這又怎麼講?我想上學,想學知識,提高自己這有錯嗎?
我找到當年帶領我們支農的團趙副政委,把心中的委屈、憤怒一股腦兒全傾倒出來。趙副政委對我的工作、能力是清楚的。此時,連裡推薦的三位名單已定。幾天後,團裡經過研究給六連又撥了一個名額,我才得以實現大學夢。
1973年我來到武漢大學。東湖之濱珞珈山上,是我親愛的學堂,這是我的希望、嚮往,這是我夢寐以求的地方。從乾涸的黃土荒原走進濃濃的綠原,我的心一下子被融化了。這裡有蔥蘢疊翠的珞珈山,有濤聲拍岸的東湖。秀麗的風景蘊滿了厚重深沉的文化。我徜徉在青山綠水,我內心愜意舒緩。
我全身心投入學習,緊張的課業,讓我感到壓力。空洞的大腦一下子擠進這麼多知識,頭都大了,一跳一跳的疼。每天教室、圖書館、食堂、宿舍。我努力適應著。
兵團廣闊天地造就了人的粗獷,一下子到了這麼秀美的環境還真有點不適應。,一天校領導看望新生,問有什麼問題嗎?我脫口而出:“吃不飽。”“吃不飽?”
在兵團裡每個人定量45斤,到武漢每月30斤,“每次打飯就那麼一點兒,太袖珍了!”周圍的人都笑了。
我努力著、奮進著、提高著。武大給了我知識,豐富了我的思想,使我心胸開闊,頭腦充實,讓我的思維有了新高度。在武大我擔任了系團總支副書記,加入了共產黨。一步一步地充實著自己。一天系黨總支書記黃訓騰對我說:“中央來函要求調查你上大學走後門的問題,經我們核查你不存在走後門的問題。青年學生之間的派性太嚴重了...”我沒有說話,心想我跟任何一方都無派無怨,我只是想讀書。望著天空,心中掠過一絲涼意。哦,我的兵團兄弟……
好在上蒼是知道我的,走在珞珈山的環山道上,鬱鬱蔥蔥,草木繁盛。使我忘記了俗世的喧囂,獲得心靈上的一份寧靜。
我感謝武大,給我知識,給我力量,給了我胸懷,給了我新的境界。幾年的兵團生活,刻骨銘心的艱苦磨礪,使我終生難忘。兵團生活是我認識社會的最初一課。我學到的知識不亞於當今的社會課堂。這是一種寶貴的經歷,這也是我大學的一部分。感激你我心中的大學——兵團!
本文作者
庫鐵軍 女 天津五中68屆高中生,1969年5月去內蒙古巴彥淖爾盟五原縣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第二師十五團六連屯墾戍邊。1971年到內蒙豐鎮地方支農,1973年進入武漢大學學習,1976年進入天津工業自動研究所工作至退休。
來源:兵團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