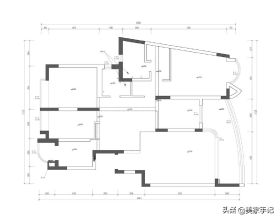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我的視線越過長江,直抵“落霞與孤鶩齊飛”的地方,然後進入長江的支流潦河。河水如一匹綢緞,稻田在周圍綠著,山巒畫出黛眉的斜線。
潦河環繞著靖安。陽光紫薇色的透徹中,我看到片片翠綠鮮嫩的葉子,那是桑。“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春秋之時,桑是宗廟的神木,早已進入先人的生活。
必是有一雙手,從葉片上摘取了柔軟的好奇。蠶與絲,催發了生活的靈感與生命的品質,使人類走過蒙昧中最美的樂段。而絲綢是女兒做的,因為絲綢,女兒才更嫵媚。
車子從靖永公路旁經過,看到一個圍起來的遺址。曾經,一萬噸的靜寂壓在上面。千年又千年地過去,沒有誰發現。後來,一個發現石破天驚。
一
李洲坳東邊的緩坡上,墓地的封土有12米厚,一點點剝離,發現了緊貼棺木的硬土,這是青膏泥。青膏泥上墊黃土,黃土經過夯打及火烤。所有的封土清理乾淨,墓坑赫然現出47個整齊的棺木。這是迄今發現時代最早的“一坑多棺”墓葬。
47個棺木中,46個都是女性骸骨,且年紀在15歲到25歲之間。在草木深深的芳香中,她們來不及細品,甚至來不及選擇一個秀枕,就姿態萬千地睡著了。
不知這些花,因何而謝。47具棺木是一次性埋下,棺中多有繞線框、梭、陶紡輪、漆勺,由此推斷這是墓主家的紡織女。
開啟30號棺,裡面放滿了花椒。“播芳椒兮成堂”,使用花椒是古人早有的習慣。花椒具有防腐除惡的功效,30號棺的文物由此儲存良好。
靖安有名的工匠蔡長遠就在挖掘現場,竹蓆從泥水中漸漸清晰的時候,他的眼睛亮了,這是怎樣的竹藝,圖案如此精美,還有刀形的小竹扇,也是如此細緻,二者皆可稱中華第一。他的竹雕上過央視,卻還是自嘆弗如。他去問其他手藝高超的篾匠,也都搖頭。隨葬品還有刀、削、鑿各類小型工具,難道竹蓆與竹扇出自這些女子之手?
接下來的震撼,是那些棺木,棺木都是整根杉木對半剖開,然後用工具掏空。主棺圓形榫卯套合最為複雜,那個橢圓就像草帽的橫截面。父親是縣上最好的木工,做過上千口棺材。蔡長遠去問父親。看到嚴絲合縫的弧形截面,老人也愣了,什麼工具什麼手藝能達到如此效果?
一個個問號和驚歎號還在出現。
我的目光投注在一片紗上,這是一件方孔紗。透過光譜測試,每平方釐米所用經線竟有280根,而每根線的直徑只有0.1毫米。由於染料加入了硃砂,織物仍色彩鮮豔。考古發掘史上,馬王堆漢墓的一件絲織物,經線密度才100多根,年代也比靖安古墓晚四五個世紀。我還看到了黑紅相間的幾何紋織錦、狩獵文織錦,都是那般精細縝密。古人的紡織技術,早就達到了匪夷所思的高度。
把無數根絲線變成一件錦繡,需要一個春夏的流盼,而把一個流盼變成一個驚豔,卻經歷了2500年。這些朱染錦緞的出現,直接改寫了中國乃至世界紡織史。
二
在江南,春秋時期墓葬極少發現。據DNA測定,這些被埋者與現在的靖安人,沒有任何脈繫上的連結。古時這裡是吳、越、楚三國交匯地。曾有一個徐國,一度是諸侯強國,後來沒落,繼而被吞併。究竟是什麼國度,什麼人,霎時間剝奪了女孩們的青春?
主人偏居一隅,屍骨蕩然無存,棺中只有一件龍紋圓形金器,身份並不確定。陪葬者不是妃嬪妻妾,也不是深宮環侍。有人猜測,這只是一個“紡織工坊”,更大的墓以及殉葬還沒有發掘出來。僅是猜測。
在這個春天,她們以另一種方式來到世上,她們曾鮮活滋潤,扎著髮帶的髮絲,依然閃著仙人般的光澤。
設想發掘者的心理,毛刷的每一次輕掃,仍然怕掃疼了她們。對於人生,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選擇,只是,她們不能。這或許,就是她們的宿命。
三
《詩經》的溱水裡,女孩們自由地嬉戲並追求所愛。
同樣是一個水草豐美的世界,天地遼闊的世界。我不知道她們會是怎樣的生活。潦河中,她們的臉龐及身段映進去,水中有了一群的豔麗。潦河的石頭很美,她們也許描摹過上邊的花紋。我敢說,她們曾盡情地享受過生命給她們的自在與歡快。
蠶的生命只有短暫的幾十天,貢獻的一顆繭卻可抽1000米絲。蠶絲本就具有高貴神秘的人文色彩。一根根蠶絲,從一片桑葉開始,將一顆心植入。女孩們語笑嫣然,採桑、養蠶、繅絲、編織。隨亂雲飛轉,伴光陰流逝。誰能想到,卻如蠶兒,復歸於絲麻。一群的燦爛,幽深中漸漸合閉。
藍色的雨在飄,還有藍色的電閃。桑發了綠芽,採桑的人卻一個都沒有出現。那是一個喑啞了的河畔。
遠處響起雷聲,雲飛得很低。當年的桑地早變成茶園。
我在園中望雨。雨如箭鏃,鏃鏃入土。黑瓷盞泡著白茶。白茶繚繞的碗底,竟然顯出釉光閃閃的一枚野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