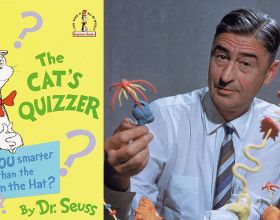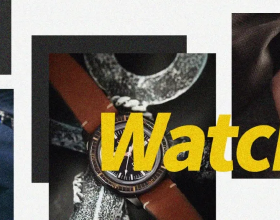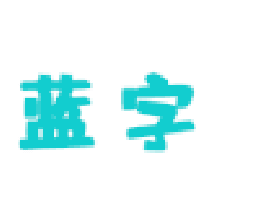作者:肖運錟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所在的13軍38師114團在重慶國防施工時,戰友範月富壯烈犧牲。我受部隊派遣,完成去城口安撫範月富烈士母親的任務後,又拖著重病回到了重慶北碚190部隊駐地的工作崗位,咬著牙關繼續堅持工作與訓練,並希望透過努力工作與訓練,忘卻傷病的痛苦,甚至寄希望於透過長時間的艱辛鍛鍊,能使身體自然康復。
誰知天不遂人願,事難逢美滿。不管我怎樣振作精神堅持工作,怎樣玩命地訓練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病情依舊一天比一天加重。在我部施工任務即將結束之際,我又被送到離軍部不遠的重慶大坪歇臺子第三十九陸軍醫院去治療。
經過醫院反覆檢查診斷,我在長壽紅衛化工廠搶險救災時被撞擊後,泌尿系統遺留下來的淤血,年長日久已經形成結石類的鈣化物。醫院先根據我個人的要求,先做了一段時間的保守治療,但幾乎毫無效果。後來在醫生的勸說下,我同意實施手術治療。但那時,醫院裝置簡陋,技術落後,藥物缺乏,主治醫生沒有經驗,我的手術很不成功。術後落得“去留存亡兩不堪,生非容易死亦難。可憐病骨如秋鶴,形容枯槁軍帽寬”的境地。
由於術後幾個月不斷地出血,反覆地感染,又被迫做了兩次修補性的手術。幾經折磨,我早已是瘦骨嶙峋、弱不禁風,最嚴重時,甚至連基本生活都無法自理了。記得第三次手術後,埋設了近20來天的引流管已經無法拔出,主治的周正華醫生說,只有再次手術才能取出。因為我對手術已經完全喪失信心,就堅決拒絕了再次手術的方案,提出採用硬性拔管的方法。但所有醫生和護士都說這樣太痛苦,而且具有造成新的重大損傷的風險。我想:自己反正都已經這樣了,寧可爛船把著爛船劃,再次承擔巨大痛苦和風險,也不接受再次手術。於是乎,醫生同意了我的選擇,我再次躺上了手術檯。
拔管那天,我的左右各站了一名身體強壯的護士,用力按住我的腹部,手術檯下端一方,一名護士緊緊地捏住引流管準備拔出,好幾個醫生站在我的周圍做好救護準備。當週正華醫生髮出拔管指令後,負責拔管的護士咬著牙,緊緊地閉上眼睛,搖了搖頭,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用力猛地一拔。只聽見“啪嗒”一聲,引流管從我的腹部猛地彈出,鮮血隨著引流管的彈出,噴灑了拔管護士一臉,連他身後雪白的牆壁上,也頓時怒放出了一團鮮紅鮮紅的“血蓮花”。只不過這朵“雪蓮花”飄逸出來的,不是醉人的芳香馥郁,而是濃濃的血腥味。病弱不堪的我居然沒有哼叫一聲,但很快就昏迷過去了。在場的醫生護士,無不為我這種頑強的意志力而感慨萬分!
當我醒來的時候,腹部像刀扎一樣疼痛,我咬緊牙關,一聲不吭,渾身的汗水直往外冒。科裡的劉護士長——一位40多歲慈眉善目的女軍人,從背後輕輕地扶起我的身軀,讓我的上半身靠著她。她一邊用溫暖柔和的手,反覆輕輕地撫摸著我的腹部,以緩解我的疼痛,一邊溫情地安慰我說:“孩子,痛就叫出來、哭出來吧,不要憋在肚子裡,那樣更難受,叫出來、哭出來會好受些。”我聽了後,兩行熱淚簌簌地流了下來。這不是因為痛,而是被她的溫暖所感動。她的關心和愛撫,她的體貼和安慰,有如和煦的春風,輕輕地撫慰著我傷痛的身軀與心靈。
或許在這世界上,只有母親才會給予的深情大愛,今天我卻從劉護士長身上真切地感受到了,我又怎麼能不感激涕零呢?一會兒,劉護士長又問我:“孩子,晚上想吃點什麼?”我使勁搖搖頭,表示不想吃任何東西。她又說:“那不行,一定得吃東西,不然怎麼恢復健康呢?廚房的糊糊面不好吃(因為我們每頓吃的都是這東西),也缺乏營養,等會兒我回家去給你煮碗雞蛋麵來。”
我急忙搖搖頭,輕聲地說:“別別別,我就吃廚房的糊糊面,謝謝您了!”但劉護士長卻不由分說,不一會兒就從家裡給我端來了一碗熱騰騰的雞蛋麵,並親手一口一口地餵我。我一邊吃,一邊流著感動的淚水。若干年以後,每當我聽到“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塊寶,投進媽媽的懷抱,幸福享不了”的歌聲時,眼前總會浮現出劉護士長這個像母親一樣溫馨的女軍人的形象,她就是我心中永遠崇敬的女神。
引流管拔掉之後,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解不出小便,小腹經常脹得像鼓一樣,疼痛難受得大汗淋漓,衣服被單一天換好幾次,都還是溼漉漉的,能擠出水來。科裡的護士小姑娘們,每天輪換著給我導尿和擦洗身子。因為自己從小信守“男女授受不親”的規矩,所以每當看到那些如花似玉、青春飛揚的女軍人給我導尿或擦洗身子時,就緊張得直冒冷汗,連說話也直打哆嗦。可這些還是姑娘的女軍人,總是那麼熱情大方、溫馨體貼、細緻入微地一邊為我導尿擦洗,一邊親切地和我拉家常,藉以消除我的恐懼與尷尬。
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裡,她們總是這樣不厭其煩、傾情關心、護理著我,最大限度地使我忘卻疾病帶來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困頓與迷茫。
“只因疾病呻吟切,識得平生第一心。”在這裡——三十九陸軍醫院,讓我真正感受到了高素質軍人之間那種高尚純潔、玉潔冰清的感情,這是那些世俗猥瑣、濁骨凡胎之徒永遠無法理解的懷瑾握瑜、高風峻節。但自此之後的幾十年間,雖然我也幾次進過醫院,經歷過更加兇險的病情,卻再也沒有遇見過像三十九陸軍醫院護理人員這種不是親人、勝似親人般的情感與服務。時至今日,我是多麼懷念那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時代和那些高尚純潔的白衣天使啊!
“八一”建軍節前夕,軍地首長來醫院看望慰問傷病員。一天下午,劉護士長通知我作為科裡的優秀傷病員代表,到醫院會議室參加慰問活動。我剛一落座,就看見我們的顧永武軍長和軍政治部主任坐在會議室上方正中的位置,兩邊還坐了一些不認識的軍地領導。我想,我們不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傷病員嗎,為什麼把慰問的規格搞得這麼高呢?但很快我就揣摩過來了:三十九陸軍醫院離軍部最近,而且住在這裡的,大多是軍直單位的傷病員,我不就是以軍部直管的成都軍區二十二工區傷病員的身份住進來的嗎?
正當我悶頭悶腦地獨自揣摩思量時,醫院院長站起來介紹各位軍地領導,接著又介紹靠近領導位置落座的幾個優秀傷病員代表。當院長要介紹到我時,顧軍長哈哈一笑,說:“不用介紹,不用介紹,這個小鬼我認識,他不就是敢於在北碚190營區內攔截軍區首長的那個大膽的兵嗎?看來我們今天是冤家路窄、又見面了啊!”
軍長剛說完,全場立即哈哈大笑起來。我尷尬地站了起來,在左右兩側的衣服上,慢慢地由上而下地擦擦手心的汗水,然後突然靈機一動,“啪”一個立正敬禮,高聲大氣地回敬道:“報告軍長,步兵114團1營營部戰士、成都軍區二十二工區北碚施工點危爆物品管理員、39陸軍醫院外科傷病員肖運錟向您報到,請指示!”立即以此把軍長踢給我的話題之“球”踢了回去,從被動地位贏得了話語上的主動權,全場又是一陣鬨堂大笑。
有了顧軍長導演的這麼一個別具風格的開場白,整個慰問活動一直籠罩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中。我也因為在北碚190部隊營區內“攔截”軍區首長的小小舉動,居然在軍長腦海裡留下了一絲痕跡而暗暗高興了好幾天。真是:
歲月輾轉似雲霞,時光流逝如落花。
禍福相依誰能料,悲歡交集綻奇葩。
【深耕戰爭史,弘揚正能量,歡迎投稿,私信必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