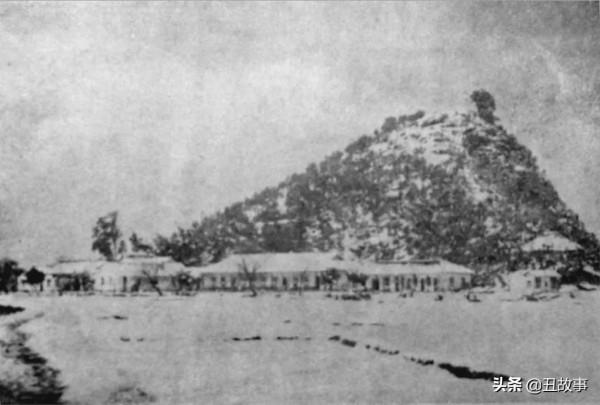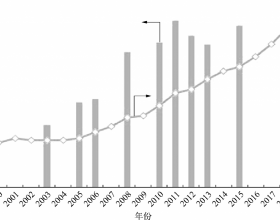郭學祥,1940年出生,浙江諸暨人。1959年畢業於湘湖師範學校,1961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
講述 郭學祥
主筆 牛牛
01 豆腐拿斧頭劈,豬肉拿鋸子鋸
加格達奇,在鄂倫春語中,意為“有樟子松的地方”。
如果沒有成為一名光榮的鐵道兵,我可能永遠不會去這個地方。
1964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三、六、九師進軍會戰大興安嶺。
1965年10月,我從鐵道兵學校(四川綿陽)畢業,回老部隊(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三師)報到。
我們四個學員從四川出發,坐火車到北京,再到齊齊哈爾。到齊齊哈爾後,還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車,才能到加格達奇。
祖國的北方已經白雪皚皚。
車窗的玻璃上,結著一層厚厚的冰花,冷氣不斷從外面透進來。
我穿著一件棉襖,外面再裹一件棉大衣。
衣服是軍校裡發的,在四川過冬肯定夠了。但在這裡,似乎和穿一件單衣沒什麼區別,還是凍得直打哆嗦,牙齒咯咯作響。
四個人擠在一起,互相取暖。
第二天早晨,太陽從樟子松的間隙中照射過來。
列車緩緩駛入加格達奇。
走出火車站,外面是一條黃褐色的土路,土塊已經凍得硬邦邦了。
道路兩旁,是一排排軍綠色的帳篷。整個城市,只能見到零星的幾座“建築”。
店裡賣的是凍梨、凍柿,豆腐是拿斧頭劈的,豬肉是拿鋸子鋸的。
幾個人來到師部招待所,在這裡休息一晚。
說是“招待所”,其實也是帳篷,左右兩排通鋪,一共能住八個人。工作人員幫忙點了煤爐,給我們取暖。
廁所是露天的,鋪兩塊木板,中間挖個坑。
排洩物已經凍成寶塔形了,越到上面越尖,邊上還擺著一根鋼釺。下一個人方便前,要先拿鋼釺把“寶塔”敲掉。
在招待所住了一夜,我們四個人到機械營營部報到。
營部邊上,剛好有一個連隊在搭帳篷。
看我們沒什麼事,他們就說:“你們來幫一下忙吧,剛到這裡,先熟悉熟悉。”
我們四個便去幫忙了。
我戴著一雙絨手套,鋼管拿在手裡,像握著一根冰棒。
手暴露在空氣中,不到五分鐘,就凍麻了。
我趕緊把手塞進棉衣裡,放在咯吱窩下面捂一會。等手恢復知覺了,再拿出來。幹一會兒,再捂一會兒,週而復始。
幹了兩個小時,帳篷終於搭完了。
回到室內,脫掉手套,手已經沒有血色了。
四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感覺心裡涼了半截。
我們滿腔熱情回到老部隊,沒想到,才來兩天,這裡惡劣的環境,就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不知道還有什麼困難等著我們。
02 一根毛竹打在下巴上,牙齒掉了4顆
我老家是諸暨浣東新東村的。
我們家五個兄弟姐妹,我是家裡的老么,上面還有一個哥哥,三個姐姐。
父親是中醫,每個月都要去諸暨店口坐診,一個月回來一次。
每次父親回家,都有不少人來家裡找父親看病。
遇到條件困難的,父親也不收錢,開個藥方子,讓他們自己去縣城抓藥。
母親走到哪都把我帶著,她教育我說:只有好好讀書,將來才能有出路。
1956年,我考上湘湖師範學校。
本來讀3年的,但“大鍊鋼鐵”開始,我提前畢業,進了蕭山鋼鐵廠當化驗員。
廠裡來動員參軍,我去報名登記,體檢也通過了。
等通知書發下來,我才回諸暨和家裡說。父母有些生氣,覺得沒和他們商量就去當兵了,但也沒阻攔。
母親只是說,出門在外,你自己各方面注意。
1961年7月,我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第三師11團1營3連。
部隊駐紮在江西南昌縣。
剛到部隊兩個星期,連隊就接到任務,去三江口背毛竹。
一人背一根,到目的地後,走在我前面的戰士,把毛竹往地上一丟。
沒想到,這根毛竹彈性很好,丟在地上,又彈了起來。
剛好打在我下巴上。
頓時鮮血直流,牙齒被打掉四顆。
我被送到江西九江171醫院,進行救治,鑲上了四顆假牙。
到部隊兩個星期就負傷了,對我是個不小的打擊。
1962年6月,我考上石家莊鐵道兵學院,學習“鐵道工程技術”。
後來,這個專業劃到了四川綿陽的鐵道兵學校,我又去四川繼續學習。
03 剛到工地,就聽說山體塌下來了
1964年,我和鐵道兵學校的同學們去“成昆鐵路”實習。津貼每人每月6元。
四川的山是綿延不斷的,幾乎找不到一處平坦的地方。
我們坐車從成都青龍場出發,前往樂山範店鎮。
部隊的運輸車,繞著盤山公路一圈圈地往上爬。好多學員都暈車,在車上吐了。
來到“大石板隧道”施工現場。
工地在半山腰上,一邊是崇山峻嶺,一邊是陡峭的山壁,往下一兩百米就是大渡河。
大渡河河水渾濁,波濤洶湧。
剛到工地我們就聽說,前段時間,成昆鐵路上出事了。
靠近雲南的一個隧道在施工的時候,山體塌下來了,犧牲了很多戰士。
上級要求我們,必須戴好安全帽,保證絕對安全。
我的工作是打風槍。前面一個戰士主要操作,我在後面輔助他。
隧道里灰塵很大,我們沒有口罩,只能拿一根水管接在風槍上,一邊打,一邊往洞裡灌水。
這樣打出來的灰塵就變成泥水了,風槍也不會發燙。
每天工作完走出隧道,一個個都是“泥人”了。
這裡的山體都是石頭,我們在隧道截面上,用風槍打出二三十個洞,再把炸藥塞進洞裡,進行爆破,把隧道一點點炸出來。
打孔的位置,和炸藥的用量,都有嚴格的講究,專門有人負責計算。
炸藥放多了,山就炸塌了,炸藥放少了,石頭又炸不開。
我們一天至少炸兩次,能推進一米,已經非常不錯了。
一千多米的隧道,就這樣一天天往前推。
當時,毛主席有一句話:“鐵路修不好,我睡不好覺,沒有錢,把我的工資拿出來,沒有路,騎毛驢去,沒有鐵軌,把沿海鐵路拆下來,一定要把成昆鐵路打通。”
我們的口號是:一定要把成昆鐵路修好,讓毛主席老人家睡好覺。
我們還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
住在當地的老百姓家裡,和他們一起下地種田,給他們挑糞,幫助他們提高生產,宣傳社會主義。
在老百姓家吃飯,要給伙食費,一天三毛錢。
老百姓吃的都是紅薯和稀粥,粥稀到什麼程度呢,就是一碗開水,加了幾顆米。
吃了一個禮拜,學員們就沒力氣幹活了,一個個餓的面黃肌瘦。
我們在“大石板隧道”實習了幾個月,隧道里風槍聲音很響,一天到晚“突突突”。
實習回來後,我耳朵不行了,別人說話聽不清楚。過了幾個月,才恢復聽力。
1965年10月,我從鐵道兵學校畢業,回老部隊三師。
此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三、六、九師已經進軍大興安嶺。
三師師部,就在大興安嶺的加格達奇。
04 連長踢踢我們,問有沒有活著的
到加格達奇的第四天,我被分配到3師機械營1連,當技術員。同行的三個學員,也都去了各自的連隊。
1968年開春,連隊接到任務,開往“西林吉”(現在漠河市的位置)
我和三十多個戰友,作為先頭部隊,提前去“西林吉”搭建營地。
天矇矇亮,我們就集合出發了。
運輸車行駛在林間公路上,凜冽的寒風呼嘯而過。兩旁是高大的樟子松,偶爾還能見到幾隻狍子和四不像,在林間停留。
這一路走了七八個小時。
趕到目的地,太陽已經下山了。
大家把東西一點點搬下車。
大興安嶺的晚上,因為有北極光,就算沒有月亮,也不會很黑,抬頭還能看到白雲。
東西搬完,我們用行軍鍋,煮了點高粱米吃。
連長說:“今天太遲了,大家先休息吧,明天我們再搭帳篷。”
此時的氣溫,已經零下四十多度了,我們要在雪地裡露天過夜。
我們找了一塊樹木不多的地方,簡單清理了下,把帳篷布平鋪在雪地上,再把各自的毛氈和墊被蓋在上面。
大家一個緊挨著一個,躺在墊被上。再找來所有能當被子的東西,蓋在身上,最上面用一層帳篷布罩住。
頭上戴著大頭帽,只留眼睛和鼻子在外面,其他都縮在被子裡。
也許是太累了吧,躺進去沒多久,我就睡著了。
再醒來,天已經亮了。
連長走到我邊上,用腳踢踢我,說:“還好,這個還活著。”
我搓了搓眼睛,醒了。
連長扯著嗓子喊:“你們有沒有凍死的啊,凍死的,起來說句話啊!”
大家躲在被子裡,一起喊:“都凍死了。”
從被子裡鑽出來,眉毛和睫毛上都掛著一層白霜。蓋在最上面的帳篷布,也鋪著一層厚厚的白霜,像下過小雪一樣。
大興安嶺的早晨,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松針的味道。
大家幹得熱火朝天,有的操作機器,平整場地,有的搭帳篷,擰螺絲。忙活了一天,一個小型的營地就建成了。
第二天,大部隊抵達後,順利駐紮下來。
05 挖下去,全是枯枝敗葉
修公路是我們機械連的主要任務之一。
大興安嶺的鐵路,都是公路修到哪裡,鐵路修到哪裡。只有把公路修好了,鐵軌才能運進去。
大興安嶺土質比較特殊,挖下去全是“腐殖土”。
所謂“腐殖土”,是樹木的枯枝殘葉經過長時期腐爛發酵後而形成。
這種土受力強度不夠,直接在上面修路,車開上去就塌陷了。
遇到這種情況,我們會操作機械,把腐殖土清理乾淨,再從取土場,運來比較乾燥的土鋪在上面,平整壓實。
但大興安嶺是原始森林,腐殖土實在太厚了,有些地方甚至超過一米。
為了按時完成任務,我們就地取材,把木頭並鋪在路上,再往上面蓋土,這樣就增加受力面積了。
部隊有規定,不能亂砍亂伐。
我們都找一些林業公司砍下來,堆在那裡沒用的,或者一些半死不活的樹木。
每修好一段,我們就要進行驗收,駕駛汽車在上面來回開。
有一次,我們修“嫩林線”(嫩江到林海),到馬尾山這個地方。
馬尾山一邊是甘河,一邊是山脈。
大興安嶺的山不高,都是小丘陵,但土質鬆軟,下面都是沙土,挖不了隧道。
我們只能從上往下,在山上挖了一道兩三百米長,三十多米深的口子。
我們管這種方法叫“大拉溝”,也叫“路塹”。
我們機械連操作推土機、鏟運機,挖了幾個月,才把“馬尾山大拉溝”的輪廓挖出來。後面交給線路連,由他們繼續施工。
還有一次,我們在“古蓮”修公路。施工的時候,正好是大興安嶺的夏天。
夏天最怕的是蚊蟲,大興安嶺的蚊蟲特別厲害,從早到晚都要戴防蚊帽。
太陽出來前,都是“蠓”。
蠓比蚊子要小,像一顆黑芝麻,也是吸血的。被蠓咬到,奇癢無比,還會起水泡。
太陽一出來,蠓就躲起來了,接下來是牛虻登場了。像轟炸機一樣,嗡嗡嗡地在空中盤旋。
等到下午,天氣涼快了,蚊子又出來上班。黑壓壓的一片,隨手在空中抓一下,都能抓到四五隻。
我們開玩笑說,大興安嶺的蟲子是“三班倒”的,但鐵路兵戰士是不休息的。
06 兩次命懸一線,死裡逃生
1973年,營部需要土木工程師,就把我從連隊調過去了。
營部就不用睡帳篷了,是住在房屋裡的,屋裡還有“地火龍”。
“地火龍”是大興安嶺的鐵道兵發明的。
用磚和泥壘起的煙道,在床鋪下面繞行,煙道一頭連著火爐,另一頭連到屋外,作為煙囪排煙。
火爐燒起來後,整個通道就像一條火龍,均勻、持久地散發著熱量。外面天寒地凍,屋內能達到20多度。
這裡叫龍頭山,離加格達奇18公里,身後的房子就是營部
我住的這幢房子裡,有五個小房間,我們五個技術人員住在這裡。
有一天早上,起床號響了,戰士們都出早操了。
我們技術人員,也要和大家一起出早操。我聽到起床號聲音,但感覺渾身沒力,怎麼都起不來,很想睡。
迷迷糊糊又睡著了。
通訊班班長很奇怪,今天技術組的人,怎麼還沒出來?
他跑過來敲門,敲了很久沒人開。
一腳就把門踹開了。衝進來一看,裡面全是煙,我們五個人都癱在床上,一動不動,怎麼叫我們都沒有反應。
班長趕緊又叫來幾個戰士,把我們抬了出去。
五個人被抬到廣場上,褲子都溼了,小便失禁了。
營部馬上向師部彙報情況。一個小時不到,醫療隊就趕來了,給我們檢查身體。
醫療隊的醫生說,要是再晚十分鐘,這五個人就沒了。
醫生讓我們在操場上走路,繞圈圈,呼吸新鮮空氣。圍著操場走了一個上午,我們幾個才算緩過來。
後來知道,是地火龍的煙囪堵住了,煙排不出去,就滲到房間裡來了。
多虧通訊班班長當機立斷,不然五個人就沒了。
還有一次,我和幾位技術人員,去連隊指導工作。
連隊駐紮在額木爾河邊。連隊的戰士告訴我們說,部隊在上游捕魚。
額木爾河有一種細鱗魚,在滿清時是上供的,慈禧太后稱其為“龍鳳之肉”。
在大興安嶺,我們頓頓吃土豆和大白菜,一天兩頓高粱米,星期日才有大米飯,更不要說豬肉和魚肉了。
他這麼一說,大家口水都下來了。
跑到額木爾河邊,河面已經凍上了,冰層下水還在流動。我跑到河中央,拿鐵鍬在冰面上鑿開一個窟窿。
就看見魚一條接著一條,從冰層下飄過來,場面非常壯觀。
這種魚木木的,有人在上面也不怕。過來一條,我撈一條,很快就撿了一籮筐。
看差不多了,我就想回岸邊了。
沒想到,剛走幾步路,“咔嚓”一聲,冰層裂開了。
我一下子掉進了冰水裡。
冰水從我棉褲的褲腿裡,一點點往上鑽,很快就鑽到了我的胸口。不到幾秒,全身都被冰水浸透了。
我雙手扒著冰面,但衣服太重了,根本爬不上去。
岸邊的戰友,看到我落水了,馬上拿著樹枝把我救了上來。
我脫掉溼透的衣服,戰友們又一人脫下一件,給我穿上。
中午,我們在連隊吃飯,炊事班燒了一大盆紅燒魚塊,都是早上撈來的。看著鍋裡魚,我有點哭笑不得。
07 車子發生了側翻,朝戰友身上壓去
1975年1月20日,剛剛下過一場大雪,營部斷糧了。
營部的管理員戴榮舫,和駕駛員一起去買糧食。
營部在龍頭山,離加格達奇18公里。買糧食的地方,在大楊樹方向,開車來回得一天時間。
大清早,他們就開著“嘎斯車”出發了。
但不到兩個小時,車子就回來了。
駕駛員停好車,跑下來說:“出事了,出事了。”
我們跑過去一看,戴榮舫癱在副駕駛座上,一動不動。
駕駛員說,他們開出30多公里,到了一個下坡。沒想到前幾日雪下得太大,把路都堵上了,他連忙緊急剎車。
結果車子打滑,發生了側翻。
車上沒有安全帶,戴榮舫當場被甩了出去,側翻的車子剛好砸在戴榮舫身上。
戰友們把戴榮舫抬下車,平放在辦公室的桌子上。
我摸了摸他的手,還是有溫度的,但人已經沒氣了。
師部的衛生隊趕來了,搶救了一個多小時,還是沒能救回來。
戴榮舫為人不錯,工作負責。他是管理員,營部的吃喝拉撒,他都很勞心的,不管是打掃衛生,還是組織會議,他都衝在最前面。
這麼熱心的人,一下子就沒了,大家都挺難過的。
出事的第三天,戴榮舫的家人來了。他們從湖北出發,坐火車趕到加格達奇。
遺體還躺在辦公室裡,部隊的領導也趕來了。
房間裡氣氛很沉重,戴榮舫愛人,還有他的三個孩子,大兒子8歲,二女兒6歲,小女兒才2歲。
他愛人抱著三個孩子,哭成了淚人。
戴榮舫的岳父也來了,他是個老革命,站在一邊安慰女兒說:“他是為革命犧牲的,不要傷心了,部隊裡總會有犧牲的。”
戴榮舫被安葬在加格達奇北山的烈士陵園。
我和王衛生員一起,送戴榮舫的家屬回老家,湖北天門嶽口鎮。
看著車窗外的景色,從一望無際的白色,變得色彩豐富起來。到了武漢,我們坐輪船過漢江,江水波光閃爍,奔流不息。
我和王衛生員在湖北住了一個月,幫戴榮舫辦好了烈士證和撫卹金,還給他愛人安排好工作。
臨別的時候,戴榮舫的愛人,帶著三個孩子來送我們。
我心情很複雜,只能反覆說:保重,有困難找政府,有困難找政府。
大概七年前吧,我在“鐵道兵吧”上看到,戴榮舫的女兒戴紅梅,在網上發帖。
戴紅梅說,想找到爸爸當年的老同事,瞭解一下爸爸的事情。她列了幾個名字,其中一個是“郭工程師”,就是我。
我給她留言:我就是你要找的郭工,當年我送你們一家人回湖北,你還是個小孩子……你們現在還好嗎?
訊息發出去,可惜一直沒有回應。
08 一個解不開的結
1977年4月,加格達奇依舊寒風凜冽。
我即將離開加格達奇,從部隊復員。在部隊生活了17年,過慣了集體生活,有太多的捨不得,放不下。
戰友們把我送到加格達奇火車站。
列車駛出加格達奇,窗外的風景一幕幕閃過,眼睛不自覺溼潤了。
回到杭州,老單位蕭山鋼鐵廠已經沒有了,我進了杭發廠,在二車間當一名工人。後來又當車間副書記,書記。
1991年,我去了杭發技工學校,當校長,支部書記。一直幹到2000年,在杭發廠光榮退休。
愛人在蕭山膠木廠工作,後來又調到鐘錶機械廠。
我和愛人1968年結婚,那時我還是鐵道兵,她是一名小學老師。
我們一年只能見一次面,就是我的探親假,20天。
我們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
孩子出生後,一直由我愛人照顧,她非常不容易,將兩個孩子拉扯大。
2019年,女兒和幾個朋友去東北玩,去加格達奇,想帶我一起去。
離開這麼多年了,我非常想念那裡,可惜因身體原因,最後未能成行。
女兒到加格達奇後,拍了許多照片發給我。
加格達奇變化很大,帳篷沒有了,街道比以前寬敞了,高樓大廈都建起來了。
加格達奇北山上,“鐵道兵紀念碑”聳立在萬綠叢中。碑前還有一隻馬鹿雕塑。
馬鹿是大興安嶺林區特有的動物種類,置於主碑前面,象徵著大興安嶺地區各族人民對鐵道兵部隊開發大興安嶺時的大力援助。
主碑是兩根放大的鋼軌,中間鑲嵌著鐵道兵兵徽,像一個解不開的結。
鐵道兵紀念碑碑文記載:
1964年,遵照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三、六、九師8萬官兵進軍會戰大興安嶺。
廣大指戰員在舉世罕見的“高寒禁區”爬冰臥雪、宿露餐風、英勇開拓、頑強拼搏,在林區各族人民支援下,到1983年底,共修建鐵路792公里,橋樑124座,隧道14座,為開發林區,建設邊疆做出了重大貢獻。
為銘記他們的光輝業績,緬懷英勇獻身的烈士,特立此碑。
牛牛說:鐵道兵精神永存
一個夏日的早晨,我坐地鐵來到蕭山潘水站。
走進小區,沿著樹蔭一直往裡走,一幢獨棟的樓房,上到三樓。郭叔已經側著身子,在門邊等待了。
郭叔說,你就是牛牛吧,歡迎歡迎。
郭叔的愛人出門了,家裡只有郭叔一人。
我注意到,房間裡擺著不少榮譽證明,其中就包括郭叔和他愛人的“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郭叔說,這是前段時間發下來的。
茶几上,還有一張白紙,白紙上擺著許多老照片。原來是,郭叔知道我今天要來採訪,已經把照片找出來了。
我問郭叔,平時有什麼興趣愛好?
郭叔說,他最近在學習強國,學習很努力,已經達到支部的第三名了。說完,郭叔拿出手機,向我展示了“積分排行榜”。
郭叔今年已經81歲,但說話中氣很足,還時不時來幾句諸暨話。
郭叔說,他從部隊回來,已經在蕭山生活了四十多年了,還是改不了老家口音。
回憶起鐵道兵往事。
郭叔說,離開部隊多年,再沒見過老戰友,但心裡一直掛念著部隊,希望透過講故事這種方式,向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致敬,向老部隊和老戰友表示懷念。
講到挖隧道時,郭叔說,他們當年是靠打風槍,放炸藥,一點點往前推的,一天最多挖一兩米,不像現在有盾構機,一個月挖幾百米。
聽到這個數字,我有些震驚。
一千多米長的隧道,就靠鐵道兵們一天一米地前推,硬生生鑿出一條通路。
當年的艱辛,可想而知。
鐵道兵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解放戰爭時期。
1945年8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在東北組建了一支武裝護路隊伍,後改為東北民主聯軍護路軍。
1953年9月9日,中央軍委決定組建鐵道兵領導機關,鐵道兵正式作為一個兵種進入人民解放軍序列。
1954年3月5日,鐵道兵司令部正式在北京成立,最多時鐵道兵總兵力達40餘萬人。
先後修建了鷹廈鐵路、成昆鐵路、貴昆鐵路、襄渝鐵路、東北林區鐵路、新疆南疆鐵路、青藏鐵路和北京地鐵工程等大型鐵路,立下了汗馬功勞。
直到1982年4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通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撤銷鐵道兵建制,把鐵道兵併入鐵道部。”
12月6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正式下達了關於鐵道兵併入鐵道部的決定。
鐵道兵在解放軍序列中消失,但鐵道兵的功績,卻永遠留在解放軍的史冊上。
如今,中國已擁有世界上最現代化的鐵路網和最發達的高鐵網。正是這些先輩們的無私奉獻,才換來了今天的繁榮昌盛。
向中國鐵道兵致敬,鐵道兵精神永存!
願山河錦繡,國泰民安。
-END-
親愛的讀者,覺得文章好看,歡迎關注醜故事,看更多精彩的生命成長故事。
本文為醜故事首發,未經許可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