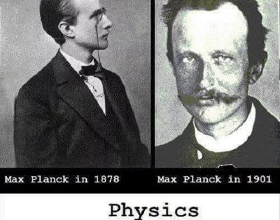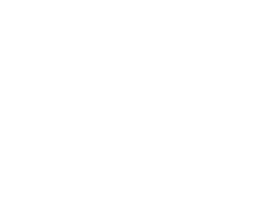有人問我,陳大爺不見了,你報警之後咋不接著往下說?其實我是覺著真沒啥好說的。胡支書報完警,當天晚上鎮上派出所來人做了筆錄。隔兩天又來了幾輛外地牌照的車和一輛軍車,把石夫人頂上給封起來了,全村人都被叫去問話。除了山頂不讓村民去了之外,生活沒有任何變化。至於到底發生了啥,陳大爺究竟去沒去石夫人,是不是像小濤說的被UFO劫走了,沒人知道。你們可別看我嘴上說的是雲淡風輕,在我心裡邊這事是個坎。到底陳大爺發生了啥事,到底有沒有個透明三角形停在半空,我比誰都想弄明白。
這回我主要想說說殺豬的事情。這行我幹了也十多年了,熟門熟路。抓著豬四腳綁好仰放在臺子上把豬頭掛出來,摸著脖子連身體那地方,用力一刀捅進去轉個半圈,然後拔出來等血放幹。刀要長,一刀進去夠不著捅不破心臟的話那可就麻煩了。幹熟練了之後也就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事兒,跟平常單位裡上班摸魚看報紙其實沒啥本質的區別。除了一件事情,準確的來說,是一頭豬。讓我記憶猶新,如鯁在喉,不說出來不痛快。
三年前村裡不給養豬了,也不讓農戶自己殺。鎮上有個屠宰場,農戶自家養的最後一批豬都一起運過去殺了。這時胡廣來,我們都叫他“胡來”,包下了屠宰場,又在屠宰場附近靠山這塊圈了幾百畝的一大塊地,辦起了養豬場。胡來是鎮上唯一一個把養豬的八本資質證書全辦下的人,這錢只能還得他賺。
說起胡來,年齡比我小點兒,村支書兒子。去外國留過學待過幾年,回來吃的開,人面廣。他辦養豬場我是出了分力的,選地建豬舍買裝置飼料我都提了意見,畢竟這活我熟。他也沒虧待我,讓我把屠宰資格證考了,去他那上班。我說資格證我有,上班就算了。村裡賣肉習慣了,坐廠裡辦公室不舒心,再說我去他那上班了,全村人就沒地兒買肉了。於是他就給我配了輛金盃車,說村裡人喜歡吃農家自養的豬。他有一批兩頭烏,是準備在山裡放養的。到時我就去鎮上連殺帶宰,把肉運回村子裡賣,價格算我便宜,當他的分銷商。我一聽這活計好,趕緊答應了。
有人說我太囉嗦,前面鋪墊太長,就是不說發生了啥。凡事都講究個前因後果,不把起因給介紹了,這原本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來龍去脈的事,到了聽的人那豈不更是一頭霧水了?也有的人說我說的不夠詳細,很多地方一筆帶過。怎麼,要不從三年前的一天我愁眉苦臉躺在床上琢磨小濤的學費咋辦的時候說起:
我正愁著呢,電話響了。我沒接,心裡只想著不能殺豬了以後該怎麼找錢。電話又響了一遍,我被煩得慌便接了起來,粗聲粗氣問:“誰啊?”電話那頭傳來一把渾厚低沉的男聲,不帶任何口音的說:“富貴哥,是我,胡來。你能不能到鎮上來一趟?我想在屠宰場後邊再建個養豬場,我爸說這事兒得跟你商量商量。”
要是這樣說,光建豬場的事我都能說上個十天八夜的,我自己都覺得累。養豬那八本證書怎麼批,豬場怎麼建,裝置怎麼買,飼料怎麼選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豬場建好之後,我又去了鎮上一趟。一來是參觀參觀,二來是拿上那輛已經改裝了貨架的金盃車。
那天天氣非常好,一片透明的藍天上點綴著幾塊稀碎的雲。空氣純淨,視野開闊。我遠遠就望見胡來穿了條迷彩工裝褲,上身套了件深藍色牛仔,帶了幾個人,在養豬場門口等。邊上是白圍牆,看不出圍了多大一圈,只知道很大。中間一個大鐵門,門上面做了個拱橋型的燈箱,五個大字寫著廣來養豬廠。胡來見我到了,扔掉手裡的菸頭,招呼人去把我腳踏車停了,便親熱的摟著我的肩,帶我進去參觀。
進了養豬場大門,在值班室裡登了記,胡來領著我進到一個更衣消毒室。等我套上一件連體工作服出來,門口就是一條新修的大約有三個車道寬的水泥路。我對胡來說:“胡來,你這衛生標準是跟國際接軌了吧?”
胡來咧開了嘴,“那必須,要做就得做最好的。況且你說了,衛生標準越高,得病率越低,產仔存活率也越高啊。”他指著水泥路右手邊說:“這邊全是高密度豬舍。按你的建議,公母豬、產仔保育、育肥都分開了。型別我選了全封閉式,除了貴沒別的毛病。豬也聽你的進了批英國pic的五元豬,目前母豬存量有五百頭。”
看著這一片豬舍,我心裡合計這投資應該要在兩千萬以上了,邊感嘆邊嘴上不忘對他的員工吹噓,“英國pic好啊,省飼料,發育快,5個月就能到200多斤。現在豬肉貴,儘量往大了養,越大飼料轉換率越高。豬舍跟豬舍中間最好再種點果樹、綠植啥的,平時淨化空氣,夏天可以遮陽。”
胡來讓人把種樹這事記下,便帶著點神秘兮兮的興奮拉著我的手,往左邊一條道走去,說:“來,給你看好東西。”
我一看道路盡頭那山坡底下一排大平房就知道,這肯定就是放養的豬舍了。我們穿過圍欄進到裡面,我卻發現設施完備,地方卻空曠的很——空曠到裡面一隻豬都沒有。
胡來看出我眼中的疑問,哈哈大笑,向身後招招手,馬上有員工遞上一臺膝上型電腦。胡來開啟指著螢幕上的那些凌亂的紅點問我,“你猜猜,這是啥?”
“不是吧!胡來,你在每頭豬身上都裝了定位?”
胡來從口袋裡掏出一個指甲蓋那麼大的黑色小方塊,上面連著一根長的天線。我拿在手裡掂量了一下,很輕,幾乎感覺不到重量。胡來抓著天線,折彎成一個橢圓形狀連在了方塊上。我才發現那根本不是天線,是固定這個方塊用的綁帶。
“這東西裝豬身上哪兒?”我問。
胡來指指我的耳朵,示意我把方塊貼到耳後的位置。
一陣優美的鋼琴旋律在我腦中響起。
“這是帶GPS定位的骨傳導耳機。你現在聽到的是莫扎特的D大調雙鋼琴奏鳴曲。”
“音樂我是一竅不通,給豬聽這玩意兒?”
“對,從和牛養殖方法中學的。別人有音樂牛,以後我就賣音樂豬。”
“每頭豬都配這,那得多少錢?”
胡來又神秘的眨眨眼,他生來嚴肅的國字臉上便有了種給人滑稽的感覺,但是聲音還是一如既往的低沉,“不要錢,只要儲存資料就行。我以前唸書時的導師給我申請的,這產品在美國也是測試階段,連山上發射訊號的基站都不用我掏錢。”
“有了這東西,我就不用在山上再弄圍欄圈地了。在電腦裡發個指令,豬就能自己回欄。”胡來轉身對他的員工說,“大山,加料時間快到了,你們先去把食槽填上。”然後拍拍我的肩膀說:“我們回外邊兒。”
等大山他們幾個人加完飼料出來,胡來讓我把耳機又貼在耳朵後邊,在膝上型電腦上一陣搗鼓。耳機裡沒有傳來任何聲音。可能是心理反應,我隱約感覺到了一陣細微的震動。
“沒聲音啊胡來。”
“哈哈,沒聲音就對了。豬能聽到的聲波頻率能高到4萬赫,比人多兩萬呢。這些指令都只有豬才能聽見。”
邊說著,螢幕上凌亂的紅點紛紛動了起來,向豬舍形狀的方塊快速移動。不一會,山上就跑下來一群豬,數量有一百來只,有大有小,白白的身子,只有頭和屁股尾巴是黑的,圓圓的甚是可愛。豬們一溜煙跑到食槽邊歡快的進食,瞬時間豬聲鼎沸。
“這批是金華的名豬——兩頭烏。肉好吃,也能加工火腿。白天全放山裡散養,讓它們自己在山上刨點吃食,傍晚回來加一次飼料。每天聽兩回音樂,絕對有噱頭。”
我把耳機遞還給胡來,一眼瞥到那白白黑黑的一群兩頭烏中間,夾雜著一個全黑的豬影,個不大,按豬的標準來說有點瘦弱。在食槽最邊上小心的吃著飼料,偶爾還被邊上的豬擠的摔在地上,爬起來抖抖腿又繼續吃。
“咦,這裡面怎麼還有頭東北大民?就一隻?”
“是啊,送貨的時候弄錯了,混裡面了,將就養著吧。”
“好像受了排擠,腿都有點瘸了。”
“來的時候是不瘸。不用管它,大了就殺,後面也不會有東北民豬了。時候不早了,我們一塊去喝個小酒?”
“不了,小濤升了高中,在鎮上上學呢。我拿了車順便接他回村。”
“那行,過倆月你再來,挑只最大的殺了,拿回村裡分掉。當是第一批音樂豬的廣告,也算是回報鄉親們的福利了。”
離開的時候,我目光停留在了一隻豬上。那隻豬聽著胡來和我的聊天,停止了進食。仰起頭,彷彿在盯著我看。眼圈一週都是白的,像是反了個色的大熊貓。就叫它白眼吧,這頭長相與眾不同的豬,看了看我,又轉頭看了看那頭全黑的東北民豬,晃了晃腦袋,也不吃食,就這樣目送著我和胡來一行人離開。
回村路上,開著胡來給我配的金盃車,不,應該稱它為分銷商專用車。生計問題眼看著就能解決,我整個人都輕鬆了許多。小濤似乎也感受到了我內心的喜悅,雀躍的跟我分享他在高中的見聞。
“爸,我同桌叫李勝。他跟我說,pi,就是圓周率,包含了整個宇宙的秘密。”他說著說著手舞足蹈了起來,“在小數點後那數都數不清的數列裡,你能找到你的身份證號碼、電話號碼。如果轉換成二進位制,你甚至能在這無窮的數列裡找到你的一生,你身邊的一切。整個宇宙從誕生到現在所有發生過的事情,都隱藏在裡邊。科學家已經在數列裡發現了氫原子方程的沃利斯公式呢!”
“你坐著好好說,別拉我手,我在開車!”
“爸,李勝說,他要把圓周率背下來,一直背到人類的極限。說如果背成了,他就能掌握宇宙的真理了。”
“他是吃飽了撐的,計算器能算的玩意兒背它幹啥。”
“我也想背。李勝說,有個日本人叫原口證,能背到小數點後10萬位。”
“那他掌握宇宙的真理了嗎?”
“我和李勝都覺得10萬位還沒到極限。可能突破人類的極限時就懂了。”
“你們這是悟道都來了。得,只要不影響分數,你愛幹啥幹啥。”
重複而又單調的日子便在我去鎮上進貨(五元豬成長期很快)和回村擺攤中度過。那段日子陳大爺還沒到處跟人喊宇宙大爆炸和放電影的事,除了織布繡花就是坐在裁縫鋪門口,抽著旱菸發著呆當我鄰居。我空閒時也會跟他嘮幾句家常。
兩個月很快過去,有天傍晚我又去了回廣來養豬場。現在再去早已是熟門熟路了,登記完換好工作服,我直接去放養豬舍外面找到胡來。胡來正在指揮員工們清掃豬舍,充填飼料,見我來了,便遞給我一根菸。
“效益怎麼樣?”我問他。
“非常好,非常好。就等這批音樂豬上市打響品牌了。你兒子上高中了成績怎麼樣?”
“班裡中上游吧,最近發了瘋,整天和他一同學混在一起背圓周率。”
“叛逆期嘛,都這樣。”
“這兩個月跟你進貨的肉錢是不是得跟你算算了,老是拿肉不給錢不是個事兒。”
“不急不急,等音樂豬品牌打出來再說。我不催你你就別急,安心賣著。”
一支菸的時間過去,大山他們都忙完出來了。胡來又拿起膝上型電腦給山上的豬們傳送了指令。不一會,豬們便聚集在食槽前。
“大山,去把食槽邊上的圍欄圈起來,等會好抓。富貴哥,你看看,相中哪頭?”
“你挑吧,你給村裡請客,我可做不了主。”這時我的眼光又撇到了那隻削瘦又帶點瘸的黑色豬影,還是在食槽最邊緣的地方小心翼翼的吃著。我感慨說:“那隻東北大民,都沒怎麼長肉啊。”
胡來似乎沒聽見,指著中間一隻體型最大,毛色發亮的兩頭烏說:“就那隻吧,看著有200多斤了。”說著抓起套杆,丟給大山他們。大山很輕鬆的就把最大的那隻兩頭烏勾了過來,跟幾個人一起把它按到在地,開始用繩綁住四肢。那豬發出一陣悲鳴,卻被淹沒在群豬吃食的鼎沸聲之中。這時我視線一掃,又看到在一群低頭搶食的豬中間,有隻豬停止了吃食,仰起頭。是白眼,眼周一圈白色特顯眼。它看著大山他們在綁那頭豬,打了個響鼻,又晃了晃腦袋,轉頭盯著我跟胡來。在那個瞬間我好像看到它露出了一個像人的表情,嘴巴微微往上斜,露出了一排牙齒。
這時大山幾個人已經麻利的把豬綁好,抬上了皮卡。胡來開車,帶我沿著山腳開了幾公里,拐了個彎,到了屠宰場。
“這音樂豬我都不讓用電。電暈了再放血放不乾淨,還是人宰的肉質更好。”胡來對我說。
“我來。”
那頭大豬在平臺上掙扎著,似乎想掙脫大山他們的壓制。我摸著脖子根上的位置,準備一刀捅進。這時我腦袋裡突然閃過白眼盯著我的那個笑容。它在笑什麼?是自己終會成為盤中餐的命運,還是在嘲笑人類的殘忍?
“哎呀,不夠深。心臟沒破,血亂濺了。”胡來叫喊的聲響和大豬臨死掙扎的嚎叫把我拉回了現實,趕緊把刀拔出來,又照準原位置全力一刀捅進轉了半圈,了結了大豬的性命。
“沒事吧?一副心神不寧的樣子。”說著,胡來遞給我一塊毛巾。
我一邊擦手,一邊把白眼盯著我的那副笑容從腦袋裡甩掉,說:“沒事,就是突然有點走神。”
音樂豬在村裡的評價非常好。肥而不膩,瘦而不柴,鮮美多汁,質嫩爽口,所有能評價肉的褒義詞都能套到上面。胡支書臉上也洋溢著喜氣,人人都誇他有個能幹註定要發財的兒子。我的攤子上也撤了商品豬的肉,只賣廣來牌音樂豬。因為胡來給我的價格很便宜,所以我賣價也不比商品豬高多少,生意很是火爆。
又過了倆月,隔壁的裁縫鋪蔡大娘找上我,說孃家的一個後生結婚要擺席,讓我去挑頭音樂豬殺了帶回來。
這回去廠裡,胡來不在。矮個子大山接待的我。用電腦把豬招回欄之後,大山指著一隻豬跟我說:“就那隻吧。最近它長的最快。”我一看,是那頭全黑帶點瘸的東北民豬。奇怪了,這豬上次還那麼瘦,怎麼突然長這麼肥了。我點點頭,大山便讓員工們開始套那頭黑豬。這時我突然看到電腦螢幕上豬舍外邊還有個紅點在慢慢的接近。
“等下,這怎麼還有頭豬在外邊?”
“興許是山上吃太多,慢悠悠晃回來的。”
這時螢幕上紅點已經到了豬舍裡邊,我往那個方向一看,白眼正站在食槽的圍欄外看著我。隔著柵欄我都能看見它臉上又露出了和上次那個一摸一樣的笑容,嘴巴微微上斜,露出一排牙齒。像是在嘲笑我奈何不了它。
“等下。”不知為什麼,我瞬間變了念頭,喊停員工們綁大黑豬的進度,抓起套杆每人發了一個。“先把食槽外的那隻抓了,那隻更大。”
白眼看到我們幾個人人手一個套杆朝著食槽外邊過去,一個支稜,眼神中露出了恐懼,打了個響鼻嗷嗷叫著往上山的方向跑。無奈上山的路早已被攔起,便叫喊著在豬舍四處亂竄。
我和大山他們東追西趕,終於把白眼一頭套住,往食槽方向拖。準備拿繩索綁了丟上皮卡。白眼一路盯著我,一路狂叫,在靠近食槽的時候突然做出仰天狂吼的姿態,但是沒發出任何聲音。我隱約感覺耳朵微微震動,便回頭一看,食槽欄裡的所有二頭烏都停下了吃食,轉頭往我們幾人這裡飛奔過來。
一百多頭接近兩百斤的豬,發了瘋似的衝破圍欄,嘶叫著筆直朝我們衝過來。大山趕緊拉著我往邊上閃,大叫:“閃開,都閃開!”其中有個員工乍見這種離奇的情景,一驚之下,腿一軟,直接癱坐在了地上。豬群直接繞過,理都沒理他,跑到白眼處,開始瘋狂撕咬白眼。一支菸時間不到的功夫,地上全是碎肢爛肉。白眼被豬群活生生的吃了!
我當時渾身雞皮疙瘩豎的都快炸了。白眼到死都在盯著我看。在豬群瘋狂又雜亂的身影和步伐中間,一直有一道帶著仇恨的目光從重重豬影中透出來,聚停在我身上。彷彿那種仇恨是實質性的鞭子,一鞭又一鞭的抽打在我身上。我感受到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震驚和做夢都沒想到過的詭異場景帶來的壓力,渾身溼透。
豬群終於安靜了下來,分散開退回了豬舍,彷彿無事發生過一般,倒地便睡。我和大山強打精神,把撞掉的圍欄裝了回去。大山看著滿地的殘渣和被綁到一半的大黑豬,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只是用眼神在詢問我該怎麼辦。
“把這隻黑豬綁了運去殺了吧,我帶回去。”我有點無助的說,“這事我會跟胡來彙報,損失我擔。”
我心事重重無精打采心不在焉的回到了村裡,也不管小濤是不是和李勝在客廳一個勁的揹著圓周率,跑進廚房坐下狂灌了許多酒,便躺到床上睡。
那天晚上,我做了個夢。
我第一回夢見我那不見了十二年的媳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