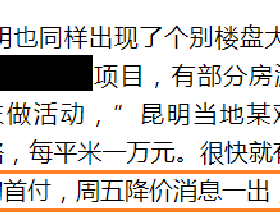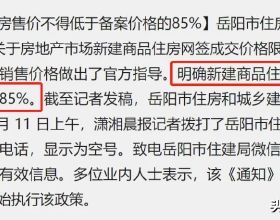又是一個柿黃時節。村子下面的丹水河,一幅波瀾不驚樣子,挽著山,襯著橋,專心一意地向南走。橋被陽光刷得金亮,象個“人”字。
李老漢去羊圈趕羊。兩隻綿羊——老白和小白就隔著圈門哞哞地叫,聲音有點賤。它們不會象黑山羊——大黑那樣很響地“噗”一聲,象個“爸”,只是愁腸滿結地叫“媽——媽”。李老漢不喜歡這種婆婆媽媽的嗲氣。他喜歡大黑的一臉沉思樣子,那不事張揚的性情。只是在不經意間,聽它很響地“噗”一聲“爸”,短促而優雅,讓他從頭到腳地滿足。
他趕著他的羊隊伍——不。準確地說是老白、小白和大黑,從村口走下路,村主任滿娃和會計小發在臨著大路的村口立著。滿娃兩手插在褲兜,叉著腿,褲腰帶撐著肚子有些費力。不到三十幾的年齡竟歇了頂,象個燈泡。小發的腳踢著路邊的石頭。這邊踢過來,那邊踢過去。
滿娃說:“李叔,放羊了?”
李老漢說:“嗯。你們幹嘛呢?”
“等人。縣裡要來人。說是咱村的地給人包了,按人頭給糧給補貼。”滿娃很有興致地說,象給村裡辦著一件大好事。
李老漢問:“那村裡人幹啥?”李老漢想不通村裡人沒有了地會是什麼情形。
“就象城裡人。平時出工,植樹、護林、養殖,節假日休休閒,娛娛樂……”小發不再踢石頭,順手摘下一枝路邊的野花在手裡一抖一抖。
李老漢想說:“那我的羊呢?”但喉頭一緊,沒有說出。他知道主任會計會說:“您可以從山上割了草抱家來喂呀。如果您不是三隻,而是三十隻,三百隻,那就不是一個羊圈裡的事兒了,就是一個山羊養殖場或者養殖基地的事兒了;那您李叔就不是一個李叔的事兒了,就是一個李場長、李總的事兒了。”如此之類天邊兒海沿兒的話,這段時間李老漢聽多了去了,但心裡還是象一團麻糾纏不清。
趕著他的羊隊伍過了路,下了河。滿河灘的草,大黑、老白和小白一幅不飢不飽的樣子,很懶散。大黑迎著太陽思考,小白圍著老白轉圈兒。河在一邊不急不躁地流。
“這世界怎麼了?”他抬頭看看天心裡想。
李老漢的祖上歷來就是“守著份薄田度日”奔波老碌的命相。到他成家後,從父親手裡接過一棍羊,羊隊伍從起初的十幾二十只不斷髮展壯大到四十、五十隻,最興旺時發展到六十多隻,一鞭子都趕不了啦。大兒子成親他賣掉了一半,小兒子修房又賣掉二十隻,到女兒出嫁,家裡人一致要他把所有的羊賣掉,說:“現在條件好了,也不缺那幾只羊錢。”他捨不得,也想不通。從十二歲跟著父親放羊,那羊,那山,那河,那日月,就跟他的生活和他對生活的全部想往“擰”在了一起,他習慣了藍天下山青、草肥、水綠,他和他的羊置身其間,那種感覺是一種農家人度日月的飽滿、充實和腳踏實地。於是執意留下了他的羊夥伴:大黑、老白和小白。
十幾年前修路,佔去了他家二畝好地。前年,村裡磚窯擴建,又佔去了一畝。現在村裡所有的地又要被開發了,要種樹,要建“農家樂”了,儘管都給了補償,日子也越來越寬鬆從容,但他心裡還是緊緊擰著,沒有絲毫鬆動的感覺。
大黑、老白和小白不知什麼時間到他身邊來了,大概想回去了。李老漢把目光投向老白和小白。老白和小白怕看到李老漢那種看著它們的目光,慌忙躲到一邊。
他看大黑:“咱們以後咋辦?”。大黑也定定地看他,那神色也彷彿說:“不知道。”
跟他的羊隊伍回來時,他的眼前晃動著一片黑兩片白,心裡說不出的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