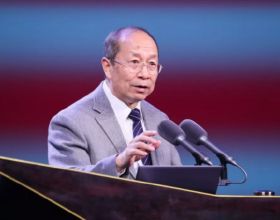三權中的獨立玩家
當2018年10月,特朗普總統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佈雷特·卡瓦諾最終在參議院的提名大戰中涉險過關時,美國媒體紛紛將其歸結為特朗普及其代表政治思潮的一大勝利。很簡單,被卡瓦諾取代的肯尼迪大法官,被稱之為“美國最有權力的人”。因為他經常在九人法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相持不下時,投下決定性一票。隨著卡瓦諾的成功上任,最高法院堅定地向保守派傾斜了。而這位法官春秋鼎盛,在美國憲法第三條第一款的規定“最高法院和低階法院的法官,如果盡忠職守得以繼續任職,並應在規定時間獲得服務報酬,此項報酬在他們繼續任職期間不得減少”的保護下,足以在任命他的總統下臺、甚至去世後多年,促使美國最高法院繼續向著對保守派有利的方向,向美國及全世界輸出秩序。
當然,這並不是說,最高法院大法官就是選擇自己出任這一職位的總統的應聲蟲。在美國提及“政府”一詞,並非只是指行政部門。美國獨特的三權分立制度,使其聯邦政府的三個分支,即立法分支國會、司法分支最高法院、行政分支—總統和國務院等行政部門,都相對獨立,從而發揮互相制衡的作用。美國的這一制度,屬於其首創,甚至和其母國英國都不同。美國前總統、政治學家伍德羅·威爾遜在其名篇《國會政體》就指出,“現代政治中最顯著的差別,並不在於總統制政府和君主制,而在於國會制政府和議會制政府。”前者即美國,是服從立法機關支配而又不對它負責的半獨立的行政官員組成的政府,後者即英國,是由實際上高於一切的立法機關認可的領袖和行政員組成的政府。英國議會號稱擁有除了“將男人變成女人”以外的一切權力,但對於美國國會就不能這麼形容。比如,美國國會擁有兔去總統職位的大權,即彈劾權,但卻不能指示總統按其路線行事。
這一原理同樣也適用於總統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關係。根據美國憲法,大法宮由總統提名,並取得參議院意見和同意後上任。1869年以來,最高法院大法宮的人數被固定為9人。由於大法官終身任職,退出職位的時間不定,因此每位總統能任命幾位大法官,甚至能否任命大法官,帶有很強的隨機性。而且美國建國兩百多年來,隨著平均壽命的提高,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壽命以及任職時間越來越長。比如倒黴的卡特總統,在其任上由於沒有任何大法官職位出缺,就不幸地沒有獲得任命機會。但一般而言,最近的幾位總統,都有至少任命2名大法官的機會。總統在提名時,都會盡量選擇和自己和本黨觀點有共同之處的候選人,但是當候選人一旦上任,就獨立行使自己的職能,即便其發揮的作用和總統設想的南轅北轍,後者也只能大呼上當,卻又無能為力。如保守的共和黨人艾森豪威爾總統曾於1953年提名加州州長厄爾·沃倫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結果此君從1953年一口氣幹到1969年,其主導下的最高法院,在促使20世紀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的美國向著自由化方向發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以至於艾森豪威爾將這一提名稱之為“我一生最愚蠢的決定”
又如在朝鮮戰爭期間的1952年,美國鋼鐵公司出現大罷工,影響了前方的軍火生產。4月8日,杜魯門總統根據總統的戰時權力,命令商務部長接管全國87家鋼鐵公司。6月2日,最高法院以罕見的神速,透過6票對3票的裁決,宣稱杜魯門總統無權接管鋼鐵公司的資產,即便可能影響到戰事。理由很簡單,總統釋出的命令必須根據聯邦憲法或者國會制定的法律,而這些依據中並不包括授權總統侵佔民間私有財產和以強力解決勞資糾紛。對於戰時權力,撰寫意見的大法官認為朝鮮戰爭是區域性戰爭,國家整體並沒有進入二戰那樣的全面戰爭狀態,總統即便要這麼做,也需要國會授權。因此,總統行為違憲。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法官,全都是民主黨的羅斯福總統和杜魯門總統任命的。
還有一例,迫使尼克松總統下臺的水門事件中,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曾經要求白宮交出作為醜聞關鍵證據的錄音帶,但尼克松總統援引行政特權拒絕交出。最終按照美國慣常的解決方式,政治問題被轉化為司法問題,錄音帶問題被上交到最高法院,1974年7月,最高法院大法官在美國訴尼克松一案中,一致裁定尼克松必須交出錄音帶。這一裁定成為尼克松黯然下臺的轉折點。而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就是由尼克松總統提名的。由尼克松提名成為大法官,後來在里根任上成為首席大法官的威廉·倫奎斯特同樣對尼克松投下了致命一票。
艱難的大法官任職之路
美國憲法並沒有對大法官的任職條件做出限制。但是戰後,大法官不僅幾乎都具備完整的法學院科班經歷,更需要是職業領域的佼佼者。甚至身體的肥胖、痴迷於菸酒,或者是經過三次才考取律師執業資格的經歷,都可能成為提名人被拉下馬的理由。一旦被提名,善於“扒糞”的新聞界就會蜂擁而至,將被提名人的履歷事無鉅細挖得底朝天,數十年前的次不經意講話都可能招來攻擊的炮火。但職業和生活的幾乎無瑕疵還只是基本的條件。
美國法院系統包括州法院和聯邦法院,兩個系統各有不同的任命方式。進一步說,美國的五十個州相當於五十個邦,沒有一個邦的法官任命方式是完全一樣的。就以最高法院大法官從屬的聯邦法院系統而言,一名聯邦法官的誕生需要經過多個環節,每個環節都存在多主體的互相制衡。
首先,當聯邦法官一職出缺時,總統需要選擇提名人。選擇候選人需要考慮到幾個因素:與提名有關的公眾或者領袖人物的願望和影響;美國律師協會聯邦司法常務委員會的專業評估意見;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在任法官的諮詢意見。其中,美國律師協會只是美國律師組成的行業協會,但卻因為其評估的專業性,實實在在地分享國家權力。1970年,尼克松總統的司法部長米切爾曾經向美國律師協會表示,尼克松政府今後將在把候選人提交到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之前,先讓協會的司法委員會對該人進行審查。協會也很重視這項事務,以提升自己在專業領域的影響,它在評估這名候選人時,可能會晤多達數百人,以確保評估的全面性。
一般而言,這位聯邦法官如果要“對口”某個州的進行服務,那麼總統還需要與該州的參議員進行商量。參議員一般都會有他們評估這位法官提名人的方式,隨後該參議員會透過“藍紙頭”( blue slip)來決定是否支援這名候選人,即在寄給自己的藍色公文紙下方寫明自己對這位候選人的意見,參議員也可以選擇不發出“藍紙頭”。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在討論這名候選人的任職資格時,這張薄紙上的意見。將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總統將候選人告知參議院,參議院的司法委員會就行動起來,蒐集這名提名人的資訊,進行背景調查,審查他的履歷和任職資格。在適當的時候,參議院會舉行聽證會,對於這名提名人,與會者自然是有的支援,有的反對。反對這名提名人的參議員會想盡辦法推遲聽證會,甚至透過不斷要求新資訊或者延長時間的方式,破壞聽證會。
司法委員會將舉行投票,決定是否將這名提名人提交給參議院。在上報時,司法委員會可以附上一份贊同的意見,也可以附上反對的意見,甚至不附上意見。反對這名提名人的參議員會繼續使用拖延戰術,阻止舉行參議院的投票。
接下來,對於這名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的候選人,參議院還要再組織次辯論,直到有一位參議員出來提議,組織一次全體投票來決定是否終止辯論和是否進入下一輪投票程式。一旦這一提議獲得透過,那麼參議院會投票決定這名候選人的資格,提名人獲得簡單多數同意,即可成為一名聯邦法官。
在這一套複雜的程式中,候選人面前的攔路虎包括:家鄉州的參議員沒有為總統提出的這位候選人表示支援;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遲遲未向參議院提交這名候選人;某些參議員阻止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順利安排一次全體參議院投票。
在卡瓦諾大法官最終接受的參議員全體投票中,情況一度扣人心絃。當時參議院的共和黨和民主黨的議員比例為51:49,每一票都至為緊要。但有一名共和黨議員史蒂夫·戴恩斯在投票當天,需要出席自己女兒的婚禮可能無法趕回。他的一名議員朋友直接表示可以將自己的私人飛機借給戴恩斯,從而讓他可以在一天之內來回華盛頓與蒙大拿州。儘管後來共和黨爭取到了足夠多的票數,戴恩斯沒有了“趕場子”的必要,但這架私人飛機一度被視為足夠影響大法官人選的關鍵因素。
政治漩渦中的黑衣人
畢竟聯邦法院系統是一個工作人員數萬名,每年預算60億美元的官僚機構。如果要說政府的這一分支遠離其他分支的影響,那是不現實的。更何況,美國憲法體制的精髓就是在於分權和制衡。最高法院受到其他分支的影響,從前面大法官的具體提名過程就可見一斑。
美國著名法律人羅伯特·博克的遭遇,頗能體現出捲入權力漩潤的提名人可能遇到的下場。1971年,博克曾經就任尼克松總統的首席政府法律顧問,其在司法部地位僅次於正副部長。當尼克松下令司法部免去堅持要他交出錄音帶的獨立檢察官職務時,正副部長都辭職表示抗議。博克按照順序接任後,開除了此人。儘管他後來任命的獨立檢察官繼續要求交出錄音帶,但博克因此得罪了盯著尼克松窮追猛打的參議院,特別是民主黨參議員。
1987年,博克被裡根提名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此時已經控制了參議院及司法委員會的民主黨人早就準備大幹一場。由於博克持有“原教旨主義”解釋憲法的學術立場,民主黨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誇張地說:“在羅伯特·博克的美國,婦女被迫到小巷子裡尋求墮胎,黑人坐在餐廳的隔離區裡吃飯,流氓警察會在深夜破門衝進公民的家中搜查,老師不能教授孩子進化論,作家和藝術家要接受政府無理的審查。”當時初入政界、擔任司法委員會主席的約瑟夫·拜登是阻擊戰的主要實施者,後來拜登作為建制派,被奧巴馬選為自己的副總統。同時,博克本人也應對不當。他在提名過程中,與報界頻頻接觸,為自己高調辯護。而其他大法官候選人基本選擇沉默,讓履歷來說話,甚至不斷拒絕回答參議院提出的某些問題。最終,博克在參議院舉行的全體投票中,以42:58落敗。這麼多的否決票,在大法官的提名中是相當罕見的。
為何大法官如此重要,是因為他們實際上是憲法的解釋者。美國憲法是兩百多年前制定的,當時沒有空軍,沒有網際網路,沒有兩黨制,跨越大西洋的旅程需要數月。而這部法律要適用於今日的美國,就必然要經過解釋。儘管其他政府主體、民間團體和私人都可以有著自己的詮釋角度和立場,但能一言九鼎的就是這九位老男人和老女人。某種程度上,大法官的政治態度與立場,可以決定這部憲法是“左翼憲法”還是“右翼憲法”,從而對總統的施政乃至世界,投下絕大的影響。總統還可以從大法官中指定一人成為首席大法官,首席大法官的一項特權是,指定判決意見的執筆者。畢竟判決意見的範圍是有伸縮性的,首席大法官憑藉自己對同僚的裁判風格和慣常立場的熟悉,透過指定執筆者,既可以把某種意見推到具體案件判決中,也可以“掛起”某種意見。當然,首席大法官除了擔任行政管理職能和此類特權外,在投票中,他也只有一票,在專業上並不高居於同僚之上。美國最高法院在建立時,仿效自己的母國英國,首席大法官披紅袍,而其他大法官穿黑袍,以示首席之尊貴。著名的馬歇爾大法官在就任首席大法官時,主動披上黑袍,和同僚保持一致。
憲法神殿的祭司
美國在兩百多年前,作為一個不起眼的小共和國,誕生於西方世界的邊緣地區。它繼承了英國對憲法的尊崇,但是又由於這個新國家拒絕了“君權神授”的君主傳統,《美國憲法》在美國其實取代了在當時西方政體中很常見的王權的生態位,在美國的地位僅次於《聖經》。大法官作為憲法的詮釋者,就像古希臘德爾斐神廟中詮釋神諭的祭司一樣,具有半神半人的光環。如果按照美國詩人惠特曼的比喻,總統是這艘國家之舟的船長,那麼大法官就是掌舵人。總統最長任職時間不過8年,參眾兩院的議員也都面臨著定期改選的壓力,而大法官很可能在其穩定任職的30年內,透過不斷在個案中釋出自己對憲法和傳統的理解,將這條船緩慢而堅定地導向自己認為正確的方向。不過,托克維爾早就評論道:“他們(聯邦大法官)的權力是巨大的,但這是受到輿論支援的權力。只要人民同意服從法律,他們就力大無窮;而如果人民忽視法律,他們就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