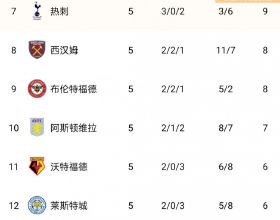1999年國慶節那天,全長沙放了個大假。
那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週年,全國都在歡慶,長沙所有的公共交通、公園、博物館、旅遊場所全部免費,上午我跟同學在教室看完閱兵直播,下午就乘中巴從泉塘到市區去玩,那時候泉塘還十分荒涼,學校周圍盡是農田,我們從學校出來要走好遠的路才能攔到中巴車,車招手即停,一停下來,車裡的人都一臉不滿瞪著你看,原來因為免費,上車後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車裡人多得能擠碎你的骨頭,開不了幾里地,有人暈車,吐了一尼龍袋,難聞的嘔吐味夾雜著汽油味佈滿車內,我們都屏住呼吸,眼睛直愣愣盯著窗外,忍受著漫長的痛苦駛進了長沙市區。
原本同學們打算去新開的世界之窗,但聽說人山人海,根本進不去,我們就轉道去了烈士公園,公交車上有個同學還被扒手給扒了一百塊錢,那時我們食堂兩塊多能吃一餐飽飯,一百塊是我們當年半個月的生活費,同學都急哭了,我們也沒什麼好辦法,大家都窮,只能一路好言好語安慰他。
大家在烈士公園漫無目的地遊蕩了半日,打聽到湖邊晚上會放煙花,傍晚時分我們走到湖邊,但來得晚,佔不到好位置,大家就蹲坐在草坪上,湊點錢買了些餃子過來分食。
天黑後,果然放起了煙花,煙花倒映在湖水裡,天上湖中一片炸開,引得我們這些湖南小城市過來的人,都覺得璀璨好看,我們或坐或臥,看著那煙花直衝雲霄,心裡頭都有些激動,我們互相看了看大家,有人說:
“不知道二十年後,我們都好大了,中國會變成什麼樣子啊?”
二十二年轉瞬就過去了。
這二十多年來,不僅整個中國發生了鉅變,我自己的思想也在波動起伏中不斷變化,慢慢地,我從激烈變成了平緩,從易怒變成了沉思,看事情也不再只看區域性,只盯著一件事、一個人,總是喜歡先將整體攤開一起來看。
我發現大多數事情並不是單一的,而是跟大系統有關,你瞭解到了大系統的運作方式,就能更深層次地瞭解一件事出現的前因後果,你會發現許多事情背後的規律,也知道如何抽絲剝繭去分析一件事,
每次我把空間與時間線放長一點,就發現自己能思索出一些不同的東西,也總能站在歷史的河岸上,看到更多清晰的脈絡與痕跡。
二十二年前,當我和同學看著長沙烈士公園的煙花向上升起時,我們對這個國家還充滿了忐忑與不解,但現在我漸漸理解了她,理解了這七十二年的變遷。
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七十多年,我們通常會把這段歷史切成兩節,就是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
對於後四十年改革開放的程序,我平時能接觸到的人,大部分觀點是認可的,而對於前三十年的歷史,大部分觀點是持不理解的態度。
因為在大家的回憶裡,前三十年總是與林林總總的運動息息相關,從1951年的三反、1952年的五反、1956年的肅反、1957年的整風與反右(1980年十萬右派平反)、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1959年反右傾運動、1964年四清運動、1966年文化大革命、1968年上山下鄉、1972年批林整風、1974年批林批孔,一直到1978年平反冤假錯案才踩住了剎車。
這中間還發生過1950年的抗美援朝戰爭,以及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三線建設,以及不堪回首的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
把這些事件累積在一起,看起來這三十年是極不平靜且艱苦的,許多人的不滿情緒,也集中在這個階段發生的事情當中。
但如果將中國的歷史拉長,我們會發現每一次中國完成大統一時,都會發生大約三十年左右的一次內部動盪期,為的是統一思想和集中權力,這個規律一直沒有打破過。
同時,每一次統一完成時,也會伴隨著強大的外部壓力,新生國家會遇到巨大的生存危機。
第二點是少有人注意到的,所以我想重點講一下這個地方。
我個人認為,其實從1949-1979年,中國一直處在戰爭或臨戰狀態,而我們是在這種狀態下推進工業化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會給國家內部施加了難以想像的壓力,而國家必須想辦法承受,在承受的過程中,間接產生了各種各樣的運動。
在1949年新中國剛剛成立之時,我們是一窮二白的農業國,全年糧食產量只有約1.1億噸,5.4億人人均只有208公斤糧食,全國只有1000萬人是產業工人,其他幾乎全是農民,同時全國只有12萬名工程師,合格的還只有4萬名,因為沒有石油、天然氣等,我們主要靠砍伐森林找燃料,民國結束時全國森林覆蓋率只有12.5%(2018年是23%),造成水土流失,引發洪災和泥石流,生態環境惡劣。
建國那年時,全國90%國民是文盲或半文盲,只有10%不是文盲,5.4億人每年只有67萬小學生入學,不到20%適齡兒童讀小學,初中入學率僅為6%,能讀到高等教育的人只有11.7萬,在農村,95%的人屬於文盲,混到高小就是知識分子。
一直到1990年代末,我學校的老師上課跟我們說,他們當年一下到水電站,只要聽說你讀過大學,所有人就服氣,覺得所有搞不懂的問題大學生都能解決,當神一樣看他們。
而且他們對知識有敬畏之心,寫有字的報紙斷然捨不得拿來墊屁股坐地下。
這就是當年知識匱乏留下的後遺症。
按當時的國力,我們的土地無法承受5.4億人的生存,只有向工業化要生存空間,我們才能活下來。
當時世界上只有兩個大國有能力向外輸出工業化,一個是美國,一個是蘇聯,而這兩個大國是敵對的,我們必須從中二選一,因為美國在解放戰爭中支援國民黨,也因為蘇聯跟我們在地理和意識上更接近,我們最終選擇了靠近蘇聯。
透過英勇的抗美援朝,我們極大的震撼了蘇聯人,他們想不到竟還有國家能將美國最精銳的部隊擊退,蘇聯對中國肅然起敬,1952年蘇聯打算援建中國50個重大專案,1953年增加91個,1954年再增加15個,最後定為156個。
這些專案包括煤炭25項,電力25項,鋼鐵7項,煉油2項,化工7項,有色金屬11項,機械24項,輕工1項,醫藥2項,其他還有44項軍工專案等。
蘇聯還向我們提供了31440套設計檔案,12140套機器草圖和2970套技術檔案等,這些資料只向我們收取了影印費。
我國根據國內礦產和交通的分佈情況,將這156個專案中的50項放在了東北,其他大多數放在了中西部地區,國防企業為了安全,也儘量放在了中西部。
為什麼儘量放在中西部?是因為當時世界各國都覺得可能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放在沿海地區不太安全。
蘇聯派來大批的科學家、工程師、技術人員,搬來大量圖紙和裝置建成了這些專案,還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工程師和技術工人,所以我們老一輩子知識分子學的都是俄語,到我們八零後時,因為世界格局的變化,開始轉學英文。
學什麼語言,主要是看你在吸引那個國家的工業產業鏈。
民國時我們火柴都造不出來,叫洋火,到1957年一五完成時,我們就突然從一個純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可以生產汽車和飛機,擁有大部分重工業的國家。
我們1956年沈飛開始產飛機,1959年產59坦克,包括核潛艇、火箭、原子彈、人造衛星等等,最早都是蘇聯人留下的底子。
那批蘇聯來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是真正出於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大公無私教我們完成工業基礎。
但就算蘇聯科學家無私,蘇聯的政治家也有自己的小算盤。
1957年,一五還沒有結束,赫魯曉夫就說要在中國建長波電臺、搞聯合艦隊,其實就是想控制中國的軍事力量。
但是中國只想獨立自主發展自己的國家,我們革命了這麼多年,就是要將一切外國勢力驅逐出去,一定要做純粹的主權國家。
我們感謝蘇聯的援助,但拒絕了蘇聯的控制。
這件事惹惱了蘇聯,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在沒有任何協商的情況下,單方面決定召回蘇聯專家,到9月就撤回專家1390人,廢除257個科學技術專案。
此後中蘇關係越來越惡劣,1961年越戰爆發,我們支援北越對抗美國,1965年蘇聯援助北越,對我們提出武器過境之類的五點要求,我們只答應了一條,加劇了蘇聯的不滿。
1969年中蘇累積的矛盾在珍寶島爆發,蘇聯在遠東邊境線陳兵110萬,號稱72小時能打到北京,隨時可能爆發戰爭,還威脅要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中國的東北、華北、西北全線備戰,也加速了三線建設。
電影《你好,李煥英》裡講的就是一家從東北搬到湖北的工廠,這家工廠就屬於三線建設的一部分,這個宏大的專案從1964年開始幹到1978年,安排了1100個建設專案,歷經三個五年計劃,投入2052億元。
為什麼要搞三線?就是擔心國家的工業被蘇聯一把打沒了,趕緊搬到安全的地方去,要是有個萬一,也給中國留下工業的火種。
我們來理一下這段時間線,就會發現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當時有多艱險。
建國後,我們選擇了蘇聯,為了保家衛國,在朝鮮打退美軍,這時是與蘇聯親近,與美國敵對,大約與蘇聯有七年左右的蜜月期,這是中國難得的和平建設時期。
從1960年開始,我們跟蘇聯開始有了裂痕,但沒有正式決裂,這時是與蘇聯疏遠、與美國敵對,中國已經開始進入危險期。
1969年珍寶島衝突爆發時,我們同時跟世界兩個最強大的國家處於敵對狀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封鎖包圍我們,以蘇聯為首的陣營要對我們進行核打擊,中國此時可以說生死一線。
當時世界兩個老大,發展中國家必須二選一,同時得罪兩邊,是一個國家最最艱難的狀況。
據三線子弟回憶,那時候他們家裡發各種手冊,包括化學戰民兵手冊、防核打擊手冊、防範生物武器攻擊手冊,都是按末日戰爭的設定來的。
可見我們也意識到自己所處環境十分危險。
幸運的是,眼見中國跟蘇聯鬧僵,美國戰略家們迅速決定與中國聯手對抗蘇聯,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過來探路,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開始轉和。
1978年12月我們宣佈改革開放,1979年2月即發生了對越自衛反擊戰,這中間其實是有關聯的。
我想在這裡討論一個問題,什麼是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並不是將自己以前三十年的努力全部否定掉,並不是說我們前面三十年就在過著愚昧的日子,然後突然醒悟過來,改革開放是指跟蘇聯整個工業體系過不下去了,已經跟蘇聯徹底鬧翻了,沒辦法從蘇聯那學習到東西了,我們的國家還十分虛弱,我們還要繼續學習,這時候只能希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解開封鎖,我們要對西方示好,融入新的工業體系中去。
剛好這也是美國想看到的,他希望拉攏我們一起幹蘇聯。
跟打完抗美援朝之後蘇聯支援156個專案一樣,1979年教訓完蘇聯的小弟越南,中美關係也開始走向親近。
但美國人可比蘇聯人精明多了,畢竟蘇聯早些年還是充滿理想主義的,美國人賊精,給的東西遠遠沒有蘇聯好。
1980年代跟美國關係最好時,美國向中國賣了24架民用版黑鷹、轉讓了TOW導彈技術、幫殲8進行現代化改造(沒成功)、轉讓了MK-46反潛魚雷技術等等。
好在美國是西方陣營的頭頭,他一鬆口,各種日資、港資、新資、韓資、臺資都湧進中國大陸,長三角珠三角開始接過中國工業的接力棒,熱火朝天地開始建設。
亞洲四小龍從此躺平。
改革開放到底是什麼?
其實就是從前三十年的一個發展系統,轉換到了另一個發展系統,讓國家能繼續完成工業化的程序,這就是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不是否定,而是承接。
所以我們不能用後四十年的發展,去否定前三十年的發展,中國的發展是七十多年工業化的累積,並不是前面閉著眼睛摸黑了許多年,到改革開放就把眼睛睜開了。
但為什麼總有人傾向於否定前三十年呢?
我個人認為,有一個客觀條件的存在,是部分人對前三十年否定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中國在發展工業時,選擇的道路,決定了前三十年的痛苦程度。
中國選擇了前期難度最大,痛苦最深的一條路,就是先發展重工業。
因為重工業能解決工業鏈裡兩個基礎問題:一是擁有了原材料生產能力,二是擁有工業機器生產能力。
日本和韓國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朴正熙對不按他要求發展重工業的企業家,直接抓去坐牢,強逼國家發展重工業。
每一個從零開始發展重工業的國家,都付出過慘重的代價。
我們常聽到一句源自西方語境的話,叫“社會主義國家一定會餓死人”,因為蘇聯、中國、朝鮮曾經發生過,所以推導是社會主義造成的。
他們說這句話時,好像忘記了愛爾蘭、孟加拉、印度大饑荒。
其實並不是這樣,古巴就沒有發生過饑荒,這句話是強行定義,本質是發生過饑荒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發展過程中,側重於重工業,是過度發展重工業付出了代價。
我們以斯大林舉例。
在列寧時期,農民允許擁有一塊私有土地,交完糧食後剩下的自己支配,大家一看可行,就熱火朝天地開幹,到了斯大林時期,他預判世界大戰即將開始,因此不惜代價發展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在農村搞餘糧徵集制,農民只能留一點點口糧,為了更好地控制收糧食,還強推集體農莊,禁止擁有私人土地,誰要是不聽,就處死或流放,政府再把收上來的糧食分配給工人,或者出口換外匯,賺來的錢,再購買工業相關產品。
烏克蘭大饑荒來源於此。
如果再查查剛起步時,同樣側重重工業的日本和韓國,會發現他們的農民也出現過極困難的局面,像日本早期為了對抗大清,農民的負擔是大清農民的五倍,韓國在人均GDP追上朝鮮時,老百姓的生活也明顯不如朝鮮,一直到達工業進步後再開始改善人民生活。
如果中國一起步就重點搞輕工,大家的生活質量會好一些,但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裡,我們無法獲得重工業的話,就沒有實力實現完整主權,也會降低國家發展的天花板。
中國重視改善生活是1973年的四三方案,到1982年才全部投產,這時候已經距建國已經過去33年了。
一個大國,要獲得發展的上限,開局就要點重工業,但人民會過得十分艱苦。
要讓人民過得輕鬆,開局可以只點輕工業,人民會過得相對輕鬆,但國家的上限會被人鎖死。
我經常看到許多人在爭論,政治制度到底是“集權”好一些,還是“自由”好一些,其實我覺得要換一種思路,就是任何國家在保證安全前提下,主要是兩大功能,一個是創造財富,另一個是分配財富。
這兩步必須先完成第一項,才能去做第二項,是前後關係。
創造財富就是工業化,國家到底是用什麼方式來完成工業化,只是一個手段,不是目的。
在前三十年,我們承接的是蘇聯的工業系統,所以也學習蘇聯的集體主義,大家同吃同住同勞動,私人空間沒有集體氛圍重要,在後四十年,我們承接的是西方的工業系統,所以也學習了西方的自由主義,出現了一大波財富英雄,私人空間比集體氛圍重要。
前三十年中國社會氣氛相對緊張,各種運動不斷,人們生活的氣氛十分嚴肅,主要是三個原因:
一是國家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而且是重集體主義的蘇聯模式;
二是每一次中國完成大一統,都會發生三十年左右的政治與思想動盪期;
三是中國一直處在戰爭狀態或者戰爭的邊緣,外部高壓擠壓了內部生存空間。
但這不是全盤否定前三十年的理由,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是一脈相承的,換了個門派修習心法,但目標還是要做武林第一。
我們可以對前三十年提出質疑,但不能全盤否定,沒有那一代人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搞出核武器、衛星、坦克、飛機,我們就是今天的越南和印度,命運被別人握在手裡。
1999年國慶節的晚上,我和同學在焰火下相互提問,“不知道二十年後,中國會變成什麼樣子?”
現在22年過去了,我也可以回答那時的自己,中國基本完成了創造財富的第一步,現在正在轉向分配財富的第二步。
只是創造財富這個過程,充滿了痛苦與血淚,許多人都不敢回想面對。
甚至我自己,只要想想那些年發生過的事情,讀一讀那時的文字,都難過得心如刀絞。
那些為了中國工業化而努力過的每一個人,或者被歷史的車輪不小心傷害到的人,都是應當被緬懷的。
文章最後,我想跟大家說一下分析事物的方法。
大家在思考一件事情對與不對時,通常會意識形態優先,比如有人會說“美國模式比較好”,也有人說“蘇聯模式比較好”,說著說著兩邊就開始動手了。
我建議放下意識形態之爭,轉而用經濟鏈來分析問題,當你這樣思考“我們透過向蘇聯學習,完成了基礎的重工業奠基,現在我們要發展輕工業,改善老百姓生活了,現在我們學習誰更好?”
只要能達成目的,學誰其實並不重要。
讓人民富裕,並且分配好財富,讓社會變得更美好,是我們的最終目的,而不是執著於意識形態,顛倒了過程與目的的關係。
執著的認定某種方法一定是對的,是意識形態的原教旨主義,不知道靈活變動的處理問題。
我們要的是一個好的結果,而不是什麼完美的過程。
最後引導我們走向復興之路的,必定佈滿了坎坷與機遇,拉長曆史來看問題,前三十年與後四十年,其實是一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