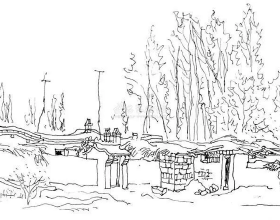前言
抗日戰爭期間,在大批抗日誌士血灑戰場、以身殉國的同時,也有大批的抗日誌士被抓後送進了戰俘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集中營或者是勞工營,最後被虐待致死。
對於所有的戰俘而言,進入了集中營就相當於一個漫長的死亡之旅,進去的人十有八九都不能活著出來。而他們也並非為了活命而甘心被俘,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顆捨身保國的決心,只是日軍沒有給他們任何機會。
例如在很多正面戰場,喪心病狂的日軍無視國際公約,公然使用細菌武器、毒氣彈等化學武器,導致很多抗日將士或被毒死,或者因中毒而昏迷,最後醒來已經成為戰俘。
還有的例如從事地下工作或者敵後工作的抗日誌士,因為敵人的突然出現而被牢牢控制住,根本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最終成為了戰俘。
今天的故事主角叫溫南文,本篇文章根據老人口述在日軍的北平集中營生活了一年的黑暗經歷,整理出來的。
這是一個抗戰老兵的血淚記憶,更是對日本侵略者憤怒的控訴。
老人回憶集中營內暗無天日的生活
1944年秋,我在河北定南縣武工隊工作。有一次我和陳海林、陳雲海去寨西店車站執行任務。因叛徒告密,我們三人均被日本憲兵抓獲,隨即押送到石家莊北兵營。
陰曆九月十四,我們幾百名囚犯被押上火車送往北平。押解之前的一天,我們同一牢房的三十來個難友,吃飯以後曾偷偷留下一個飯碗,趁看守不注意時,壓在屁股底下把它坐碎,每人分一小片準備路上暴動用。
可是上火車時,我們這三十來個人被敵人分開了。我們這節車廂有四十多個人,原來同一牢房的只有十多個人。我們全被反綁著,由兩個日本士兵押著。
路上一個同志用碎瓷片割斷了自己的繩子,當他正在給別人割時,被日本兵發現了,一刺刀砍過去,那個同志立刻滿臉是血,因為人心不齊,碎瓷片又太少,暴動失敗了。
一路上火車走走停停,也不知走了幾天幾夜,下了火車一看,才到下花園。日本士兵押著我們步行向北平走去。就這樣,我們來到了西苑日本1417憲兵司令部所屬的甦生隊(即勞工集中營)(甦:su,一聲)
甦生隊的地址,在頤和園東北,有數棟樓房。關在這裡的多是從華北各地俘虜的我八路軍戰士、抗日干部、國民黨士兵以及從各地抓來的勞工。日寇除了讓這些人為北平駐防的日軍兵營做苦役以外,還分批送往日本做勞工。
這所集中營的四周圍牆上架著50公分高的電網,圍牆外面還架有縱橫交錯的幾道電網。電網外面有一條5尺寬的水溝,水溝外面是馬路,有日軍日夜巡邏。集中營大門朝南,駐有一個班的日軍,電網的總閘就設在門口。
俘虜被押解到甦生隊以後,首先由警防隊搜身。這裡的警防隊有一百多人,都是戰場上投降日軍的國民黨士兵。隊長叫蔣唯一,原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團長,在戰場上帶部隊投降了日軍。他們身穿黑制服,手持警棍,專門虐待俘虜。
搜身搜出來的財物,都入了警防人員的腰包。搜完身後,他們叫俘虜把衣服脫光,換上破舊的俘虜衣。但戰場上被俘的八路軍不換俘虜衣,仍穿原來的軍裝。
我們被押來以後,站成一排一排的,警防隊叫我們把所有的財物都交出來。我身上帶著二十幾元的偽幣沒有交,因為它是組織上交給我的活動經費,萬一我能逃出去,還得用它。警防隊看沒人交出財物,便一個一個地搜身。我的錢因為藏在襪子裡,沒有被搜出來。但換衣服時連襪子也要脫掉,錢被警防隊發現了。一個隊員一邊罵,一邊掄起警棍劈頭蓋臉朝我打來,就這樣錢被他們搜去了,我還捱了一頓毒打。
俘虜進了集中營後,不叫名字,按天干地支排號,我被排為戊字0046號。在這裡除了原來認識的人外,雖同住一年多,但誰也不知道誰的姓名。如我所在班的班長,釋放後在淶源軍區招待所再次相遇時,我才知道他姓黃。
俘虜們四十人為一班,住一間屋子,從俘虜中指定正副班長各一人。屋裡有鋪板,上面鋪幾塊破席。 每人發給幾塊約有50公分見方的碎毯子,又小又破沒法蓋,就抽出毯子上的線把幾個人的碎毯塊連在一起,有的用柳條穿在一塊, 幾個人共同蓋。
我們進去的時候天已經很冷了,樓里根本不生火,西北風一刮,刺骨地冷。身上無衣,腹內無食,很多人就這樣被凍死了。
我們睡覺都是兩三個人搭伴兒睡,睡覺時人還是好好的,但越睡越涼,一推同伴,人已經死了。我們屋死的二十多個人,大多數是這麼睡死的。
這裡每天兩頓飯,每頓飯只有小半碗摻著沙子,已經發黴的米飯和小半碗水。吃不飽,餓急了就趁幹活時偷挖地裡的白菜根吃。有時外出做工,見到馬路邊的野菜也拔著吃;有的人還把野菜藏在懷裡帶回來,分給難友們吃。但若被鬼子見到,也要挨一頓毒打。
俘虜在屋裡彼此不許說話,白天只准坐著,大小便也要向警防人員報告。警防人員值勤時,每天都找茬毒打俘虜。
一天夜裡,一名俘虜因拉肚子去廁所沒來得及報告,被警防人員看見,說他是有意逃跑,最後被活活打死。
俘虜們進甦生隊時身體還好好的,由於吃不飽飯,每天還要乾重體力活,呆不了兩個月,就垮得走不動路了。早上還要跑步,跑不動也得跑。
由於生活環境惡劣,俘虜們的衣服和被子上的蝨子多得沒法處理,只好用席棍織成小掃帚往下掃,掃成堆再用腳將蝨子搓死,由於蝨子太多,白天干活又累,晚上很多人睡覺睡的比較沉,睡著後被蝨子吸血給吸死了。
到後來90%的人都得了傳染病,全身浮腫,頭腫得象柳鬥,腳腫得連鞋都穿不上,得不到治療,不少人被活活的折磨死。
我們開始時常去附近的日本兵營做勞役,以後又到先農壇南城牆下挖洞,還到過德勝門內喇嘛廟北城牆下挖洞,建汽油庫、彈藥庫。
每天從早到晚不停地幹,要勞動十幾個小時,拼命地做些挖土方,打洞、運料的活,吃不飽,再加上患病,全身虛腫無力。監工的警防人員見誰不使勁幹,就棍打腳踢,有的人被打得再也沒有爬起來。
曾在我晉察冀三分割槽定北縣擔任過特別區區長的劉尚仁同志,患有嚴重的疾病,但也得去做苦役。在先農壇挖土時,他病得動不了了,鬼子不但不給治病,反而把他扔到俘虜住的蓆棚外邊。最後慘死在那裡,被埋在南城城牆下。在集中營裡像這樣慘死的,何止一個劉尚仁!
大約在1945年初,日本人從甦生隊抽出了1000人,說是要去青島做勞役。陳海林同志也被抽走。事後聽人說,這1000人到了青島後,加上從石家莊及其他地方抽調的勞工共3000人,集中到青島海港碼頭收容所。
碼頭上停泊著日本的輪船,原來是準備把這些人送往日本。上船之前, 每個俘虜發了三個小窩頭,正吃的時候,突然飛來一批飛機,在上空投彈轟炸,輪船被炸沉了,3000名勞工也被炸死了2000多人,陳海林同志就是這樣被炸死的。日寇在遭受這次襲擊之後,便不再往日本運送勞工了。
1945年春,鬼子部隊的一個衛生班來抽血,我們被押到醫務室後驗完血型就開始抽血。這些血是用來給戰場上的日本傷兵輸血的。俘虜們的體質本來就很弱,抽完血後面色煞白,有的癱在地上,由別人架回去,有的當時就跌倒死去。
俘虜們痛罵這所醫務室是傳染疾病的傳染室,是吸人血的吸血室,本來這次抽血也有我,但因為班長和我的關係不錯,怕我抽血後受不了,就沒叫我抽。我因此躲過了這一關。
在甦生隊裡,每天死亡的俘虜總要在幾十人以上。死後就送到樓下的太平間,死人多時還得往上垛。抬死屍的人也是每個班抽出四個人,從早到晚不停地輪班抬。
有一次輪到我的班,抬的死屍當中有我的表兄宋栓堯同志,我含著眼淚把屍體抬到萬人坑,悲痛的淚水奪眶而出,實在不忍心往井坑裡扔。鬼子見此情景,拿槍托使勁戳了我兩下。我們只得忍痛扔完死屍,抬起空棺材往回跑。
1945年夏,有一個從山東押來的俘虜越牆逃跑了。這個人身材高大,體格魁梧。一天夜裡,他用胳膊夾著一個同他一起被抓愛的十幾歲的孩子、跳過了集中營的兩道電網和水溝,成功地逃跑了。一時俘虜中議論紛紛,有人說此人必有高超的武功及飛簷走壁之術。
幾天以後,又有一個山東俘虜想趁黑夜逃跑,跳在了電網上未能逃脫,被電擊穿,活活燒死。鬼子見電網起火,便向起火的地方打了幾槍,然後拉了電閘,把燒焦的屍體抬了下來。
第二天,日本鬼子把全體俘虜集中起來,開了個現場會,把那具燒焦的屍體抬出來讓大家看,說這就是逃跑的結果,以此來威嚇俘虜。其實只要有一線生機能逃出去,誰肯在這地獄裡等死。
日本投降後獲得釋放
1945年2月初的一天下午,一架重型飛機在西苑上空雲層中嗡嗡地飛翔。轉瞬間俯衝下來三架小飛機,向西苑機場方向飛去,在機場上空迂迴投彈後飛走;接著又俯衝下來三架小飛機,繼續轟炸西苑機場,將西苑機場炸成一片火海。這時所有駐西苑日軍兵營內的高射炮和高射機槍,一齊向天上開火。但小飛機在重型飛機的掩護下,向東北方向飛去。當時我們在樓上透過窗戶看得十分真切,大夥議論說:“這下鬼子快完蛋了!”
到了8月14日夜裡,我們在樓上突然看見日本鬼子住的北樓前著起火來,不知是燒什麼東西。十點多鐘的時候,又聽見鬼子們的哭泣聲。這時大家才意識到:準是鬼子快投降了!
“八一五”日本投降的訊息,我們是20日下午才知道的。
甦生隊的日本鬼子把我們召集在一起,宣佈了這個訊息以後,還宣佈了要釋放我們。大家心裡別提多高興啦。當天發給每人新的青色棉衣棉褲一套,日本軍用毛毯兩條,棕色膠木小碗兩個,還給每人發了一些路費和一個釋放證。
第二天,日本鬼子把大鐵門開啟,同志們獲得了自由。當我們走出甦生隊時,心裡既激動又難過。 激動的是勝利的這一天終於盼到了;難過的是關在這裡的26000多人,釋放時只剩下2400多人,活下來的不足十分之一!
當時所有人的身體都已經很虛弱了,如果鬼子在晚投降幾個月的話,恐怕這2400多人,連400人都不一定能剩上了。
結語
這只是日軍在中國土地上所建立的集中營中的一個,全國各地遭受這種殘忍折磨的又何止這幾萬中國同胞。日軍集中營的大門就像一個地獄之門,進入者有去無回。而即使活著出來的人,也大多落下終身殘疾,失去了勞動力。
這就是集中營內的真實寫照,這也是侵華日軍欠下中國人民的又一筆血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