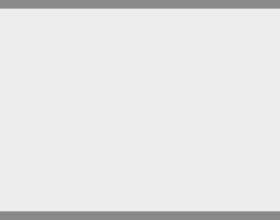(圖片來源:圖蟲網)
張翼/文
當論及納粹德國所犯下的罪行時,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針對猶太人及其他族群的殘酷種族滅絕。誠然,納粹德國的種族屠殺罪行是如此的駭人聽聞,以至於當大部分的歷史學“鏡頭”都聚焦於此時,納粹的其他罪行反而“失焦”了,這其中就包括納粹在戰爭中的經濟掠奪。
納粹德國在國內及其征服地區的經濟掠奪乃是戰爭機器的重要支撐,若沒有這些掠奪而來的物資,納粹或許根本無法發動戰爭,更遑論犯下如此罪行。有鑑於人們在納粹的經濟犯罪方面的認識不足,法國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呂康(Christophe Lucand)以葡萄酒為切入點,撰寫了《硝煙中的葡萄酒:納粹如何搶佔法國葡萄園》一書,為我們解析納粹德國如何將法國的資源整合進侵略者的戰爭機器,並進一步揭露那些為虎作倀的法國“合作者”們如何在戰爭中大發國難財,卻又在戰後逃過懲罰。
納粹是怎樣掠奪法國的葡萄酒的呢?莫非就像古代的日耳曼蠻子入侵一樣,把羅馬洗劫一空,大掠而歸?事實是,納粹德國的掠奪方式看起來和正常的買賣毫無二致,他們到葡萄酒莊園後用優渥的價格買下老闆手中的葡萄酒,然後再透過現代化的交通網路將酒運送回國,最終分配到前線士兵的手中。整個過程沒有直接暴力,私有財產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買賣雙方和和氣氣,就像戰爭並不存在一樣。不明真相的人很容易被這種假象矇騙,不免懷疑說,這難道不就是正常的貿易往來嗎,為什麼說是“掠奪”呢?問題的關鍵就在於,納粹用來購買葡萄酒的錢是哪來的,答案其實也很簡單:羊毛出在羊身上。
1940年德軍的閃電戰擊潰了法軍的抵抗意志,法國投降後和納粹德國簽訂了停戰協議。在協議中,納粹德國要求維希法國政權承擔德國佔領軍的軍費,同時禁止任何法國人向海外轉移資產的行為。納粹德國透過此條款向維希法國勒索了驚人的財富,保守估算維希法國每年承擔的軍費高達1500億法郎,超過法國在1939年全年的財政預算。為了籌集這筆“足以供給1800萬人”的軍費,維希法國開徵重稅,將負擔轉嫁到所有法國人頭上,讓每一個法國人出錢來供養騎在他們頭上的佔領軍。除了數目驚人的軍費外,納粹德國還強行控制匯率,原本10-12法郎兌換1馬克的匯率強行改成20法郎兌換1馬克。這種做法大大地增強了馬克的購買力,因此也就讓納粹德國得以更有效地吮吸法國的民脂民膏。在這樣現代化的掠奪手段面前,古代那種直接而純粹的掠奪無疑相形見絀。
維希政權在納粹的羽翼下逐漸穩定下來後,結束了佔領初期混亂無序的局面。為了更好地掠奪法國的葡萄酒資源,新的行業協會很快得以建立,以控制全國的葡萄酒生產、加工、銷售與運輸。德國方面派出官方的採購專員,用從法國人民身上搜刮來的財富購入這些葡萄酒,再將其送進納粹高官的別墅,普通德國人的餐桌和奮戰在從北極圈到突尼西亞漫長戰線上的德軍士兵手中。當然,除了這一“官方”渠道之外,納粹德國的各個勢力都有自己的代理人,他們從法國的社會渣滓中物色合作的物件,這些被選中的人在佔領軍的庇護下狐假虎威,繞過一切法規和限制,盡心盡力地為各自的主子奉上想要的物資。赫爾曼·戈林厚顏無恥地承認“我仍想搶劫,我還想搶走一切”,“我們可以利用一切手段,給德國帶來需要的一切”。
然而這樁買賣並非納粹德國買家的“獨角戲”,而需要法國賣家的參與。大多數法國酒莊老闆對納粹德國這樣“慷慨”的買家態度曖昧,儘管他們也不是不知道納粹用來購買他們葡萄酒的錢乃是用陰險而殘酷的手段從法國人民身上剝削而來的。許多不甘淪為亡國奴的法國人都拿起槍來加入了抵抗運動,可大部分的酒莊老闆卻把佔領時期稱為“戰敗的幸福時光”。難道這些酒莊老闆就毫無愛國心嗎?
要解釋這個問題,還需要把時間撥回到戰前。法國的葡萄酒生產在20世紀初迎來了長足的技術進步,同時阿爾及利亞殖民地的葡萄酒產業也欣欣向榮,這兩個因素共同推動了葡萄酒產量的急速上升。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20年代開始的大蕭條引發了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危機,法國的葡萄酒市場因此深陷供過於求的泥沼之中。由於嚴重的供求失衡,法國政府不得不出臺保護主義的政策,制定“合理的社會價格”保護酒莊利益,並推動減產,甚至蒸餾消耗過剩的葡萄酒。然而這些舉措僅是揚湯止沸,並不能徹底解決酒莊的庫存積壓問題。因此,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大量收購葡萄酒對於苦於手中積壓的酒莊老闆而言,無疑是天大的利好訊息,更何況德國人的出價遠高於所謂的“合理社會價格”。在這樣強烈的經濟利益誘惑之下,愛國心自然無從談起。
就算是曾經的戰爭英雄也無法抵禦這樣的誘惑,皮埃爾·安德烈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這位葡萄酒大亨曾在一戰中服役於法國第四十四步兵團,並因為英勇的戰鬥而榮獲勳章。他在戰後涉足葡萄酒產業並迅速發家,法國戰敗後他立馬效仿前一戰英雄貝當元帥出任傀儡政府首腦的行為,開始和納粹當局合作。在他寫給納粹當局的信中,他諂媚地宣稱自己有德國血統,可以不顧一切地奉獻於納粹事業,相比於那些被迫合作的人,他認為自己“生來就是合作者”。
正是在諸多類似皮埃爾·安德烈這樣的資本家的幫助下,納粹巨大的胃口才能夠被充分地滿足。隨著戰局的逆轉,納粹也加大了在法國掠奪強度,這使得原本供過於求局面徹底翻轉為供不應求。少數獲准出售葡萄酒的餐廳中,一瓶酒的價格足抵得上兩頓飯,黑市上的葡萄酒價格同樣令人咂舌。在這樣畸形的繁榮中,又如何能夠指望賺的盆滿缽滿的資本家良心發現,共赴國難呢?最諷刺的是,當盟軍光復法國後,那些在戰爭中大發國難財的酒莊老闆又轉而編造起“沒有賣給德國鬼子一滴酒”的神話,聲稱自己用各種巧妙的方法保護了法國的財產免遭德國人的掠奪。當然,不利於他們的交易憑證已經被銷燬,少數遭到肅清委員會清算的老闆也很快獲得了減刑。畢竟戰後的經濟復甦,還需要他們的“精誠合作”。
呂康對二戰中法國葡萄酒產業的命運也就敘述到此了,他用葡萄酒產業的例子為讀者生動地展示了納粹德國如何用高效的現代化手段壓榨戰敗國資源,使其服務於自身的總體戰需求。事實上,不僅是法國,包括低地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在內的整個西歐都被納粹整合進自己的戰爭機器中,使德國敢於同世界為敵。可以說德國在整個歐洲的經濟掠奪乃是助長其侵略氣焰的重要經濟基礎,其造成的惡果並不亞於種族屠殺。由於納粹德國的殘酷掠奪,到了戰爭末期,原本是世界最富庶地帶的西歐已淪為饑荒肆虐之地。西歐的飢餓一直延續到1946年才逐漸得到緩解,許多法國人甚至在解放之後,還不得不依賴黑市生活。伊恩·布魯瑪在《零年:1945》中就提到了一位英國人在拜訪他在巴黎大學任教友人時發現他依然需要到黑市購買商品,飢餓使他的西服看起來大了兩號。
納粹德國的經濟罪行卻並未如同其犯下的種族屠殺罪行那樣昭然若揭。這首先是因為納粹在榨取手段上的隱蔽性。卜正民在研究抗日戰爭中日軍對江南地區的統治時指出,戰爭期間只能維持生產的農業國是沒有什麼資源可以被榨取的,被佔領國只有具有現代工業化的生產、運輸能力時,佔領者才有利可圖。否則剩餘產品太少,汲取費用太高,以戰養戰就無從談起。對於日軍而言,中國廣大的鄉村不僅無法提供任何工業產能,還成為抵抗運動的牢固根據地,這使得日軍試圖在中國以戰養戰的策略根本無法實現,只能依賴殘酷的“三光政策”並最終進一步激發了廣大群眾的抵抗意志。然而法國的高度工業化卻導致納粹德國可以透過諸如強制改變匯率這樣隱蔽的方式高效地掠奪法國的資源,並最大限度地降低直接暴力所激發的抵抗情緒。站在更為廣闊的歷史視角來看,近代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的經濟掠奪,乃至美國在90年代強制讓日本接受“廣場協議”也都體現出這種經濟領域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的威力。
在納粹的掠奪中受益的合作者們也阻礙著針對經濟罪行的清算。正如呂康在書中指出的那樣,納粹對於法國葡萄酒的掠奪事實上讓葡萄酒莊老闆大獲其利,在這樣的經濟誘惑下,這些人成為忠實的合作者,幫助納粹掠奪自己國家的財富。對於資本家而言,愛國生意與賣國生意都是生意,利潤也並無民族之分,那麼與敵人合作又有什麼關係呢?從這個角度來看,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歐洲的抵抗運動普遍都帶有左翼色彩,二戰的階級鬥爭屬性也因此得以浮現。
但是,階級清算卻並未隨著戰爭的勝利而到來,包括葡萄酒莊老闆在內的大部分合作者不僅逃脫了懲罰,還為自己編造了“為了保護自己的葡萄酒而放棄唾手可得的利益,勇敢地抵抗入侵者的威逼利誘”這樣無恥的謊言,來掩蓋他們在戰爭中賺的盆滿缽滿的事實。當那些與納粹軍官通姦的婦女被憤怒的市民拉上街頭,被剃成羞辱性的光頭時,這些罪惡深重的資本家卻逍遙法外。這不得不讓人懷疑所謂的正義,究竟只是遲到而已還是說永遠都不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