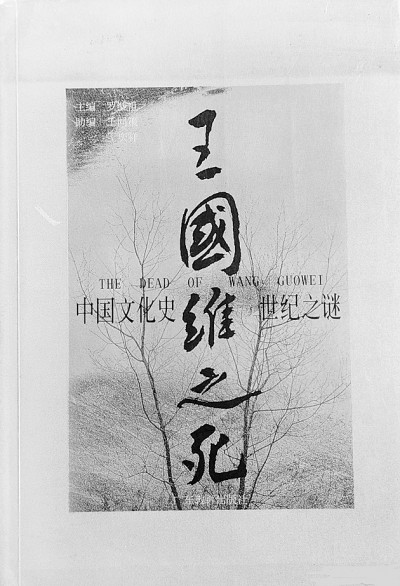【述往】
作者:彭玉平(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學人小傳
羅繼祖(1913—2002),浙江上虞人。自幼在祖父羅振玉指導下治學。曾在東北博物館、大連圖書館工作,吉林大學教授。著有《遼史校勘記》《永豐鄉人行年錄》《楓窗脞語》《庭聞憶略》《王國維之死》等,編有《羅振玉學術論著集》。
羅繼祖是羅振玉長孫,他1913年在日本京都出生時,王國維也攜家眷寓居京都,所以羅繼祖一出生就“認識”王國維。在日本京都生活和隨羅振玉回國寓居天津期間,羅繼祖都曾多接王國維音容。羅繼祖說:
我五六歲就見過他,一九二三年,他應溥儀之召從上海來北京,到一九二六年這幾年間,他每到天津必住在我家,我那時已經十二三歲,至今對他的聲音笑貌還留有印象,中等身材,清癯面貌,唇上鬑鬑短鬚,頭垂髮辮,戴近視眼鏡和瓜皮帽,繫腰帶,一口海寧話,一般聽不大懂。一九二七年校刊《王氏遺書》時,我十五歲,《遺書》雖然還讀不懂,但卻參預了校字之役。(《讀〈關於王國維的功過〉》,《讀書》1982年第1期)
其實不是“五六歲就見過他”,而是一出生就“見”過的。羅繼祖與王國維前後相識並交往的時間有七八年之久,王國維的形象留給後人的是想象,而留給羅繼祖的則是印象。加上他參與校訂《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其對王國維的熟悉程度確實非後來人可比。1940年羅振玉去世後,羅繼祖積極參與羅振玉《貞松老人遺稿甲集》八種的校寫以及聯絡印製等事,其中《後丁戊稿》即為羅繼祖所編,乙丙等集也主要由其校理。羅繼祖與其三姑母即羅振玉三女、王國維長媳羅孝純也較為熟悉,與王國維子嗣似也有一定聯絡。
大概因為整理編輯羅振玉文集之故,羅繼祖較早接觸到王國維致羅振玉若干書信,最早初步整理羅振玉與王國維往返書信的應該是羅振玉本人,總數有十數冊,他後將其中若干付諸裝池,由五子羅福頤儲存,1949年夏,羅福頤曾撰簡跋,略述其經過。1963年,羅繼祖即將輾轉獲得的160餘通王國維書信輯為《觀堂書札》,並交中華書局擬出版,後因故未出。“文革”結束後,羅繼祖索回書札,其中118通論學書札先刊於華中師範學院歷史系編印的《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一集。1979年8月,華東師範大學吳澤派人到長春羅繼祖處尋訪王國維遺稿,羅繼祖因將《觀堂書札》交付,蓋吳澤擬編王國維全集,第一卷《王國維全集·書信卷》即將羅繼祖所輯悉數收入,由中華書局於1984年出版。
1973年3月,羅繼祖開始編纂羅振玉年譜《永豐鄉人行年錄》,1976年12月完成初稿。(參見羅繼祖《臺灣版〈羅雪堂先生全集〉校讀記〔上〕》)起初,該稿本及過錄本只是寄奉其五叔羅福頤、堂姑母羅守巽、堂姑丈周子美(羅莊之夫)等家人審正。1978年7月10日,羅繼祖致信羅守巽雲:“《行年錄》重要在後半,如有意見,請提出。侄但據事直說,自問當無曲筆處。”(本文所引羅繼祖致羅守巽信,均見於朱松齡編著《羅守巽資料選編》,2021年1月編者自印本)可見,此書以據事直書為原則。1979年九十月間交吳澤寓目,吳澤認為羅繼祖用力甚深,澄清了不少問題。1979年11月,江蘇人民出版社致信羅繼祖,表達了出版願望。1980年年初,上海、南京兩地爭欲出版此書,最終此書於1980年4月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並綴一副書名《羅振玉年譜》。羅繼祖起初主張不署撰者之名,但在出版社的要求下署了“甘孺”之名。書出版後,羅繼祖寄張舜徽一冊,張舜徽回信說:“極佩敘事審密,無溢美,無浮言,宣傳祖德,可頌可傳……”(轉引自1981年1月羅繼祖致羅守巽信)這個評價應該是相當高了。
因為手握很多書札等第一手材料,故《永豐鄉人行年錄》中即多關於羅振玉與王國維關係的敘寫。此外,有些不宜寫入行年錄的內容,不妨在私人通訊中表達。如關於王國維與羅振玉晚年交惡之事,1978年11月26日,羅繼祖致信羅守巽雲:
王家的事,祖父性偏急,又專聽三姑一面之辭,其實王太太這人並不兇狠,不過好聽錢媽等人的挑撥,三姑就受不了,以致反目。事後王家對此並無惡感,所以《錄》裡也不必補敘。
很顯然,羅繼祖對王國維與羅振玉的關係,其實有很多話要說。不過限於年譜體例,不能過於枝蔓,遂有不少譜外之談。類似的言論其實已先見於羅繼祖1978年10月22日撰成的《跋〈觀堂書札〉》(刊於《讀書》1982年第8期)。
追溯“逼債”說之非
羅繼祖發表有關王國維死因的文章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促成他撰文的直接原因是“到目前還有人在刊物上說王靜安之死不是殉清而是受羅逼債,豈不可笑”(1981年5月12日羅繼祖致羅守巽信)。在羅繼祖看來,王國維之死緣於羅振玉逼債之說,乃是因當時遜清朝廷的內部矛盾而杜撰出來的、出於政治目的虛妄之說,為何過了半個多世紀依然有人拾此陳說?
關於王、羅晚年交惡之事,羅福頤早在1953年即撰文略述本末,惜未能發表,後來羅繼祖述及此事,也大體承羅福頤之說。
關於逼債說,羅繼祖至少在1982年5月2日已知鄭孝胥乃始作俑者。當日他致信羅守巽說:
鄭海藏以詩出名而非學者,故少為人稱道,且其人不純正,祖父與之始終不協。現知王觀堂死於逼債之說,乃鄭作俑,而為郭沫若等人所信,則其為人更可知,殆所謂政策策士一流。此事自不必與二姑言之,侄在《行年錄》中敘說已明白,將來還有許多材料可寫。
所謂“政策策士一流”,實際上揭示了逼債說背後的政治陰謀。而在《永豐鄉人行年錄》中,羅繼祖的說法尚比較模糊:
孝純為長子婦與繼姑有違言,僕媼復從中構之。靜安雖家督,而平日家政皆潘主之,己不過問,與鄉人事無鉅細皆過問不同。至是伯深卒,靜安夫婦蒞滬主喪,潘處善後或失當,孝純訴諸鄉人,鄉人遷怒靜安聽婦言,而靜安又隱忍不自剖白,鄉人遽攜孝純大歸。自是遂與靜安情誼參商。京津雖密邇,迄靜安之逝未再覿面,函札亦稀通矣。伯深服務海關,卒後卹金,鄉人且不令孝純收受。(《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十二集)
羅繼祖在此處加按語:“羅、王之隙,外人不知內情致生種種猜測,有謂王女適羅被休,實則羅女適王,因婿死而大歸也。靜安投湖後,疑竇益啟,至有謂逼債致死者。其真情雖王門子弟亦無知之者,何論外人,更何論溥儀。”溥儀的《我的前半生》弄混王、羅兩家姻親關係,宣傳逼債說,羅繼祖在此予以回應。頗疑羅繼祖在為鄉人撰寫年譜時,尚未確知逼債說之始作俑者乃是鄭孝胥,因為羅繼祖在言及逼債說之時,矛頭除了針對溥儀,其他就是“王門子弟”了。直到1982年5月,也就是《行年錄》撰成四五年後,他才知道“王觀堂死於逼債之說,乃鄭作俑”。羅繼祖這一節文字對王、羅晚年交惡原因的剖析是中肯的,兩個不同性格的人,面對同一件棘手的事情,都沒有調整自己的性格,以致近三十年情誼轉成參商。同樣瞭解王、羅晚年交惡原因的王國維弟子戴家祥,即對羅繼祖《行年錄》中的相關說明表達了認可。羅繼祖《〈觀堂書札〉再跋》一文曾略引其語云:
戴教授從王登明丈手裡看到《行年錄》後,寫信給我,說羅、王晚年失歡一事,師母潘氏即把所見所聞告訴姨甥趙萬里,趙又轉告我,與大作翕若合符,無偏無頗,正是史家求是態度。
作為王國維弟子,戴家祥的無疑代表了一個重要群體的態度。
王國維殉清說的堅守者
羅繼祖一直堅定地持王國維之死乃殉清之說。《行年錄》於丁卯年記雲:
年來南勢北漸,鄉人與同志數輩日憂行朝,以為危於釜魚幕燕,宜為未雨綢繆之計。顧行朝上下沓洩,人言弗恤,居恆怏怏。五月三日,靜安憂憤自沉頤和園昆明湖……鄉人年來與靜安雖疏闊,而效忠故主之念,固信誓無貳也。“再辱”云云,自本“君辱臣死”之義。靜安無遺折,殆不欲為身後乞恩計,鄉人乃為代作,竊比古人尸諫,冀幸一悟……(按:遺折上,曾引起溥儀懷疑。在《我的前半生》說遺折是羅偽撰,字寫得很工整,不是王國維手筆。此事始末,他人未必知,王門弟子則不容不知。)
這節文字包涵很多資訊,而這些資訊的匯合點則在遜清尸諫之說。先說遺折,羅繼祖直言乃是羅振玉代王國維而作,“王門弟子則不容不知”下語很重,其所透露出來的資訊,羅振玉事先應該與王門弟子有過溝通,至少王門弟子當時是預設和支援了羅振玉這一行為的,因為彼此最直接的動機就是為王國維求得死後之哀榮。羅繼祖提及1927年之時,他人或無感於時事變化,甚至對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感到“興高采烈”,而羅振玉及其同僚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不斷的行進中,對溥儀安危的擔憂,卻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既然可以不顧遜清朝廷與民國政府當初簽訂的協議,將溥儀趕出紫禁城,則在國民革命的大潮中,對蝸居天津張園、形同“釜魚幕燕”的溥儀,做出進一步的行為也是完全可以想見的。作為曾經的“舊臣”,自然與一般民眾的關切重點不一樣。羅繼祖述說其祖父及一幫舊臣的憂慮,應該切合事實。但王國維的“憂憤自沉”是否也在這“同志數輩”中,卻也是一個疑問。至少與王國維已經交惡的羅振玉不會在這個時候與王國維來協商行朝未來之事了。則羅繼祖在這裡順著文勢說到王國維的憂憤自沉,其中的關聯處,交待得還是不夠充分的。後來羅繼祖對此說得更為詳細一些。他說:
根據王先生十六字的遺囑,再結合王先生一生言行來看,我們說王先生之死是殉清,是尸諫,推而至於陳先生贊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梁先生從各方面的分析,王先生地下有知應嘆為知言……王先生之死有遠因,有近因,遠因應追溯到幼年在家庭裡所受的封建教育和中年所研究的西洋哲學;近因呢?我認為,葉德輝之被槍斃不能說沒有關係,起碼使王先生在心靈上增加恐怖……梁雖是帶有政治色彩的人,但不是革命物件,到必要時還要避一避時局風頭,因而使王先生感到天津張園溥儀身邊太危險了,同時也感到自身,甲子僥倖不死,這一次萬難倖免了,所以決然自殺。(《〈觀堂書札〉再跋》)
羅繼祖聯合陳寅恪、梁啟超之說來整合殉清尸諫說,這裡的邏輯關係尚需進一步論證,但羅繼祖的傾向性是非常明晰的。關於王國維之死的遠因、近因說的分析維度,應該也大致符合一個自殺之人的常態。與《行年錄》稍有不同的是:《行年錄》主要從溥儀可能身陷危境而自己上言不能達,以此“憂憤自沉”;而此處所憂則不僅有溥儀,也有自己。至於說甲子“僥倖”不死云云,則還是為了合理解釋“一辱”與“再辱”的關係。其實客觀的情形是:甲子之變,不遑說溥儀,王國維同樣也無性命之憂;北伐即至,王國維同樣是安全的,甲子之變時,王國維尚身在南書房行走任上,而此時他從“組織關係”上已經與遜清朝廷無關。在這種情況下,能否“倖免”於難,其實是無需考慮的問題了。深感羅繼祖此處“僥倖”二字或有失當。
王國維當然是關心溥儀的安危的,但以一個遜清朝廷局外人的身份,這種關心是否到了需要自沉以明志的地步,還是有疑問的。所謂“君辱臣死”,一般的前提是君已受辱,方才談得上臣以赴死,豈有君尚未受辱,而先行赴死的?以當時王國維與溥儀行朝相當鬆散的關係,是否要走到這一步,實在是有疑問的。
要說明王國維之死是殉清,必須以王國維是忠心耿耿的遺老為前提,若“遺老”尚且不純、不願或不徹底,“殉清”未免就成無根之談了。羅振玉一心以復辟清王朝為念,此已成共識,羅繼祖也持此看法。但王國維是不是與羅振玉一樣心甘情願做遺老呢?學界的看法頗有差異。羅振玉、金梁、楊鍾羲等遺老自然眾口一詞以王國維為忠誠的遺老,而遺老群體之外的人看法就不一定了。顧頡剛在《悼王靜安先生》一文中就認為,王國維“他做遺老明白是他的環境逼迫成功的”,若非因得到羅振玉的種種幫助,王國維“何必因靠羅氏之故而成為遺老”,所以“大家只覺得他是一個清室的忠臣而已,這豈不是一個大冤枉”。(《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郭沫若在《魯迅與王國維》一文中即認為:因為結識羅振玉,王國維的周邊形成了以遺老為主體的群體。在這樣一種環境中,“厚於情誼的王國維不能自拔,便逐漸逐漸地被強迫成為了一位‘遺臣’。我想他自己不一定是心甘情願的”(《郭沫若全集》第二十卷)。1980年4月,謝國楨為《永豐鄉人行年錄》撰序雲:“餘以為雪堂老人於清末成為保皇派,猶且拖著王靜安師一齊下水,誤己誤人,自貽伊戚。”顧頡剛、郭沫若與謝國楨都認為王國維是“被”羅振玉遺老的,“被”遺老與一心要做遺老顯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羅繼祖則承羅振玉之說,認為他們都是典型的清朝遺老。1978年10月22日,羅繼祖撰《跋〈觀堂書札〉》認為:“祖父和王先生效忠清朝的信念,至死不渝,這一點是共同的,並不為家庭嫌隙有所動搖。”他更認為王國維成為遺老乃是其自覺的行為,並非受羅振玉引導或逼迫。他說:
有人說觀堂隨祖父避地日本,才使觀堂走上遺老道路,這也是形式邏輯的看法,倘使當日觀堂從心裡不願追隨,也不會違心曲從……我認為觀堂甘心作遺老決定於去日本之前,從觀堂所作《送日本狩野博士遊歐洲》和他自稱得意之作的壬子三詩完全可以看出。(《對王觀堂的器重——〈家乘點滴〉之六》)
如果把王國維與遺老的關係分幾個階段的話:辛亥之後至寓居京都期間是第一階段;從日本回到上海寓居時期為第二階段;從北上出任南書房行走至去世為第三階段。第一階段是清亡初期,王國維在京都以若干文學作品表達了“故國之思”;第二階段王國維從京都回到上海,與沈曾植、朱祖謀、鄭孝胥等遺老過從較多;第三階段入直南書房,則與遜清朝廷以及溥儀發生了直接的關係,並親身經歷了甲子之變。羅繼祖認為王國維在去日本之前已然有遺老之心,實際上直接否定了由羅振玉影響而成為遺老的可能。羅繼祖提出的依據是其《送日本狩野博士遊歐洲》一詩以及稍後編定的《壬子三詩》。但此《壬子三詩》正是去日本之後創作的,尚不能證明王國維在去日本之前即有遺老之心。在《壬子三詩》中,《頤和園詞》以慈禧一生為中心寫愛新覺羅一氏末路,《蜀道難》哀悼端方,確實對清王朝的終結寄寓了深深的哀思。狩野博士雖然任教京都大學,但因為初到京都,故在送行狩野遊歷歐洲時,也瀰漫了一種濃重的故國之思,其中若“談深相與話興衰,回首神州劇可哀。漢土由來貴忠節,至今文謝安在哉”云云,也確乎蘊含著一定的遺民之思,而在鈴木虎雄索閱此詩時,王國維呈上詩並致函,特別提到詩歌中對日本社會政治制度也有憂慮,他說:“竊念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國維以亡國之民為此言乎。”(王國維1912年10月7日致鈴木虎雄信,見《王國維書信日記》)他直接以“亡國之民”自稱。但這種遺民之思究竟是出自本心,還是來自羅振玉的影響,若無十分明確的證據,也確實不能簡單就下結論。
對於謝國楨說羅振玉“拖著王靜安師一齊下水”,羅繼祖不能認同。他說:
據我主觀認識,羅、王兩人在清末這段時間對時局的看法還是很一致的,不是你東我西。從王先生性格可以說,他沒有世俗獵取高官的慾望,也沒有做革命投機生意的奇想,書生本色只有規行矩步地服從命運,況且回顧家世還有“安化郡王”那一段忠勇殉國的光輝歷史,以及他那“我是祝陳鄉後輩”的有抱負的詩句,所以跟著泛海東去,並不是受外界力量的“拖”。(《我的祖父羅振玉》,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
其實不遑說清末這段時間,民國年間,王國維與羅振玉對政治形勢的判斷也是基本一致的,檢《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可見其大概。羅繼祖對王國維性格的把握是準確的,王國維對政治有態度,但自身基本無慾望,也就是沒有用行動介入其中的慾望。張勳復辟時,寓居上海的沈曾植、康有為等紛紛北上,便無一人提議帶上王國維,沈曾植更是將北上之事囑家人勿告之王國維,可見即便在遺老群體中,王國維也是基本被忽略甚至迴避的一位。
羅繼祖又說:
他前半生,出國留學,學洋文,研究西洋哲學,儼然是個維新開明人士。中間對仕進無意,專去研究文學和戲曲,也不失為一個想在新的學術領域裡創新的學者。後半生由於時局劇烈轉變,隨我家東渡日本,治學方面也舍舊從新,又和溥儀搭上關係,墮落成為頑固遺老,走上反動。短短五十年而變化這麼大,令人難於理解。不過這裡要說明一下,影響不能沒有,迫脅並不存在,因為王先生並不是胸無主宰隨人牽著鼻子走的人。(《〈觀堂書札〉再跋》)
王國維治學範圍大體經歷了一個從西方到中國的轉變,而其政治思想也有從務新到守舊的變化,這都是可以覆檢的事實。不過羅繼祖在這裡將王國維與溥儀建立關係與成為“頑固遺老”直接掛上鉤,似乎也顯得有些跳躍。但羅繼祖說“王先生並不是胸無主宰隨人牽著鼻子走的人”,這是深契王國維個性之言。但這種自成崖略的個性,也可能恰恰成為他“遺而不老”、有思想而乏行動的理據,可能誰也難以撼動王國維以遺老之心而自居於遺老群體邊緣的狀態了。
即便羅振玉家人,也並非都從殉清角度來解讀王國維之死。1954年,羅福頤曾撰《憶觀堂先生手札二通》(《江海學刊》1982年第2期),其中即有云:“其實觀堂丈之死因,實先罹喪明之痛,後悼亂離之憂。”此文雖然發表於文章撰寫後近三十年,但他對王國維死因的分析,與王國維之女王東明的看法相似,尤其是王國維之死與長子王潛明之死的關係,兩人的看法彼此呼應。我覺得應該引起充分重視。
“同志數輩”說與遜清朝廷黨爭
這裡再簡略說說羅繼祖提到的“同志數輩”的內涵,字面上當然是指志同道合的幾個人。在王國維與羅振玉交惡的情況下,王國維不在“同志數輩”,大概是不言而喻的。但據實說,王國維原本是在其列的。丁戊年(1937),羅振玉撰《升文忠公〈津門疏稿〉序》言及溥儀在紫禁城時,升允密疏陳奏,“或公起草,或遣予代作,或一人具疏,或聯名以聞。當道為之側目,致以公與予為朋黨,公弗顧也”。此處雖然只是言及羅振玉與升允二人,但其實下面接著說:“亡友王忠愨公受知於公,為公門人,其任南齋時二疏並附錄卷末,一以志公眷眷君國,一以志當日之聲應氣求,如公所謂吾道不孤者,俾傳之方來,不至泯滅。”(《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十集)
王國維與升允聲應氣求,確乎是事實。羅繼祖《永豐鄉人行年錄》亦記雲:
鄉人與王靜安先後被遜帝召直南書房,王出升吉甫薦,鄉人度亦出升薦,曾面質,升堅不肯承。鄉人既屢與升聯名上書,遜帝師保左右嫉之甚。及遜帝出居日使館,諸人議論紛紜。升自津扶病趨謁,贊鄉人議,群遂指目為朋黨,鄭孝胥且悻悻南歸。即遜帝蒞津,租張園為行邸,時園歸粵商,鄉人與同直清遠朱聘三汝珍共經手,某某乃藉端媒櫱,計得售,遜帝漸疏鄉人。顧問之授,外示尊崇,實遠之也。
這裡說了溥儀身邊的派系鬥爭問題。其實羅繼祖在《〈觀堂書札〉再跋》中將張園當時的黨爭說得更為細緻。他說:
溥儀身邊大致分成三派:親貴和內務府舊人為一派,鄭、金就是從這一派裡分裂出來的;以陳寶琛為首,因他是師傅最受溥儀尊敬,有一些人依附他作外圍成一派,這兩派人數都較多;南書房同僚溫肅、楊鍾羲、朱汝珍和祖父、王先生,包括柯劭忞(柯名義隸懋勤殿)為一派,這一派人少力弱。黨論傾軋的結果,祖父被疏遠了,派中人也受到打擊。(《〈觀堂書札〉再跋》)
這就是當時朝廷三組“朋黨”的基本情形,而鄭孝胥與金梁則是其中用力最大者。後來的情況雖然有一些新的變化,但羅振玉的劣勢還是沒有改變。羅繼祖說:“後來張園小朝廷的權一直掌握在具體執事人胡嗣瑗、景方昶、陳曾壽幾個人手裡,鄭孝胥和他們時分時合,因為只有他們才能朝夕和溥儀接近,他們又都學會一套固寵弄權的手法,得到溥儀的信任,把張園弄成死水一潭,外人如何也打不進去。”(《〈觀堂書札〉再跋》)升允、羅振玉與王國維三人是相對固定的“朋黨”,其中升允與羅振玉要更為密切,而朱汝珍則是與羅振玉共同經手張園的人。因為他們一度深得溥儀讚賞,也因此受到其他政客的嫉妒。鄭孝胥悻悻南歸大概就是一種跡象了,但後來鄭孝胥地位日隆,羅振玉的邊緣化也就慢慢成為了現實。今檢王國維與羅振玉往返信件,也頗有共疏之例。但當年的“同志”,到了1926年、1927年之交時,顯然發生了轉變,這也同樣是一種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羅繼祖關於王國維自沉的描述應該更多來自於羅振玉的自述。羅振玉在《集蓼編》中述及此事雲:
乙丑以後,連年值內戰,津沽甚危。予與升文忠公、王忠愨公憂之甚,然均無從致力……至丁卯,時局益危,忠愨遂以五月三日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上聞之悼甚,所以飾終者至厚……一旦完大節,在公為無遺憾,而予則草間忍死,仍不得解脫世網,至此萬念皆灰……(《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十一集)
羅振玉的表述還是有比較明確的時間意識的,羅繼祖以“年來”二字,將“同志數輩”的關係似乎一直延續到丁卯五月。而羅振玉則將“乙丑以後”與“丁卯”做了區分,在丁卯以前是明確的“予與升文忠公、王忠愨公”三人,而言及丁卯,則不再合說三人。但將時局與王國維之自沉直接聯絡起來,羅振玉與羅繼祖還是一致的。羅振玉以“完大節”來定位王國維之死,則殉清之意故昭昭在焉,羅繼祖承續此意,只是言說得更為詳實而已。
辯誣:身份與學術的雙重責任
1918年4月25日,羅振玉致信王國維,提及柯劭忞之幼子方六七歲,“頗似長孫”,羅繼祖在此信下按雲:“公札中謂‘頗似長孫’,乃以我為比,我小時弱不好弄,公甚喜我規行矩步,聽大人話。記得我七歲返上海時,熟人見我說舉止甚似三太爺(三太爺乃淮安人對公之習慣語)。公此札竟舉我為典型,可見愛我之篤矣。”(《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東方出版社2000年版)作為長孫,羅繼祖幼時備受羅振玉賞愛。
“這幾年來,我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為我祖父辯誣,同時也為王觀堂先生辯誣。”(羅繼祖《再為觀堂辯誣》,《揚州師院學報》1987年第4期)辯誣應該並非羅繼祖的初衷,只是對於被塵埃掩蓋了很久的事實,他有一種揭示真相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質實而言,羅繼祖對王國維之死的看法基本上籠罩在羅振玉之說之中。但除了殉清說之外,羅繼祖確實澄清了諸多謬說,其貢獻值得充分肯定。
《光明日報》( 2021年09月20日07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