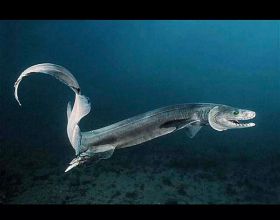整理 / 烽火臺
一、中國儒學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學
儒出身於“士”,又以教育和培養“士”(“君子”)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說,士出來任職做官,為社會服務,就好象農夫從事耕作一樣,是他的職業。荀子在講到社會分工時,也把“士”歸於“以仁厚知能盡官職”(《荀子·榮辱》)的一類人。所以,從這一角度來講,原始儒家學說也可以說是為國家、社會培養官吏的學說,是“士”的文化。
子貢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的問題,即怎樣做才稱得上“士”。孔子回答說:“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論語·子路》)這句答話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時也指出了做為一名“士”的最基本條件和責任:一是要“行己有恥”,即要以道德上的羞恥心來規範自己的行為;二是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國君所交給的任務。前者是對士的道德品質方面的要求,後者則是對士的實際辦事能力方面的要求。而這兩方面的統一,則是一名合格計程車,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荀子寫了一篇題為《儒效》的文章,其中對於儒者的形象和社會作用是這樣來描寫的:“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美俗”就要不斷修身,提高道德品質,以身作則;“美政”則要“善調一天下”,為社會制訂各種禮儀規範、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會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基於以上對於“儒”、“士”、“君子”的基本社會使命的分析,可以說原始儒學的主要內容都是關於“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規範和從政方面的治國原則。而且,從孔子、孟子到荀子,他們所提出的各種道德規範和治國原則,都是十分具體的、為人處世中踐行的規範和原則,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而上學原理。
人們稱孔子之學為“仁學”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孔子是把“仁”作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規範來要求的。如他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論語》一書中記載著許多孔子回答弟子們問“仁”的言論,其內容都是實行行為中所要遵循的各種具體規範和原則。如:
答樊遲問仁,一則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雍也》)一則曰:“愛人”(《顏淵》)。
答顏淵問仁,曰:“克己復禮為仁。”(《顏淵》)
答仲弓問仁,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顏淵》)
答司馬牛問仁,曰:“仁者其言也訒。”(《顏淵》)
答子張問仁,曰:“能行五者(恭、寬、信、敏、惠)於天下,為仁矣。”(《陽貨》)
再如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陽貨》)“剛、毅、木、訥,近仁。”(《憲問》)以及有子說的“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等等,無一不是具體實踐行為中遵守的規範原則。
《論語》一書中也還記載著許多條孔子答問為政的言論,同樣也都是十分具體實踐行為中遵守的規範原則。如:
子貢問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顏淵》)
答齊景公問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
答子張問政,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顏淵》)
答季康子問政,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
答子路問政,曰:“先之,勞之,無倦。”(《子路》)
答仲弓問政,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子路》)
答葉公問政,一則曰:“近者悅,遠者來。”一則曰:“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
又答子張問從政,則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堯曰》)等等。
孟子除了進一步發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學說而著稱於世,而其所論的"仁政"內容,同樣也是十分具體的。如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而所謂的“正經界”,就是“分田制祿”、“制民恆產”(《孟子·滕文公上》、《梁惠王上》)等。再就是他經常舉以為例的周文王的“仁政”內容,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徵,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以及“尊賢使能”(《公孫丑上》)等等。孟子對為什麼要行仁政和為什麼可能行仁政,也進行了理論上的說明,但他的那些理論說明,大都是感性直觀的。如他認為,因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仁愛之心”,先王同樣也有“不忍人之心”,此心發之於政,即是“仁政”等,來論證行仁政的根據。又以“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盡心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等“推恩”理論,來說明行仁政的可能性等等。
孔子、孟子在修身與治國方面提出的實踐規範和原則,雖然都是很具體的,但同時又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成分,也就是說更多地寄希望於人的本性的自覺。所以,孔子竭力強調“克己”、“修身”(《憲問》)、“為仁由己”等,而孟子則以“性善”為根據,認為只要不斷擴充其“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公孫丑上》)、“求其放心”(《告子上》),即可恢復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實現“仁政”理想。
與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則具有更多的現實主義傾向。他在重視禮義道德教育的同時,也強調了政法制度的懲罰作用。他認為,人的本性並不是那麼美好的,順著人性的自然發展,必然造成社會的爭亂。因此,必須用禮義法度等去化導人的自然本性,即所謂的“化性起偽”,然後才能使之合乎群體社會的公共原則和要求。所以,荀子在強調自我修養、道德自覺重要性的同時,更為強調“師”與“法”的教育與規範作用。如他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荀子·性惡》)又說:“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為也。”(《荀子·修身》)
同樣,荀子設計的治國原則:“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與具體的“富國”、“強國”之策,乃至他的“禮論”、“樂論”、“君道”等等,可以說都是非常富於現實主義的,都是在肯定當時已經形成的社會等級和職業分工的基礎上,來規定社會每一個成員的名分和位置,並要求其各盡其職,從而達到整個社會的和諧一致。當然,這並不是說在荀子提出的治國原則中沒有一點理想主義的成分。因為,如果他的學說中一點理想主義成分都沒有,那麼,他的學說就不會有什麼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稱為一名思想家。
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戰國時期,是社會上具有廣泛影響的“顯學”之一,他們提倡的道德修養學說在“士”階層中有著深遠的影響,而他們設計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國原則,則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統天下和禮義王道為上等,太脫離當時諸侯稱霸、群雄割據的社會現實了,因而始終沒有能得到當權者的賞識和採用。所以,原始儒家學說與以後成為實際社會制度依據的儒學不同,它還只是一種關於道德修養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學說。在我們以下的論述中,人們將會看到,分清這種差別是非常重要的。
二、中國儒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是以董仲舒、《白虎通義》為代表的兩漢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學
漢初統治者為醫治秦末苛政、戰亂造成的社會民生極度凋敝的狀況,採用了簡政約法、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方針政策,以恢復社會的生機。與此相應,在文化思想上則主要是推崇和提倡黃老道家學說,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漢武帝時才有所變化。不過,這並不是說儒學在漢初社會中一點也沒有起作用。儒學在傳授歷史文化知識方面,對漢初社會仍然是很有影響的。儒家所推崇的歷史文獻——“六經”的教授和研究,也是得到官方的肯定和重視的。荀子的學說在漢初儒家中影響很深,“六經”中的《詩》、《易》、《禮》、《樂》等學,都有荀學的傳承。同時,荀子作為先秦諸子和儒家各派學說的集大成者,他那廣採各家學說之長的學風,對漢初思想的開展也有很大的影響。如西漢大儒董仲舒的學說中,不僅接受和發揚了荀子關於禮法並重、刑德兼用的理論,而且還大量吸收了墨家“兼愛”、“尚同”的理論,乃至墨家學說中某些帶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為突出的是,在他專攻的春秋公羊學中,充滿了陰陽家的陰陽五行學說,並使陰陽五行思想成為漢以後儒家學說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班固在《漢書·五行志》中說:“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這一事實。董仲舒曾向漢武帝建議:“諸不在六藝(六經)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書·董仲舒傳》)這是以後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方針的重要根據。但必須指出的是,董仲舒這裡所說的“孔子之術”,顯然已經不是原來的孔子學說,也不是原始儒家學說,而是經過他和漢初其他儒家學者發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陰陽等各家學說之長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術”。
董仲舒對於儒學的發展不僅在於學理方面,而更在於他把儒學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學,是一種密切聯絡社會現實的學說。公羊學認為,《春秋》經所載對於各類社會事件的判斷和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都具有某種法典的意義,可以作為當今社會(漢王朝)判斷各類事件和評價人物的依據和範例。這也就是當時社會上相當流行的所謂“春秋斷獄”說。由此,他們進一步又認為,《春秋》經中所說的“三統”、“三正”、“三世”等理論,都是為漢王朝的建立作論證的;而《春秋》經中所提到的各種禮義法度也都可以為漢王朝所效法。於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藉以揭示孔子作《春秋》之宏旨及其包含之微言大義。他認為:“《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玉杯》)“《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竹林》)所以,他引述子夏的話說:“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俞序》)董仲舒的這些觀點在當時是很有影響的,如司馬遷在談到《春秋》時就明確表示說:“餘聞董生曰。”同時,他也竭力強調說:“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史記》太史公自序)無怪乎當時就流傳著所謂孔子作《春秋》“為漢帝制法”的說法。
《春秋》被認為是孔子所作,而孔子所作的《春秋》又居然是為漢王朝制訂禮義法度,那麼孔子應當放在什麼地位上呢?董仲舒與漢儒們想出了一個絕妙的稱號:“素王”,即一位沒有實際王位的王。這樣,儒學就開始與當時實際的社會政治制度聯絡了起來。不過,這在董仲舒時代僅僅是一個開始而已,直至東漢章帝時,由皇帝親自主持召集大儒們舉行了一次“白虎觀”會議,會後由著名學者班固整理纂集,公佈了一個官方檔案:《白虎通德論》,這才真正完成了把儒家一部分主要學說轉變為實際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律條,以及全體社會成員必須共同遵循的道德規範。從此以後,儒學已不再是單純的倫理道德修養和政治理想的學說了,而是同時具有了一種社會制度方面的律條的作用。
與儒學政治制度化發展過程的同時,兩漢時期也出現了一股把儒學宗教化的傾向。在董仲舒和當時流傳的緯書中,不斷地把“天”描繪成儒學中至高無上的神。如董仲舒說:“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並且竭力宣揚天是有意志的,能與人相感應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從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學理論。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為了神化教主,在當時流傳的大量緯書中,不僅把孔子說成是神的兒子,而且把他的相貌也描繪成與一般凡人極不相同的怪模樣。同樣,為儒家所推崇的歷代聖人,如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等,在緯書中也統統被裝扮成了與眾不同的神。又,這些緯書都是以神話和神秘化了的陰陽五行說來附會地闡釋“六經”以及《論語》、《孝經》、“河圖”、“洛書”等,這些也可以視作是配合當時儒學宗教化所需要的儒教經典。再有,由秦漢以來逐步完備起來的儒家禮儀制度(可參看《禮記》中的"冠義"、"婚義"、"鄉飲酒義"、"聘義"、"祭義"等篇的內容),也為儒學的宗教化準備了儀式上的條件。從兩漢儒學發展的歷史看,儒學的宗教化是與儒學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關的,是同步進行的,前者是為使後者得以成立和鞏固服務的。
儒學社會政治層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強,同時也就減弱了儒學作為一般倫理道德修養和政治理想層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學那裡,它是透過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啟發出人們遵守道德規範、追求理想社會的自覺。所以,儒學對於士大夫們的修身養性具有重大的意義和作用。可是,當儒學的一些主要內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後,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覺與否,自願與否,都必須遵守的外在規範,因而它的修養意義和作用就大大地被減弱了。這樣,儒學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卻成了它在道德修養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機。
到了漢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學禮教(名教),一方面成為束縛和壓制人的自然感情的東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偽君子沽名釣譽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玄學乘此流弊而起,調和名教與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強調以“自然”為本。並且在理論學說上,玄學也明確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後漢紀》卷十二“袁宏曰”)。所以,自從玄學誕生以後,儒學儘管在政治制度層面仍然保持著它的統治地位,而在思想修養層面的功能,卻已為玄學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東晉南北朝以後,以至於隋唐時期,佛教思想的影響又超過了玄學,在士大夫的思想修養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所以,從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約七百年間,儒學只有那些體現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東西,在統治階層的維護下繼續起著作用。
儘管這一時期儒學文獻方面的研究也並沒有中斷,但象唐孔穎達編纂的“五經正義”之類的著作,除延續漢儒和玄學家的觀點外,並沒有多少新意。所以,儒學在人們的思想修養方面,也發揮不出多大的作用。後人在評論儒釋道三教的社會功能時,常說:“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趙昚語,轉引自劉謐著《三教平心論》捲上)這種說法從一個角度反映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佛道的學說在人們的修身養性方面所起的作用遠比儒學為大。
兩漢時期儒學性格的重大變化,以及由此而發生的儒學的兩個層面的社會功能的消長等,是很值得人們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問題。
(注:圖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