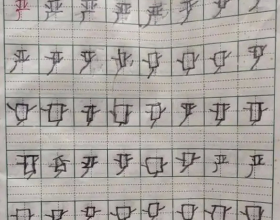在這個依舊許可寫得不好的時代,詩人陳超認為,詩的本質不是表達經驗,也不是志在抒情,而是詩本身,"不管你屬於哪種創造力型態,每個真正的詩人生命內部,都有個’絕對的詩’的幽靈,或舍利。’"
從這種說法來判斷李田田(九零後女孩,鄉村小學教師,在《詩刊》發過頭條,上過中央電視臺《新聞1+1》節目)言及自己見聞或者經歷的詩,我們可以說她的詩是"絕對的好詩",裡面藏有好詩的"舍利"嗎?
在《師範女生的愛情》一詩裡,她這樣寫自己的"師範生活",言及自己的"師範姐妹"——
"師範學院百分之九十是女生
四年來,我的室友都沒談過戀愛
對男人的認識不是白馬王子
便是偶像劇裡的三生三世
還沒畢業就相親
第一次相親就飢不擇食
一個個都懷孕了
然後就開始吵架,後悔
我問她們,為什麼不戴避孕套
她們說,反正是他的人了
她們連選擇權都放棄了
在春天自廢武功"
在陳超看來,"詩,是個體生命和語言的瞬間展開。"李田田在這首詩裡展示的,是師範女生的"在春天自廢武功",除了最後一句令人有一種喟嘆混合著莞爾,其他的句子在我看來,"語言的瞬間展開",也太普通了。這首詩唯一的意義,或許只在於能引發人們對"師範學院女生"戀愛與性的關注吧?
相比之下,我認為,《羞恥》一詩,更能體現李田田作為《詩刊》"頭條詩人"的能力——
"夜深了,他把臥室的觀音像
移到另個房間
才開始脫掉我的衣服
木床咯吱咯吱響
整棟吊腳樓都在顫慄
"而我不敢呼風喚雨
隔壁躺著他病危的父親
不時傳來可怕的咳嗽聲
我想逃離這窮鄉僻壤
睡在月亮裡
"早上起來,他依舊擺好觀音像
點蠟燭,跪拜
我忽然感到羞恥"
陳超認為,"詩的含混和清晰一樣,本身不等於詩的價值。詩的價值:含混,必須有內在的精敏做基礎;清晰,必須有’光明的神秘’。"
這一首《羞恥》裡,"我"為什麼"忽然感到羞恥",那是既清晰,又"含混"的,能夠引發人們長久的感思。吊腳樓裡,被移走又移回的觀音像,病危父親可怕的咳嗽聲,被脫掉的女性衣服,咯吱咯吱作響的木床,出於"羞愧",想從窮鄉僻壤去月亮入睡的"我"……詩歌不僅僅是傳釋作者的情感、經驗、智識,詩還有屬於它本身的情感、經驗、智識。同樣一個李田田,既能夠寫出普普通通的《師範女生的愛情》,又能夠寫出不同於流俗的《羞恥》,這進一步印證了陳超的說法,"好的詩歌,像真佛,是有’後光’的。那光圈,看得見,摸不著,那是我們難以磨滅的茫然無知的美妙頃刻。"寫詩,即是踏上拜佛之途,想見一次真佛,想體會一次那樣的"美妙頃刻",就只有不斷地擴充套件自己的感知邊界,讓自身不斷地進入詩,成為世間一條柔韌的神經纖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