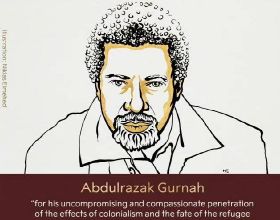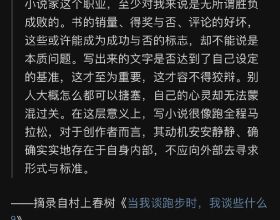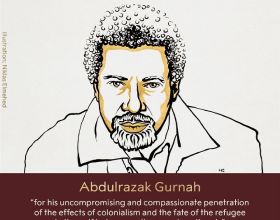中西方意識形態的分歧,很難調和。這方面的矛盾在過去,今後都將存在。
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形象文字化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藝術。我們的一段歷史程序,會出現許多文學作品。如果這些作品比作一副畫卷,這副“畫”會從各個方面反映出歷史程序的各個形態。假如我們看一副草原風景畫:碧綠的草,噴薄而出的太陽,壯闊的雲彩。同時對草下面枯萎腐爛的草,小蟲子的屍體。。。並散發出腐敗的氣息這些形態,會忽略不寫或少寫。因為這不是美麗草原形態的主要方面。
當我們看到一碧千里的草原風光,清香的草木味撲鼻而來,讓人心曠神怡,如痴如醉,我們會感受到生命的美麗;冉冉升起的太陽,衝破雲霞,戰勝了黑暗和寒冷,和藹熱情,將世界攏入懷中,賦萬物生機,給世界以光明,展現一種大無畏的精神;殷紅的朝霞浸染了東方的天空,紅雲縱橫,橫跨天際,盡情綻放著肆意的激越,令人心潮彭拜,能給我們的工作和生活帶來激情與活力。而碧草下面灰色部分,雖然是真實的,但帶給我們的是晦暗,頹廢,產生消極情緒。
關注碧草,太陽,雲彩等文學作品,象徵著蓬勃的生命力,衝破黑暗,積極向上,百折不饒,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作為西方意識形態諾貝爾文學獎視而不見,對碧草下面灰色部分情有獨鍾。
我們民族經歷過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有新中國成立後建設社會主義激情燃燒的歲月。 抗日戰爭時期,蕭軍《八月的鄉村》,舒群《沒有祖國的孩子》,茅盾《白楊禮讚》, 杜鵬程《保衛延安》,梁斌《紅旗譜》,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等文學作品為中華民族十四年抗戰和解放戰爭留下史詩般的歷史畫卷。 解放後,有王蒙《青春萬歲》,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李存葆《高山上的花環》等許多作品描繪了捍衛與建設新中國的壯麗畫卷。改革開放時期,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引起了熱烈凡響,那個理想式的喬廠長,在改革開放初期“摸著石頭過河”過程中,帶動了一大批人勇於投身到前無古人的革新大潮中,深圳蛇口“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理念席捲中國大地。還有張潔《沉重的翅膀》,李國文《花園街五號》,路遙《平凡的世界》,關注改革程序和改革對整個社會尤其是人的思想,道德,倫理觀念帶來的變化。許多作家開始把創作目光由歷史拉到現實,一邊關注著現實中的改革發展,一邊在文學中發表自己關於祖國發展的種種思考和設想。與時俱進,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真實地反映了歷史變革在神州大地上引起的迴響,多層面、多角度地展示了改革開放的壯麗畫面。
同時也有賈平凹《廢都》,作者寫的是他生活了二十幾年的城市生活,那個年代的城市與鄉村、男人和女人、外界與內心。理想的坍塌、價值的失落。給人頹廢的感覺。賈平凹《廢都》獲得法國費米娜文學獎。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思想的穿透力且具有魔性,嫻熟的語言能力,擁躉粉絲無數,其作品大多寫實,筆下歡樂與苦難,時有沉重感,也有灰色調,其寫實性的價值可為後人認識中國另一方面,也就是草原畫作綠葉下的陰影部分有一定價值。
文學的責任,便是作者要憑藉心靈的感悟與想象向讀者展現一個有意義的生態。而文學本身,理應對其涉及到的廣大民眾及後世讀者負責。西方不想看到華夏民族的復興,總希望中國處在矇昧,混亂,落後的狀態:政治上“威權”,外形上“咪咪眼”,心理上“猥瑣”。唯西方“高大上”。在這樣的操弄下,能夠正面反映中華民族時代風貌的優秀作品不在他們選擇的範圍內。
我們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自強不息艱苦奮鬥,一路披荊斬棘,雖有波折,但從不氣餒,一路高歌,走上了民族復興之路。西方勢力操作話語權,對中國汙衊和詆譭,阻擋不了中華民族復興的步伐。假以時日,我們不再“韜光養晦”,我們一定能再造一個超越“諾貝爾獎”的中國獎。到時候,“和平獎”、“文學獎”將是人類公認的大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