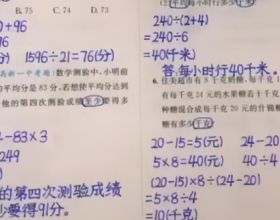1939年12月6日,歷經千辛萬苦,拖著已經被日寇折磨成殘疾的身體,北平志成中學學生耿全民,終於逃出敵佔區,來到了昆明。他帶回了大量日軍機密檔案,以及敵佔區日軍情報,對於他在敵佔區的種種悲慘遭遇,根據他在西南聯大林教授家裡的口述,經修改整理,發表於《大公報》。以下,節選自耿全民對遭遇日軍酷刑的回憶錄:
(作者注:有些行刑過程過於血腥、暴力、殘忍,本文迴避。請讀者自行腦補)
我是北平志成中學的學生,平時住在西城狀元府飯店內。在去年五月一十二日早晨六時許,當我要將夜間由無線電中聽得我方退出徐州的訊息帶至學校告訴同學們時,就聽得大門外有大卡車的停止聲,緊跟著有許多由汽車上跳下來的皮鞋聲,馬上房門被打得如同雷聲一般。我知道事情有些不妙,恐怕又是日憲兵查店來了,我急速地回到屋內把昨日由廣播電臺抄下來的一些紙條及手中現拿著的、編輯好的中央廣播的訊息拿到後院,擲在廁所的糞坑內,當我回到屋內時,十幾個日本憲兵也來到我的屋子裡。其中一個為首的,短短的個子,一臉生就的橫肉,兩個耗子眼睛,在厚厚的嘴唇上留著一叢標準的日本小鬍子,頭上戴著一頂瓜皮小帽,上身穿著一件灰色肥大的袍子。他惡狠狠地看了我一眼後,問我:“姓什麼?”我回答說:“姓耿!”他又說道:“你是耿全民吧?”我又回答說:“是!”“那麼好極了!”他說完這句話後,向後邊的日本憲兵“唧唧咕咕”地說了幾句話,馬上就走過一個憲兵來,把一付手鐐子帶在我的手上了!隨後把我架上了一輛大卡車,一直開到東城煤渣衚衕三號北平憲兵隊——將我押在一間八號的監房內。
這個院子,是個四合套的房子。我住的是間南房,在這間房子內,我數了數,共有二十個人,連我在內。我是第八號,在這個房子內,最使我奇怪而又納悶的是,每個人都坐得像筆管似的直,面向著牆一言不發。我等了一會,實在忍不下去了,我就向我旁邊的一個人問道:“你們因為什麼都不說話?而坐得這樣的直,不煩嗎?......”
我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啪!”的一聲,就像一排針亂刺我背的一樣疼痛。我一回頭,看見一個兇狠的日本憲兵,手拿皮鞭在用力抽打我。他的胳膊打得大半是沒有力量了,才趾高氣揚地罵了一聲:“八格牙魯!”跟著說:“不說話的有,你腰直的有”,就揚長而去了。
“我旁邊坐著的一個人,兩眼充滿了同情的淚水,望著我出神,似乎要說話而又不敢說的神氣,望了我一會兒,後來對我說:“我的小朋友!快快地坐好了,像我們的一樣。不然的話,他們這一群兇狠的惡狗還會進來打你的,你是新進來的人,不知道他們的規則。他們的規則,白天不準睡覺,不準說話,不準站起來,坐著時須得坐直了……”
坐在我旁邊的兩個人——九號與十五號都是平津一帶的日本反戰的中堅分子。九號叫井上,十五號叫阿塞一郎。井上因放火焚燒他們軍隊的子彈庫而被捕,阿塞因以商人之名,進行聯絡平津日本軍人,從事反侵略戰工作,在北平的“皇軍俱樂部”被他們軍閥的爪牙—反間諜工作者——所逮捕。
在打我的看守者出去了沒多久,就聽見院裡有人喊我的名字,緊接著,打我的看守進來,把我帶到院內。喊我的人就是當天早上逮捕我的那個為首者,他是北平日本憲兵隊特高課課長,叫做伊藤海,在七七事變前就在平津一帶活動,是個有名的“中國通”。
他把我帶到一個陰森森的小房間內,房間內的地上、牆上都放置著打人的刑具。在一張桌子旁,坐著一個人,他是個朝鮮人,叫小榮,專任審問時的翻譯官,伊藤海坐在當中,指定我坐旁邊後,他便開始問道:
“耿同學,你們的計劃,我們日本憲兵隊已經破獲了!請你趕快地把其餘參與計劃的人說出來!你說出來,我們把你放了,否則,可不要怪我們對你不客氣。”
“什麼計劃?我都不明白,我是個中學生,每天除去上課之外,什麼我也不知道。”我回答著。
“我知道你是學生!你們學生都是抗日分子。你今天不說,我就要對你不客氣了!”伊藤海狠狠地威脅我說。
“你讓我說什麼?我什麼也不知道!”我仍然地分辯著。
“好,不給你點厲害看看,你是不知道皇軍的嚴厲。跪下!把上身衣服脫下來!”他氣憤地命令著我。
伊藤海把牆上掛著的皮鞭取下來,在我頭上、後背上用力地抽打,起先打得我身上奇痛難忍,後來,由奇痛變成了麻木。之後,我什麼也不知道了!不知道有多少時候,感覺有人在我頭上潑冷水,我睜開眼睛,看到兇狠、慘暴、毫無人性的伊藤海,對著我得意的笑。
他又開始破口大罵:“跪起來,給我說!”
“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依然地辯解著。
“你什麼也不知道?八格牙魯!”一腳把我踢倒後,接著說:“去!下午,再給你點兒厲害看看!”
這時的我,費盡了整個全身的力量也站不起來!坐在桌旁的朝鮮人小榮看我被打得這個樣子,把我拉了起來,我才一顫一顫地跟著守門的敵憲兵回到原處八號。這個時候已經是正午十二點鐘了。中國的差役正在給犯人們分發口糧,也分發給我兩個饅頭,一塊鹹菜,一碗稀飯。這些東西,我一點也沒有吃,因身上頭上被皮鞭打的地方,此時更疼痛起來了!
午飯後,小榮把我帶出去了,但這次沒有把我帶到早晨去的那個屋子裡去,而是把我帶到另一個陰冷的院子裡。在院子當中,擺著一條類似平常上房用的梯子,但是,這東西兩端的下面有兩尺多高的板凳,在這怪物旁邊,放著一條由南牆邊上自來水龍頭引了過來的三丈多長一條紅橡皮管子。除去兇狠的伊藤海站在這個怪物東西的旁邊之外,還有兩個敵憲兵也在他的旁邊。
我到院中時,伊藤海向我笑了一下後,向我一撇嘴,站在他後邊的那兩個如狼似虎的憲兵走過來,就將我綁在那個不知殘害過多少愛國志士的怪東西上了!伊藤海又向我微笑了一下說:“小耿呀,你若是還不說出你們的計劃,我就用冷水把你灌死,說不說?”
“什麼計劃不計劃,我一概不知道,我是個學生。”我回答說。
“好!不真給你點兒厲害,你是不會招的!灌他!”他跟著說了幾句日本話。
他的話剛停止,我的臉就都是水龍頭噴出的水了!
起初,我還能呼吸,後來水管子口對準了我的嘴噴,水從口腔流下去了,就覺得呼吸急促,就在這時,我的知覺便失去了。
當我知覺恢復時,我已躺在太陽光射在的地方,我的兩鼻孔內感覺特別的難過,比患重傷風病還要難過到萬分。臉上、脖子上似乎有什麼瘡疤樣子的東西貼著,我忙用手摸了一下,原來是已經曬乾了的血疤!我的媽呀,這些是怎麼弄的呀?我的內心又驚嚇又悲憤地猜想著。早晨皮鞭打得身無完膚,但是還不至於流血啊?
後來我回到監內,聽那些個獄友們說的,我的頭上的幹血是從口內和鼻內流出來的,當我被冷水灌昏過去後,我的內肚充滿了冷水。他們為著不讓我立馬死的緣故,就命兩個日本憲兵拿了一塊三尺寬、八尺長的木板子,放在我的肚子上,按著板子兩頭,用力地向下壓,把我肚子內的水又都倒壓了出來。水是壓出來了,但我肚子內的血也被壓得混水流出來了!
從那天起,直到今天,我的胃口神經便失去了知覺,飯吃不吃都無關,吃是固然不餓,不吃也感覺不出來餓還是不餓。
這群禽獸不如的日寇,看見我醒來,又把我再次綁在那個怪東西上後,伊藤海說:“你覺得不大好過吧?告訴你,不好受的東西還在後面呢,現在趕快把你們同夥說來!”
我這時對生根本沒有什麼留戀了,幾次毒刑拷打後,最後還不是得像傳說中一樣,把我槍斃或是活埋了嗎?現在,不如給他一個橫的回答,讓他們一下子把我弄死,免再遇這“活閻王”的毒刑、輪迴的苦罪。
所以,我大聲地喊著說:”你們趕快把我槍斃了吧!”
伊藤海“呸”的一聲唾了我一臉唾沫,緊跟著瞪圓了眼,怒狠狠地說:“八格牙魯,槍斃你?哪有這麼便宜的事?不說出你的同夥出來,就慢慢地活剝你皮,說呀!”“啪”的一聲,他又狠狠地打了我一個嘴巴!
我挺了一挺我的腰,也是同樣瞪大了我的兩眼,自自然然地、毫不畏懼地說:“好,你們要活剝我的皮,就請趕快來剝吧!......這句話我還沒說完,伊藤海親自把水管拿起來,用力地插入我的嘴裡,向內灌水,我又被灌得失去了知覺。
這次醒來,我已半躺半坐地靠在我住的監房內——八號的南牆邊上,當時慢慢地睜開眼看時,坐在我對面的九號犯人——井上,正看著我,用袖子抹他臉上的眼淚。
第二天早晨,叫我站在伊藤海的對面,旁邊立著兩個穿便衣的日本人,其中一個手中拿著燃著的大木棍。
伊藤海見了我的面,就說:“跪下!”
我跪下後,他仍然問我昨天所問的那些話,我還是堅決地答他一個不知道。他便一聲不響地向那穿便衣的憲兵使了一下眼色,他們便把大木棍交給伊藤海,將我按倒,把我的褲子向上拉,伊藤海便用燃著的大木棍向我兩腿上燒,他一邊燒著,一邊逼我招供。
可是這個時候,任他們怎樣殘暴、毒辣,我是依然地沒向他說半句話。伊藤海用盡力氣,把大木棍向我的兩腿上捅,陣陣的奇臭難聞的氣味及火燒油漬中加帶水分的滋滋聲,彌滿了整個的房間。
耿全民說完了這段話後,把褲子向上拉了一拉,兩條大腿在一支電燈光照射下,佈滿了燒傷的傷痕。
伊藤海見我被燒傷了仍然不肯招供,便放下燃燒的大木棍,拿來一對木夾子,每隻手指都被夾住,幾個日本兵一起用力拉緊夾子,我疼得昏死過去。他們用冷水把我潑醒,繼續夾,就在這種酷刑下,我那天昏死又澆醒,反覆了三次。
第三天,他們又把我的腳用粗繩子繫住,吊在一棵大樹上,兩個日本兵一拉,我就被倒著吊在半空中,他們又搬來一個大水缸,放在下面,一鬆手,就把我投入盛滿水的水缸中,我嗆水暈了過去。他們把我用皮鞭抽醒,再吊起來,再沉入水缸。我昏死幾次,但還是什麼也不說。
第四天,伊藤海又玩起了新的花招,他對我說:“你這兩天想得怎麼樣了?是繼續在這受罪還是想回學校讀書?你不要再嘴硬了 ,與你一起同住的幾個同學都已經招供了,你還是說了吧”
我還是沒有回答,坐在旁邊的翻譯,朝鮮人小榮假惺惺地說:“伊藤海課長念你年幼無知,被抗日教育洗了腦,小耿啊,你還年輕,你把你是如何加入抗日團體的經過說出來,我擔保伊藤海課長馬上就能放你出去。”
我還沒等小榮說完,就打斷他的話,怒吼道:“你們說的話我聽不懂,你們想弄死我就趕快動手吧,何必多說這麼多廢話?”
伊藤海勃然大怒,拍著桌子大罵,又對外說了幾句日本話,幾名日本憲兵進來,一個手裡端著一大盤辣椒油,一個手裡拿著灌腸器,他們把我按倒在地,用灌腸器向我的鼻孔裡注射辣椒油,這些辣椒油迅速填滿了我的鼻子、嘴巴、喉嚨,我眼前一陣火花冒出,緊接著一片烏黑,我又死了過去。
自從我被灌了辣椒油,八天沒有再審我,這群禽獸見嚴刑拷打和酷刑都沒能撬開我的嘴,便改變了套路,變成了軟硬兼施的方法,有時審訊時抽我幾鞭子,有時語氣溫和、甜言蜜語,或者用金錢誘惑。任憑他們使用什麼計策,我雖然每天飽受肉體的折磨,但我堅持說什麼都不知道。
最後,他們拿我沒有辦法,把我送到唐山憲兵隊,唐山憲兵隊隊長藤淺雄,想出更絕的招數,他們把我白髮蒼蒼的父親抓進了監獄,威脅我做他們的密探,否則就會將我和我的父親一起槍斃。
我不忍心看到我年邁的父親,一樣受到我經歷的酷刑,就假裝答應了他們的要求。
他們終於把我放出來了,並給我了一本北平、天津、唐山地區的通行證,我利用這個證件,以日軍密探的身份,暗地裡解救了一些愛國人士,並將日軍一批機要檔案偷到手,然後趁機逃了出來。
我終於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但是,可憐我那老父親,自從日本鬼子發現我逃走後,他被那群豺狼拉到街口,當眾砍頭了。
說到這,耿全民已泣不成聲。 這位年僅19歲的學生,左側耳朵已被打聾,四根手指只剩半截,右腿已殘廢只能拖著腿走路,嗓子已爛說話低沉沙啞,如果他不說,誰都以為眼前的這位面黃肌瘦、佝僂著身子的男人是個40歲以上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