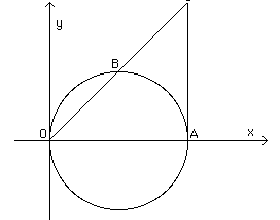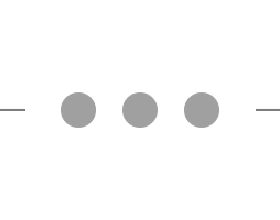王懷軒

普內比米爾玄武岩石碑,曼徹斯特博物館藏,8134號,出土於埃及,具體地點不明,高40.5釐米,寬28.5釐米,厚5釐米,1959年1月由馬克斯·E.羅比諾私人捐贈
普內比米爾玄武岩石碑是2021年中華世紀壇“遇見古埃及:黃金木乃伊”展出的藏品之一,長期儲存在曼徹斯特博物館(第8134號),出土於埃及,具體地點不明,高40.5釐米,寬28.5釐米,厚5釐米,1959年1月由馬克斯·E. 羅比諾捐予曼徹斯特博物館。
對於後期埃及而言,如何在記憶中貯留已然為“帝國”所撕裂的文化,是一個永恆的主題。自公元前一千紀伊始,底比斯祭司便開啟了對於神聖信仰的再造,力圖透過轉向內在而彌合日漸崩解的埃及世界。此後,無論是利比亞新貴的“埃及化”,抑或是努比亞治世和第二十六王朝的“復古”,皆是古埃及文明重新整合“自我”與“他者”、“過去”與“現在”的重要努力。到了馬其頓征服以降的托勒密時代,這種對於既往傳統的追尋和安頓更是達到了巔峰。當然,面向過去的“迴歸”其實本身就蘊含著新的革命性元素,這也使得托勒密埃及的聖與俗更顯多元而立體。
這在普內比米爾(Pw-nb-im-ir, Pawer)的圓頂獻祭碑中可見一斑。該碑共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為獻祭影象,下部為五欄銘文,圖文之間呈並置關係。其中,獻祭者普內比米爾身著祭祀衣裙,左手持薰香,右手呈祈禱狀,他的身前擺放著古埃及傳統的貢桌,上置用於進獻的膏油和穀物。左側的神祇先後是以木乃伊姿態出現的奧塞里斯、伊西斯和奈芙蒂斯,前者手持埃及國王特有連枷與拂塵、頭戴“阿太夫”王冠,兩位女神亦手握權杖,並分別冠以相應的神冕,與其聖書體神名呼應。神與人、乃至諸神相互之間的身高比例也彰顯出了明確的尊卑次序。在獻祭影象上方,還有一個帶翼的太陽圓盤。銘文首先載述了神祇序列,包括“逝者與阿拜多斯之主”普塔-索卡爾-奧塞里斯、“聖潔女神”伊西斯和“偉大的”奈芙蒂斯。隨後,銘文還鐫刻了獻祭者普內比米爾本人及其父圖特、母塔霍爾之名。
和托勒密時期重要的“希臘化”風潮迥異,普內比米爾的獻祭石碑完全是典型的埃及式樣,沿襲了自古以來的銘文程式與藝術法則,幾乎沒有希臘等異族文化元素出現。這便包括古埃及藝術傳統中的正面側身率、假想透明等方法特徵以及如上所述的比例構圖原則。實際上,在古埃及傳統中,以“Htp di nsw(國王所獻祭品)”開頭的獻祭碑文歷史極為悠久,早在普內比米爾數千年前便已出現,並一直延續到托勒密時期,成為布克哈特所言的那種“神聖的終止”,或曰“埃及人的法則”。不過,這種永恆性和程式性,恰恰是其宗教神聖性的不二來源;也正是由此,它才能夠與流動的世俗世界截然二分,成為某種能夠真正安頓心靈的依歸。因而,當帝國崩潰以降古埃及人與周邊諸文明的接觸愈發密切甚至日顯弱勢之時,作為神聖存在的傳統程式——無論是獻祭碑銘還是藝術法則等——非但沒有被外來文化所簡單地代替,反而是更為突出地彌散到了社會的各個角落,甚至“征服”了無數異邦人。
然而,在普內比米爾石碑上,身處希臘化之際的時代特色同樣也是極其明顯的。一方面,即便獻祭場景中的基本元素與比例法則依舊一如既往,但與通常只出現一位神祇的傳統不同,此處受到供奉的神卻高達三位。另一方面,普內比米爾石碑的銘文雖大抵沿襲程式,但同樣迥異於傳統:儘管其主要部分仍是由聖書體書寫,但在第一欄中卻使用了世俗體文字,這種托勒密時代的風尚甚至在晚王朝時期都是難以想見的。而在神祇序列中提及奧塞里斯之時,亦使用了托勒密時期的特有名謂,即“普塔-索卡爾-奧塞里斯”。與此同時,從石碑的雕刻和銘文所言來看,普內比米爾的身份可能不盡尊崇,但他在畫面中的身高卻甚至與諸神不相上下——在新王國崩潰以前,這幾乎只是神聖王權的殊榮。不難看出,在普內比米爾所處的晚期埃及,既有的“禮制”已經得到了極大程度的“僭越”乃至顛覆,神聖與凡俗的界限似乎變得只是“煞有介事”了。
事實上,這一“逸出正軌”的“非禮”可能也是晚期埃及人在傳統與現實的巨大張力面前所進行的某種轉圜。與新王國以前之自在發展和帝國時代的兼收幷蓄皆為不同,拉美西斯王朝晚期以來的古埃及人先後面臨著利比亞人和海上民族所帶來的衝擊、前者與努比亞人的先後之徵服,乃至亞述人、波斯人、馬其頓人等外來文明對於本土政權的釜底抽薪。在這一鐵器帝國紛紛崛起、並以昔日之“野蠻”征服“文明”的時代,包括埃及在內的諸早期高階文化紛紛以轉向內在的方式賡衍著日漸衰微的傳統。不過,阿斯曼等學者即指出,與其他走向將文字“正典化”的諸文明不同,晚期埃及人是以神廟這種“把神聖文獻實體化了的‘平面圖(snt)’”載刻其文化記憶。其中,和影象互為表裡的古埃及人象形文字即透過不斷地擴充符號以儘可能留住整個埃及世界。與此相呼應,在諸如普內比米爾石碑等物質載體中,作為影象的諸神、聖書等也便不斷增多。這種所謂的“氾濫”,與其說是神聖觀念的消解,毋寧說是其對於自身世界的反思與迴護。而之所以能夠“禮崩樂壞”,根本上則是由於既有禮制所依附的神聖載體業已悄然發生了變化:在傳統的埃及社會中,這便是神聖的王權本身;而當王權經由晚期帝國之衰微、第三中間期時代的幾度崩解,乃至波斯和馬其頓人所帶來的異族創傷之時,面目全非而徒有其名的“法老”,顯然已經不再能夠安頓傳統文化與埃及人的內心世界;取而代之的,便是帝國晚期以來的神廟及其祭司——亦即彼時埃及的文化精英。正因如此,既然王權已經不再神聖,那麼由其而生的諸般禮制也就沒有了延續的必要,神廟、“生命之屋”乃至每個人的內心世界成為了真正的舞臺,嶄新的“禮制”遂應運而生。
這便是一種基於時移與世易的“逸出正軌”:雖然包括希臘在內的諸異族文化並沒有完全消解古埃及的歷史傳統,甚至反而刺激了其對於“自我認同”的追尋,但“他者”所帶來的衝擊與震撼卻是極為強勁而真切的。這意味著,對於普內比米爾這樣的晚期文化精英而言,即便自身身份不盡顯要,但在托勒密時代的“雙面社會”中,如何於神聖的傳統與凡俗的世界中求得某種平衡,從而既為他者“解密”,又使自己得以寬釋,依然是一個極為嚴峻且無以迴避的問題。當然,也正因普內比米爾只是一位普通的古埃及文化精英,才使得某些不太拘泥於傳統與時代程式的“僭越”更為彰顯。然而,站在歷史的角度,這種禮制層面的“僭越”卻反而呈現出了諸文化間的碰撞與交融,及其在藝術創作領域所迸發出的獨特活力。在此意義上,帝國乃至諸如此類的所謂“政治”成就也便不再是衡量文明高度的絕對尺度。事實上,可能恰恰是在這種“亂世”乃至“末世”之中,難見於真正“盛世”星空中的繽紛色彩方才得以自在滋長,而這也正是普內比米爾石碑在其聖俗之間所凝結的世界圖景。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