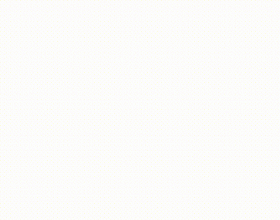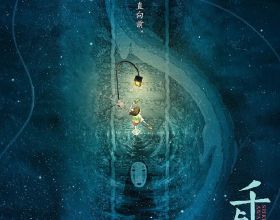我始終相信,一些人披著“人皮”,內在其實是隻“魔”,他們遊蕩人間,一點點開始作“惡”,極善偽裝。驀然回首才驚覺,我與這種人共室了三年。
師大宿舍上下鋪床位有八個。我們七個來得早,各自挑好了床鋪。餘下一個靠門的下鋪空著。冬天一開門,寒風呼呼灌進來,那個鋪首當其衝被最先光顧。
晚上大家一起唧唧喳喳邊聊天,邊吃零食。門開了,豔抱著大包拎著小包進來,她只能睡那個下鋪了。大家七手八腳上前幫忙,鋪床,擺物,一個多小時幹完了。
豔長得纖細柔弱,非常耐看,細長眼,厚嘟唇,有點像名星鞏俐年輕時的模樣。她那雙“千層底”布鞋格外惹眼,低頭坐在鋪上,話不多,也不怎麼吃我們的零食。宿舍裡擺了個大儲物櫃,大家把自己雜七雜八暫時不用的東西擱裡面。那種老式櫃子,沒有鎖。
“我的手錶不見了!”一天,晚自修回來的玲最先發現自己物品丟失,大喊起來。我們都擠過去翻儲物櫃裡自己的東西,“我的洗髮水不見了!”“牛肉乾呢?”“誰看到我的潤膚乳了?”寢室裡亂成一鍋粥,大家七嘴八舌嚷嚷著。
豔幾乎哭出聲來,“我的飯票不見了!”她哽咽著,眼睛裡蓄滿淚水。大家默不作聲地看她。來師大上學的同學,家裡都不富裕,否則也不會高分選擇了免學費的師範大學。而穿“千層底”來上學的女生,全校也是屈指可數。
室長芬帶頭,每人給她湊了些飯票,她期期艾艾地收下了。芬得知她和自己是一個縣城的老鄉時,愛憐地對她說以後自己就是姐姐了。
寢室失竊一案,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大家一起去水房洗漱或洗衣時,讓手腳不乾淨的人鑽空子進去了,並約好以後宿舍集體外出時,輪流看守物品。
芬年齡最大,性格陽光開朗。復讀了兩年才考上這所師大。靠姐姐中途輟學打工掙錢供她唸書。她眨巴著一雙長睫告訴我們,導致她學習分心的是青梅竹馬的男友小凱。他倆初中就談了,小凱先追的她,又雙雙考入同一所高中。
第一年倆人同時復讀,小凱再次落榜後跟著當包工頭的父親做工程賺錢去了。她沉下心來逼自已考進了師大。眉舒眼笑地講起自己和小凱的美好時光,聽得我們幾個羨慕不已,笑說畢業就等喝她的喜酒了。
豔靜靜聽著,一副柔弱無骨,人見猶憐相。我們的高談闊論她從不表態。影子一樣黏在芬的身前身後。
開學不久,小凱來學校看芬。他英俊瀟灑,風流倜儻,佷會照顧人。我們沾了芬的光,他給芬帶的美食,大多吃進了我們肚子裡。
小凱常抽機會來,芬每回偏心,分給豔的東西份量特別多。小凱帶芬去吃飯,豔偷偷地遠遠跟在他倆後面,被發現了,說自己習慣了和姐姐待一起,芬不忍她獨自回學校,就喊她一起吃飯、看電影。後來,每次小凱來,芬就喊上豔一起外出。
冬天的北風呼嘯而至。晚上,豔哼哼唧唧喊冷,一幅弱不禁風的樣子,芬當即和她調換了鋪位,看得我們只有眼熱的份兒。
“小玉,”玲神神秘秘地攔住去圖書館的我,她四下望去,見周圍沒人說:“前天中午,我不舒服,沒吃飯,就回宿舍睡覺。門虛掩著,推開,看到豔正翻儲物櫃裡大家的東西,還挑了一些裝進手提袋裡。我問她幹嘛,她說芬姐叫她找東西,我看到自己的手鍊在她袋子裡,就伸手拿了出來,生氣地警告她下不為例。她淚水漣漣地說拿錯東西了。”“我懷疑以前丟的東西和她有關!”玲急切地說。
我不置可否,笑著安撫她:“好啦,開玩笑可以,真說出去就是造謠了。”內心深處不相信長著一雙人畜無害清亮眼睛的豔是個手腳不乾淨的人。
然而,事實往往令人始料未及。
那次體育課,我的腳輕微扭傷,回寢室休息。或許鑰匙的轉動無聲,或許是豔太專注。她正把大家的沐浴露、洗髮水挨個往手邊兩個瓶子裡倒,動作嫻熟流暢到震驚了我。呆立良久,才反應過來,大聲呵斥:“你在幹什麼!”
她住了手,卻也不慌不忙。幾秒後,淚如雨下,說起自己長年臥床的父親及腿腳不便的母親,說起自家那間堆滿廢品的家。又說她知道這麼做很丟人,卻更怕被大家瞧不起。我沉浸在她悲傷的故事裡不能自拔,對她心生憐憫,一直安慰她。
我沒告訴其他人,可大家不約而同做法一致。除了玲常私下叨唸豔不是什麼好人外,剩下的六人無論誰去洗頭洗澡、冼衣服,會叫她一起去,想幫她省洗護用品。
時光荏苒間,到了大三。豔一直都是“熊貓”級待遇,她心安理得的享受特殊關照。連大學輔導員那個年近半百的"大叔”,隔三差五就召我們幾個開會,含沙射影暗示要團結,互幫互助。我瞬間想起上次在校園角落那棵老槐樹下,輔導員“安慰”哭得“梨花帶雨”的豔,清楚地看到輔導員攬她入懷,替她擦淚的情景。當時莫名覺得不可思議,繞道逃了。
每次班裡助學金是豔的,連獎學金名單裡也有成績平平的她。她是我們八個裡最先入黨的。大家心裡都覺得有失公平,可是看到她那弱柳扶風的樣子,沒人在她面前提過一句。
又是週六,我和玲在街上逛累了,咬牙奢侈了一回,坐在商場轉角處喝著鮮榨果汁。突然,玲拽我比劃著叫我朝前看。商場裡如織的人流中,小凱擁著豔,說說笑笑朝外走,豔一改昔日困苦樸素的穿衣風,散開的一肩長髮灑脫飄逸,一襲粉藍小短裙,襯得她如清水剛出的芙蓉,清新雅麗。我和玲瞪大眼睛瞠目結舌,顧不上喝手裡的果汁,追了出去。
他們一起進了賓館。我死死盯住賓館門,玲找公用電話撥通了寢室電話。芬剛洗完澡回來,聽完,哈哈大笑說我們認錯人了,她昨天親自送小凱上了回去的車。玲又賭咒又發毒誓地告訴她千真萬確。芬這才尋找豔,誰都不知道豔去了哪兒。她打了計程車趕來。
芬報了小凱的身份證號,果然開了208號房,他萬萬料不到芬會來吧。
芬渾身顫慄不止,大口喘著氣,我和玲幾乎是抱著她去找到的房號。她氣得失了智,未到門口就大喊男友名。好一陣兒,門才開,小凱和豔穿戴整齊地站著。“芬,別多想,她是你妹妹,也是我妹妹……”豔站在小凱身後,一臉嬌羞透著雲淡風輕。昔日那個百依百順唯唯諾諾的豔全然不見了。
芬疾步走向雙人床,一把掀開凌亂的被褥,裡面有條粉色的女人內褲。“這是什麼!叫我別多想,你們做了什麼!”芬怒不可遏地吼著,大顆大顆淚珠從臉上滑落。“我倒要看看你這個賤貨不穿內褲什麼樣!”芬撲過去撕扯豔的裙子,她用手拼命護著。“滾開!你瘋了,要幹什麼!”小凱衝過來一把推開了芬。“我喜歡她的柔弱溫和,準備過幾天跟你說,既然已經知道了,那擇日不如撞日。”他橫在豔前面斬釘截鐵地說。
“啪”芬甩了他一耳光,扭頭就走。我倆緊跟在她身後出來。剛出賓館門,小凱追了過來說:“等一等,這五十萬,算是我對你的補償再多我也沒了。”說著,他將一張存拆放在芬手上,轉身回去了。
玲怕芬氣瘋了撕掉存摺,趕緊從她手裡奪過來保管。“放心,我還沒傻,錢我要!”芬一字一頓地說。
豔搬下了一樓。我們只當從來不認識她。每天都為芬擔憂,她吃得少,睡得更少,失去了昔日的陽光開朗。一個勁兒拼命用功學習,話也少了。
豔搬走一個月後,芬的心情逐漸有一絲絲好轉。一個隔壁大二女孩來借書,看到正喝水的玲,驚訝地說:“你怎麼用豔的杯子?她天天中午回寢室喝水。”我們警覺地逐一查了所有東西,沒有丟失!
大家商量著換把新鎖,還沒有來得及落實。更可怕的事就來了。
豔在體檢中查出了乙肝大三陽,傳染性強。校醫來找我們說豔半個月前就確診乙肝了,一樓的她獨自隔離居住。要我們這些密接觸者全部去檢查是否被傳染。
“隔壁女孩上週中午看到她進我們寢室,還用我杯子喝水?她會不會…”玲提醒大家,“別急,明早抽血看結果再說。”芬安撫大家,我們都很沮喪,也無比震驚憤怒,她居然如此惡毒。
芬徹底爆發了,她把攢了很久的怒一起發洩出來。當晚她說去圖書館自修晚回。
第二天,我們才知道芬出事了。她把豔打傷了。豔在醫院躺了兩個多月。因為小凱的斡旋,芬沒有賠償。她退了學,去了廣州做生意。那次體檢抽血查肝功,大家也沒有被豔傳染上。
畢業後,大家各奔前程,各自忙碌。歲月漸行,聯絡也越來越少,只知道芬創業成功當了大老闆,卻至今未婚。
小凱娶了豔,婚後幾年投資失敗,豔離婚捲走了他剩餘的錢消失了好幾年。這幾年聽說嫁給了一個有錢人,只是肝硬化很嚴重,終日輾轉於治病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