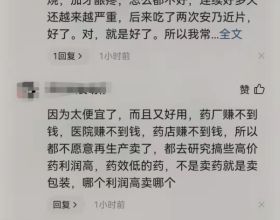小時候生長在關中農村,可以說,是在吆喝聲中逐漸長大。
挑著擔子的貨郎進村了,一聲聲的吆喝中,婦女們各自理理亂蓬蓬的毛髮,走到貨郎面前,買上幾枚針、幾個暗釦,一盤線,也或者幾個皮筋。走街串巷的貨郎渴了,離誰家近,就很熟絡地串進門去,就著水缸痛快地喝上一肚子生水,然後,回到自己的“貨架”旁,跟一幫圍攏來的婦女磨嘴皮。村婦們多半並不扭捏,很大方地讓貨郎給他們再多點優惠,貨郎有時應允有時拒絕,訴說他的辛苦和不易。多數時候,雙方在磨嘰一陣後,也就達成一致;少數時候,碰到一些“不顧臉面”的厲害媳婦,明明人家貨郎沒同意,硬是隻放下她願意給的數,然後拿上自己中意的東西,化作一陣風,跑了。
“哎,你這人咋是這,啥人嗎?簡直跟強盜差不多。”臉色難看的貨郎的疾言厲色,只能讓風聽給風看了。
小時候的鄉村安靜且寂寞,所以時常盼貨郎。因為每次貨郎來了,必然會像過節似的熱鬧個一時三刻。
最初的貨郎是挑著擔子,隨後有了架子車,不管是挑著擔還是拉著車,那時的貨郎都著實令人羨慕。貨郎的賣貨筐,在那時的我看來,簡直像是無底的百寶箱,要啥有啥。還好那時的我年紀尚小,不懂什麼叫情竇初開,不然,怕是定會戀上那些神奇的賣貨郎。
那時候的一切生活必需品,來源似乎都是各色走村串巷的賣貨郎。
賣醬油的來了,一聲吆喝,人們圍攏了來;賣冰棒的來了,一聲喊叫,人們走上前去。還有賣韭菜的、賣大蒜的、賣瓦罐的、賣甕的。賣豆腐的吆喝聲很有特色,好像那一聲豆腐的吆喝,經常是在凌晨的五六點,豆腐郎吆喝的時候,一般是先發出一個悠遠綿長的“賣……”,猶如老師講課前,先整肅課堂紀律,然後,在人們都屏聲靜氣,靜待下文的時候,他才不緊不慢地喊出拉長腔的“豆腐”,而且,最末的“腐”字音調上揚,實在是極有韻味。
同賣豆腐幾乎同樣勤勞的,要數賣甑糕的。賣甑糕的吆喝聲跟賣豆腐的又略有不同。雖然他也一樣是拉長了“賣”字的發音,但“甑糕”二字的發音比起“豆腐”,似乎要平緩一些。反正,時間一長,大家也都摸清了規律,外面一吆喝,就知道是誰的豆腐誰的甑糕,並能根據各自耳畔的聲音準確地判斷出,這賣豆腐或者賣甑糕的,離自家還有多遠的距離,再然後,估摸著時間去到各自的家門口,割些豆腐或者買點甑糕。
那時候的甑糕屬於貴重食品,當然沒有誰家會鋪張到天天都吃。只在偶爾,買上一點,一家人嚐個鮮,解個饞,就已經很幸福;那時候的豆腐原汁原味,如果沒有口福,聞聞也很不錯;那時候的韭菜味道噴香,是家常臊子的絕對主角;那時候的醋,在我的記憶裡也有著濃墨重彩的一筆。
賣醋郎出現時多半會拉著架子車。架子車上有個形狀很像碌碡的木桶,車走在高低不平,坑坑窪窪的村道上,難免顛簸,顛得厲害時,就會有醋溢位桶口。這些溢位桶口的醋,就成了孩子們的眼中的寶物。
孩子們跟在賣醋郎身後,眼巴巴地等著他早點停車,及至賣醋郎終於選定位置,車子還未完全停穩,就有孩子撲到醋桶跟前,站在架子車後方,貪婪地吮吸起桶口溢位的醋來。實話說,味道實在好極。偶爾,趕上醋郎心情好,會很慷慨地從醋桶舀出半勺,讓圍著醋桶轉悠的孩子們輪流喝上一口。老實說,比後來城市裡流行的醋飲營養美味的多了呢。
如今的鄉村,都在忙著搞城鎮化,城鎮化後的鄉村,商店、小賣部甚至超市一應俱全。屬於貨郎們的時代和屬於我們兒時的那些快樂,必然會隨著時代的發展逐漸消失甚至徹底銷聲匿跡,然而又似乎,無聊的午後、遙遠的清晨的那些各式各樣的呼喊,時不時地,還會來撞擊我的耳膜。
“賣……豆腐
賣……甑糕
賣醬油嘍
賣粉條哩
補鍋
磨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