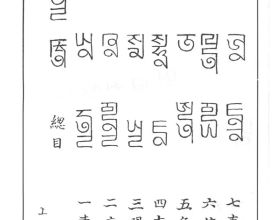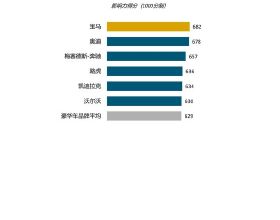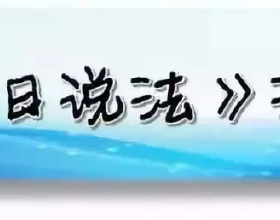2018年6月中旬,我應邀赴斯德哥爾摩參加瑞典皇家理工學院的一次博士論文答辯。答辯開始之前,我問參會的教授們:“維納死在哪裡?”沒想到,來自歐美五國的五位同事和當地的教授不但不知道,有的還反問:“Who is Norbert Wiener?”
原來,這裡沒人知道鼎鼎大名的控制論之父,更不知道他就死在大家的身邊。
次日,順利完成答辯的新科博士幫我找到了維納的去世地點——1964年3月18日下午,“就在那長長的臺階之上,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呼吸也隨之停止。”
我正詫異,這臺階分明只是寬而已,其實一點也不長,難道是後來改建了?疑惑之際,藍天白雲之下,忽然一陣大風襲來,我急忙轉身並扣住帽子,結果動作太急、墨鏡落地。待我站穩睜開眼睛,卻直覺得一團烈火撲來,原來是辦公樓前的簇簇紅花。
這一切,來得如此急促,讓我一時頭暈目眩、不知所措,腦中竟奇怪地閃現出維納生前的自我評價——
他就是盜火給人類而犧牲了自己的普羅米修斯,把智慧機器的“自動智慧”新技術帶給了人類,卻擔心人類屈從於機器、放棄選擇和控制的權利,內心總是充滿了一種即將來臨的“悲劇感”,“覺得自己是一個會給人類帶來災難的先知”。
2018年6月,由金峻臣博士抓拍於維納猝死之地。
催生了三個諾獎
其實,縱觀維納的一生,悲劇是其脫不掉的底色。
猝死之後,他的批評者說,其瑞典之行是“覬覦諾貝爾獎”的一次遊說之旅;但支持者反駁,維納訪問瑞典就是傳播控制論,並非乞求諾貝爾獎委員會。
他們也許都忘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維納的工作曾經直接幫助四人獲得三個諾貝爾獎:玻恩(1954年物理學獎)、海森堡(1932年物理學獎)、沃森和克里克(1963年生理學或醫學獎),他們在獲獎時或者獲獎前都公開承認維納對他們工作的重大貢獻。
1925年,玻恩曾親赴麻省理工學院(MIT),直接和維納合作。他需要維納的幫助,試圖調和搖搖欲墜的原子粒子模型與突如其來的波函式之間的關係。儘管兩人合作發表的論文奠定了量子力學的基石,但玻恩承認他沒有完全理解維納的計算方法,也“幾乎沒有接受”維納的波函數理論的核心概念。
然而,數年後,玻恩因“對波函式的統計闡釋”獲得了諾貝爾獎,並公開承認維納是“卓越的合作者”。
1927年,玻恩的學生海森堡運用維納在“幾年前......在哥廷根介紹過”的諧波分析方法得出他著名的不確定性原理,後因此獲諾貝爾獎。
按維納自己的說法,他10歲時,完成的第一篇哲學論文《無知理論》就討論了所有知識的不完整性,成了他終生的理念,而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原理不過是其一個具體的體現而已。
1951年,年輕的沃森來到劍橋大學。此時,正值維納的控制論在英國的影響達到高潮,這引發了沃森和克里克利用控制論分析遺傳物質DNA分子結構的想法。1953年,他們給《自然》雜誌寫信,提出“控制論將在細菌層面的研究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的論斷。幾周後,他們公佈了DNA的分子結構與模型,由此獲得諾貝爾獎。
克里克隨後正式提出的“資訊是生物系統的一項基本屬性“觀點,清晰地揭示了生命的新奧秘,但其運用的模式和“10年前維納提出的模式驚人地相似”。
面對這些諾貝爾獎,無人知道維納內心的真實感受,他是否認為自己也應該得諾貝爾獎呢?世人不得而知。可以確定的一點是,維納覺得世人沒有給他合適的讚揚,這是他患狂躁抑鬱性精神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並終生受其所害。
正如維納女兒所說的,“我父親永遠要求得到大量的稱讚和安慰,他處於情感混亂時需要得到更多。”
《維納傳:資訊時代的黑色英雄》,作者:[美]弗洛·康韋、[美]吉姆·西格爾曼,譯者:張國慶,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8月版。
悲劇人生
然而,維納在這一方面不但“供需嚴重失衡”,並由此陷入了個人生活的悲劇。
這位20世紀的少年天才、美國首批媒體的寵兒和明星,在遭遇兩位心上人的“十動然拒”之後,不得不與父母安排的、但內心一直拒絕的女友結婚。
婚後,這位教授夫人儘管在生活上給予維納精心照料,但是她的主要心思花在如何控制維納的情感和“朋友圈“,成了家裡的控制“控制論大師的大師”,在社交圈裡贏得“名譽教授(Frau-Professorship)”的稱號——維納一高興,就想著如何讓他“抑鬱”,便於控制;一旦看到維納與自己不喜歡的人太親密,便想方設法進行破環,甚至不惜拿女兒的貞潔名譽作為“核武器”,誣告維納學術上的關鍵同事設局讓維納的“不止一個”學生誘姦其女兒。
這場悲劇不僅是維納個人家庭的,更改變了人工智慧發展的歷史程序。多少年後,人們才知道,這便是長期令人困惑的控制論“金三角”(維納、麥卡洛克、皮茨)破裂的神秘原因。
我在美國學習與工作時,有幸結識了一批猶太裔學者和朋友。他們告訴我許多與維納相關的故事和傳說,特別是那些來自東歐的朋友,描述了很多關於上世紀70年代之前美國學界有種族歧視傾向的白人和猶太裔學者之間的衝突與糾結,維納及其控制論就是這些故事中最精彩的篇章。
《維納傳:資訊時代的黑色英雄》英文版封面
記得《維納傳:資訊時代的黑色英雄》英文原版一出,同系的猶太裔同事Russ就興沖沖地拿著他買的書來辦公室找我,讓我一定讀一下,“終於有人給維納伸張正義了!”這本書深深地吸引了我,但當時沒時間細讀。
十年後,我有幸獲得維納獎,於是又託美國的學生專門為我再買了一本寄回國內細讀並做了大量筆記,讓我對維納本人和他所處的時代及相關技術的發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2015年10月,在香港IEEESMC(系統、人、控制論)學會年會上,我作了維納獎講座的學術報告,核心之一就是平行智慧控制與“維納運動”及其學術之道,引用了《維納傳》中“維納小道”三部曲中大量史料。
我還曾一度安排學生專門做這一方面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研究,但因內容不符合理工科的學位要求而作罷,這也是為什麼我積極參與並推動重新設立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主要原因之一。
這是一本傳記,但更是一部傳奇,因為它不但揭示了現代智慧科技的源頭與發展,真實地敘述了人類社會及其時代對技術進步的嚮往與恐懼。更重要的是,本書透過一批科技發展引領人物的探索與努力,直指人心的深處與遠處。我相信每一個讀者都會發現自己欣賞本書的角度,找到自己希望的東西。
在此,我羅列三個問題,以饗讀者。這三個問題在相關學術界裡廣泛流傳,但與所謂的科學“正史”相悖,卻與本書有著書裡書外、千絲萬縷的關聯,可供大家在閱讀時思考。
現代計算機的先驅?
眾所周知,今日的計算機都是基於所謂的“馮·諾伊曼體系結構”,但真名應是“維納-馮諾伊曼體系結構”還是“馮·諾伊曼體系結構”?
維納從上世紀20年代初就開始現代計算機的研究,早於目前已知的絕大多數現代計算機先驅,並於1925年秋與MIT工程系的新秀、二戰時的美國軍事科研的領袖、且在戰後以《科學:無盡的前沿》而聞名的布什進行相關合作。布什不但承認維納的方法具有相當大的應用價值,並在他的成名專著中進行介紹。
1936年,維納來清華任教,同他的第一個博士畢業生李鬱榮教授一起提出了離散計算機的設想,並安排清華大學向MIT購買相應裝置器件,希望進行實驗,可惜因種種原因被時任MIT工學院院長的布什否定。
美國參加二戰後,維納於1940年再次向布什提出現代計算機設計的“五項原則”,依然沒有回應。
馮·諾伊曼最初參加控制論“梅西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維納關於計算機設計的思想,這讓維納十分興奮,產生了把馮·諾伊曼從普林斯頓“挖”到MIT做數學系主任一起共事的想法,並立即付諸行動。為此,維納於1944年底將美國研究電子計算和相關技術領域的頂級數學家以及人工神經元網路計算的主要理論家召集起來,與馮·諾伊曼在普林斯頓開了為期兩天的會。
後來,還把他在這一方面研究最得力的助手介紹給馮·諾伊曼,推進相關工作,並終於在1945年6月底正式提出了今天被稱為“馮·諾伊曼體系結構”的現代計算機體系結構。
按照馮·諾伊曼自己的描述,其計算機是第一臺“將維納提交給布什的五條原則整合為一的機器”。
這就是為何美國軍方和學界有人認為:“馮諾伊曼體系結構”的真名應該是“維納-馮諾伊曼體系結構”的原因。
然而,計算機界人士無人有此提法。實際上,這在1947年於哈佛舉行的世界上第一個重要的計算機大會上就已註定了。
那一年,哈佛物理學家、哈佛Mark計算機的創造者HowardAiken乘完成MarkII之際,召開了一次自動計算機會議,歐美157名大學代表、103名政府代表、75名產業代表與會,但大會期望的主角維納卻因為計算機與“制導導彈專案太緊密”,在最後時刻拒絕參加,不但讓組織者艾肯憤怒,更讓報紙及媒體關注並大肆宣揚,迫使維納私下宣告:“我放棄所有計算機相關的研究”,還公開宣佈:“不再從事和美國政府有關聯的任何研究工作。”
維納從此成了資助艾肯研究的海軍情報機構,接著陸軍空軍情報機構,後來聯邦調查局FBI長達17年的嚴密監視,直到去世。
這樣的後果就是當時研究計算機的人員,包括人工智慧的研究人員,爭先恐後與維納保持安全距離,除了擔心自己的研究經費受影響之外,還擔心受到政府軍方情報部門的騷擾。
現代資訊理論的先烈?
現代資訊理論之父是夏農還是維納?這可能是最讓維納傷心與悲憤的問題。
維納從其學術生涯之始,就萌生了現代通訊與資訊理論的思想,一直把自己視為是資訊時代的“先知和引路人”。
二戰期間,他像幫助自己學生一樣,毫無保留地幫助已經畢業但不斷來MIT找他解疑的夏農,特別是關於熵的研究。但最後,維納卻拒絕再見夏農,因為覺得夏農是來“挖他腦袋”的。
最讓維納惱火的是,他關於現代通訊與資訊理論最核心的研究和成果,卻被夏農的上司(一位數學家)束之高閣,劃為“絕密”材料歸檔,結果只有極少數人才可以看到,而且將其輕蔑稱之為“黃禍”(YellowPerils)。
更可氣的是,夏農與他的這位上司搶在維納之前發表了著名的《通訊的數學原理》,成為現代通訊和資訊理論的奠基之作;而維納因為保密的原因,遲遲無法發表自己的成果。
這就是為什麼至今還有些人為他憤憤不平,認為維納才是資訊理論的真正之父,比如夏農的熵只是把維納的熵改了正負號重新解釋但等於沒改,而夏農主要是靠重新解釋和轉述他人的成果而出名,從布林的代數幹到維納的資訊理論。
夏農也承認,自己通訊理論的“新數學理論的一些中心觀點要歸功於維納”,而且“明確地說,通訊理論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維納的基本哲學和理論。”
夏農晚年也否認“資訊理論”這個詞是他創造的,他的夫人進一步解釋道:“這件事”讓夏農“煩惱過好幾次,但到那時,他也無法控制了。”相當程度上,維納就是為此而發明“控制論”一詞,試圖挽回局面,而且裡面除了通訊、資訊、還加了智慧,但就是少了控制。
同事Russ在哈佛與MIT讀的文學學士和工程博士,他告訴我,維納認為資訊理論方面自己是被犧牲的“先烈”,而且根源是哈佛數學系一幫傳統白人精英對他的“迫害”——
先是讓維納失去了在哈佛數學系任教的機會,失業陷入困境後險些自殺;來到MIT數學系之後,哈佛數學大佬還逼他放棄自己開創的研究方向,以確保大佬自己在普林斯頓的學生沒有競爭對手,順手還堵死了維納希望去普林斯頓的路。
更讓維納氣不過的是,在他事業將要“起飛”的時刻,這些人竟然“追殺”到歐洲,讓他的好朋友與其反目,突然取消承諾給他在哥本哈根的教職,幸虧英國劍橋的朋友救急,否則維納將再一次陷入困境。
正是哈佛數學系對他的這類“打壓”,在隔壁的MIT產生衍生效果,使身邊人肆意掠奪其學術成果,也留下讓後人閒話的維納-哈佛數學系之間糾纏不清的複雜關係。
主流人工智慧的叛徒?
人工智慧的原名是不是就是“控制論Cybernetics”?維納對人工智慧的起步與發展到底做出了多大的貢獻?這是一個極其複雜但又十分有趣的問題,對此我無法回答。但我知道,維納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多大貢獻,特別是他的思路與方法,直到今天才發揮作用,並將在未來的類腦類人和社會智慧研究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實際上,將Cybernetics譯成“控制論”的學者自己也認為,這個詞應該譯成“機械大腦論”,選擇控制而非機械大腦是由於當時政治的原因。
說維納是主流人工智慧的“叛徒”,是因為他背叛了自己從業初期以“邏輯”分析開路的主流“邏輯智慧”的道路,回到自己少年時代以動物生理生物研究和計算手段研究知識和智慧的初心。
他的理念贏得了一大批人、特別是青年學者的支援;他的“迴圈因果論”引起了學者的重視,激發了麥卡洛克和皮茨堅信,大腦的神經元網路連結就是頭尾相連的生物“迴圈因果論“。1943年,兩人提出“人工神經元”計算模型,開闢了計算智慧和認知科學的新時代。
然而,在這之後,維納卻又一次“背叛”了自己的追隨者,在毫無警示的情況下與麥卡洛克和皮茨等人決裂,致使“金三角”頓失。
這就是人工智慧史上無人願意提及的一段黑暗歷史,不但斷送了麥卡洛克和皮茨當時如日中天的學術生涯,後來年輕的皮茨還早早地慘死於急性酒精中毒。
皮茨“深愛著維納,維納給了他從未感受過的父愛。失去維納,他就失去了生活的意義。”這不單是皮茨個人的悲劇,更使計算智慧研究剛剛起步就陷於困境,導致相關研究的有志之士,特別是青年學者紛紛離開維納。
“離維納的控制論越遠越好”,這就是當時提出“人工智慧”一詞的青年人麥卡錫的想法,他曾在“控制論”和“自動機”之間徘徊不定,最後選擇了“人工智慧”。
麥卡錫是1948年在加州理工讀書時聽馮·諾依曼講維納的認知和控制論而萌生了研究智慧計算的想法,後來自己都表示“人工智慧本應叫控制論,也是智慧自動化(Automation of Intelligence)”,其實正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流行的“自動智慧”“自動計算”思想。
就人工智慧而言,正如維納的學生與同事,相當程度上也是敵對者的威斯納所承認的:“稱他為催化劑式的人物還不足以描述他扮演的角色。”
他的另一個學生,也是維納核心圈最年輕的成員塞爾佛裡奇,是人工智慧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關鍵人物,其程式Pandemonian開啟了模式識別和機器自學習的研究,後來與麥卡錫一同組織了1956年的第一次人工智慧研討會後,緊接著又在MIT組織舉辦了第一次認知科學研討會。顯然,他沒有完全背叛維納的理念與方法。
可惜,沒有維納的參與,源頭的控制論面對新生的人工智慧,很快就在“較量中敗下陣來,不僅沒有得到資金的支援,還失去了自己的地盤”,但“維納的科學在科技新時代更廣闊的領地贏得了人心。”
深度學習和Alpha Go的成功,相當程度上證明了維納的遠見,但更重要的是,維納的認識對未來智慧的影響——
一是“資訊的傳播極大提高了人類感覺的閾值......整個世界都被納入人類的感知範圍”;二是為了避免智慧技術“給人類帶來負面影響,唯一的答案在於建造這樣一個社會,它的基礎是人類價值,而不是買賣。”
諾伯特·維納。
同情和尊重之心
二戰之後,維納陸續做出一些令人震驚的舉動:“粗暴地辭去了院士的頭銜”,稱美國科學院是“一幫自私,不負責任的人”;公開寫信登報、在會議雜誌上宣告與美國軍方、大公司、政府斷絕關係,不再為他們從事科研工作,甚至還從MIT的“數學系辭職過50次”......
但在維納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的家庭迎來了一個“巨大的喜訊”——
維納被肯尼迪政府授予美國科學界的最高榮譽“國家科學家獎”,以“表彰美國對他在戰時以及和平時期對科學做出的卓越貢獻的認可和感謝”。共同獲獎的是他的二位老對手和朋友:布什和夏農的上司兼堅定支持者皮爾斯。皮爾斯選擇夏農而忽視維納。
在獲獎時,維納“眼睛裡反射出絢爛的光芒”,其實氣色不佳,臉色蒼白,十分憔悴。此時,他擔心夫人的病情,憂心大女兒因“金三角”事件依然不理家人,甚至電話都不接……獲獎儀式完後,他就接受了荷蘭中央大腦研究所的聘任,啟程赴歐。一個多月後,維納猝死於斯德哥爾摩。
讀《維納傳》,最讓我感觸的是維納對弱勢的同情和尊重之心。
他與自己的第一位博士生李鬱榮的關係,與李鬱榮第的第一位博士生印度人Bose(創造了著名博士音響公司)的關係,與他同強勢白人精英的關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且“對各個國家的古老文化傳統都滿懷敬意”。
在中日之間,他認為當時強大的日本“太勢利”,而選擇任教中國。或許,這與他自己的身世和所受的磨難相關。無論如何,令人敬佩。
1949年末,當雄視天下的波音公司來信向他尋求技術支援時,他把回信公開發表在《大西洋月刊》上,還用了一個具有挑釁意味的標題“一位科學家造反了”。他呼籲從事科研的科學家不參加戰後新的軍事裝備競賽,因為研究成果“可能落入不負責任的軍國主義者手裡,做害人的事情。”
然而,當貧窮的印度政府希望維納赴印指導他們把自己建成“自動化生產巨頭”時,他立即答應,開始了“印度的未來:論建設自動化工廠的重要性”之行,幫助制定發展綱要,成為印度科技發展的一個重要拐點。
維納的夢想是培養一批“體制外的科技工作者”,這一設想對當時印度未來的發展十分有價值。記得30多年前,我實驗室的印度同事告訴我:印度資訊產業和軟體外包企業的發達,就是維納上世紀50年代種下的種子。
有人認為,維納的魅力脫胎於大自然某種魔力,他的思想神秘、深邃、滄桑、難以描述,卻“能喚醒我們沉睡已久的思想與感官”“越過柵欄看見遠方的路”。同事和朋友在他身邊工作時,常有“整個人彷彿得到了昇華”“猛然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這種感覺真是太不可思議了”,“只要和維納交談,你的思維一定能上個新臺階。”
可維納臨終前與之交往最密切的印度教神秘大師卻說:“那就是維納,他是個純粹的人,我知道。”
用時下人工智慧風行的語言說——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不知道維納是何人,但知道自己真的不知道維納對科技特別是智慧科技的貢獻有多大。對我而言,這個世界對維納最大的不公就是把布什列為網際網路第一位先驅(Pioneer),而不是維納——這位現代通訊和網路技術的真正奠基人和賽博空間Cyberspace的創造者。
相當程度上,維納就是資訊時代黑暗的叛徒,未來光明的使者。
參考資料:
[1] F. Conway, J. Siegelman, Dark Hero of the Information Age: In Search of Norbert Wiener The Father of Cybernetics, Basic Books, 2005, New York.
[2] Fei-Yue Wang, From Norbert Wiener to Karl Popper: A Journey of Parallel Cybernetics in Three Worlds, Norbert Wiener Lecture, IEEE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Society, Hong Kong, China SAS, October 11, 2015.
[3] Herman Goldstine, The Computer from Pascal to Von Neuman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J: Princeton, 1980.
[4] Michal Meyer, The Rise and Fall of Vannevar Bush, Distillations, Science History Institute, 2018.
[5] MTR Editors, Claude Shannon: Reluctant Father of the Digital Age, MIT Technology Review, July 1, 2001.
[6] Siobhan Roberts, Claude Shannon, The Father of the Information Age, Turns, Annals of Technology at The New Yorker, April 30, 2016.
[7] Gonzalo Suardiaz, Claude Shannon, the Forgotten Inventor of the Digital Age, BBRA Openmind, April 30, 2021.
上文經出版社和“知識分子”公號授權刊發,作者王飛躍是“諾伯特·維納獎”得主、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研究員。原標題為“維納:控制論之父鮮為人知的悲慘遭遇”。
撰文|王飛躍
編輯|李永博
導語校對|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