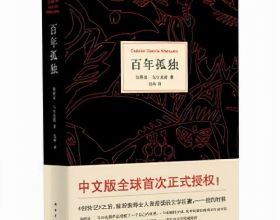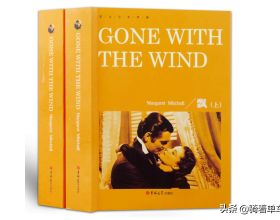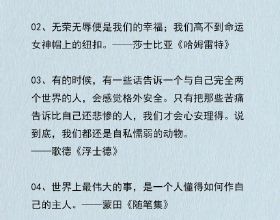中國小康網訊 1956年8月3日,為紀念巴黎聖母院建成610週年,法國和義大利傾其兩國演員豪華陣容,根據雨果原著合拍電影《巴黎聖母院》,於次年殺青。這部長達115分鐘的鴻篇鉅製,完整地再現了雨果原著裡巴黎聖母院的恢弘壯麗,因為是在聖母院裡實地取景,所以成了影史上最經典的版本。
這部最經典的《巴黎聖母院》,於1972年引入我國。不輸於電影裡演員豪華陣容的是,上海電影譯製廠的老一輩藝術家們,也貢獻了超豪華的配音陣容——給主教克洛德配音的是邱嶽峰,給愛斯美拉達配音的是李梓,就連裡面的配角,都是尚華、蘇秀、劉廣寧這樣的“聲音傳奇”。
上海電影譯製廠引進的1956版《巴黎聖母院》海報
經歷了700多年的風風雨雨,巴黎聖母院見證了近代史的重大節點,其中就有不少中外名人與它結緣:貝多芬和拿破崙反目;雨果的同名小說和梁啟超、魯迅介譯的趣聞等等。
因為一首交響曲,貝多芬和拿破崙鬧掰了
231年前的法國 大革命,讓統治法蘭西半島幾個世紀之久的君主制土崩瓦解。肇始於康德的理性精神,加上狄德羅、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等一眾百科全書派的啟蒙浸潤,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等民主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法國人民心中燃起的革命之火,也給宗教的象徵巴黎聖母院改了名字——“理性聖殿”。
革命者中的激進派們,將聖母院裡先賢的雕像當成了反動勢力的泥偶,將之悉數“砍頭”,只有那口“卡西莫多大鐘”倖免於難。“理性聖殿”的地下室,成了藏酒的佳窖。那些以革命果實釀造的芳醇,倒映著巴黎人民狂歡的身影。
然而自由與平等旋即變成了混亂與無序。於是,法國人民將勝利果實拱手讓給了一位掣著革命的電光石火,能以鐵腕恢復秩序的強人,他就是拿破崙。
拿破崙發動“霧月政變”,讓雅各賓派退出“C位”。可接管了革命政府後,拿破崙卻對保皇派和天主教示好,於是他被指竊取了革命果實。遠在萊茵河畔諦聽革命潮響的康德的老鄉——貝多芬,聽到了拿破崙加冕稱帝的訊息,氣憤地將原本獻給他的交響曲譜撕得粉碎。
當然,我們今天仍能幸運地聽到這支差點夭折的交響曲,這便是《英雄交響曲》。讓貝多芬始料未及的是,那幢被啟蒙主義者冠以“理性聖殿”之名的恢弘建築,見證了他倆的反目——拿破崙把加冕典禮的地點,特意選在了巴黎聖母院。
如今,貝多芬的交響依然流淌在人民心中。可是對於拿破崙來說,走向革命反面後的落寞與不安,只有巴黎聖母院那寬厚而博愛的石頭交響,才能夠寄寓撫慰吧。
梁啟超給譯者起名,魯迅給作者起名
梁啟超(左)與魯迅(右)
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部分覺醒的中國人開眼看世界,櫛沐歐風美雨,最先接觸啟蒙思潮的知識分子,開始大力譯介西方優秀文明成果。其中,就包括《巴黎聖母院》作者——維克多·雨果的作品。
大家也許想象不到,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孽海花》的作者,筆名“東亞病夫”的曾樸,就是《巴黎聖母院》最早的譯者之一。
“東亞病夫”這個詞最早現於晚清上海的《字林西報》,出自梁啟超的譯文:“東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作為我國近代啟蒙思潮的先行者,曾樸將梁啟超的譯名作為自己的筆名,箇中便有發奮自勵的緣由。
曾樸自晚清時期,就開始大量介譯雨果的作品,是雨果名著《九三年》、《笑面人》等名著的最早譯者。而翻譯《巴黎聖母院》時,卻到了上世紀二十年代,他的思想也由改良主義傾向於革命。當時的原著譯名,則直接取自書中男主角卡西莫多——《鐘樓怪人》。
1927年,曾樸創辦了“真善美書店”,“真善美”正是法國 大革命時期的文學口號。於同年出版的《鐘樓怪人》,就是他的“開店首發”之一。卡西莫多——這位相貌奇醜無比,卻心地極其善良的敲鐘人,正是被壓迫的底層人民的代表,曾樸將他作為真善美的代言人,從側面體現了那個年代的革命想象。
曾樸版《巴黎聖母院》,作者雨果譯作“囂俄”,名字非常革命化。可惜,這個譯名卻不是這位當時介譯雨果作品最多的譯者的首創。“囂俄”來自於另一位著名文學家的手筆——
1903年,還是日本東京留學生的魯迅,發表了我國第一部雨果小說譯作《哀塵》,作者署名“囂俄”。雖然《哀塵》不是《巴黎聖母院》,而是雨果另一部鉅作《悲慘世界》。但“囂俄”這個名字,卻印在了民國時期各個版本的《巴黎聖母院》的作者欄,這也是魯迅對我國譯介史的貢獻之一了。(子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