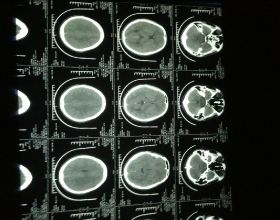東京、江戶,兩個不同的名字,命名了同一座城市的今與昔。東京,這座2020年的現代都會,白日裡折射著陽光的玻璃穹頂與夜晚閃爍的巨大電子螢幕交相輝映,濃烈的現代文明氣息充溢在空氣的每一奈米之中,高聳的東京晴空塔是構建在都會繁榮之上的高傲,與趕著去上班的西裝革履裹著的冷漠,似乎構成了東京人的主要氣質。
但翻開江戶的一面,三個世紀前的歲月中,高聳的江戶城堡裡,錦衣玉食的將軍和他的眷屬高踞其中,恪守武家禮法。但在他們鮮少投下目光的下町平民居所,卻充滿了喧囂歡鬧,草臺班子上演著時下流行的乞丐歌舞伎,江湖郎中售賣來源可疑的偏方,藝伎在遊館中接客,論金賣笑。還有一群放蕩不羈的傢伙,他們衣著看似質樸,卻品位不凡,他們嬉笑著、歡鬧著、吵鬧、打罵,他們在大人物的眼皮下過著屬於自己有聲有色的生活——他們是一群“江戶子”。
“粹”:成為“江戶子”
即使在今天的東京,江戶子也是一個諧趣的名詞,意義之豐富,遠超它們字面的含義“出生在江戶的人”。在今人眼中,江戶子與御宅族有著某種親緣關係,熱播泡麵番《磯部磯兵衛物語》的主人公磯部磯兵衛就是這樣一位江戶子,“早晨起來吃了早飯出了家門,走路去了學校,然後坐在位子上和中島閒聊,上課後就睡著了”——簡直是一個社會閒散人員的形象。他最大的發明就是發現把腦袋貼在牆上平躺著是最舒服、最放鬆的姿勢。他讓人印象深刻的名言是:
“雖然我啥都沒幹,真是辛苦自己了。”
但這真的就是江戶子的生活狀態嗎?解答這個問題的關鍵,自然不在一部21世紀的動畫片裡,而在那座已經被現代文明重重覆壓在地下的江戶城裡。
江戶城的開創,有許多傳說,其中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江戶選址的因由:兩泡尿。
戰國時代的兩大豪傑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在對著小田原方向撒尿時達成了一個約定,豐臣秀吉將江戶與圍繞著它的領地作為封賞賜給德川家康。儘管表面看起來豐臣秀吉相當慷慨,但其內心卻暗藏玄機,他指望以此讓德川家康遠離當時的權力中心京都。但德川家康卻另有盤算:雖然此時的江戶只是片蚊蟲猖獗、蘆葦叢生的海灣,但他卻從中看到了無限的遠景。他在這裡修建了雄偉的江戶城堡。城下的護城河、房屋和街道則構成了環繞於它之下的“城下町”。江戶城由此建立,並在未來的兩個世紀初,成為號稱有著“八百八町”的江戶城。
德川家康像,被認為是其三方原戰敗後特意請畫師狩野探幽描繪自己慘敗時的落魄樣貌,以志不忘,但這則傳說實際上是明治時代以訛傳訛的傳言。這幅畫真正的名字是“家康公長筱戰役小具足著用之像”。
兩泡尿最終誕育出一座人口達到百萬之數的繁盛都會,不能不說給人一種荒誕不經之感。或許從江戶誕生伊始,這種荒誕不經就作為一種城市性格深植其中。未來,江戶子的性情也由這種不羈衍生而來。這種不羈可以擴展出一種豪邁的意氣,也就是江戶子所謂的“粹”。這是江戶子自尊意識的根本。所謂的“粹”,在江戶讀作“iki”,與“意氣”的發音相同。它是指那種活力與魅力並舉,喜好新奇而又注重品位的氣質。
對江戶這座城市來說,近水樓臺的精神氣質便是所謂的武士精神。儘管這種武士精神多少是文學小說創造出的神話——當武士在戰場上搏殺時,很難從殺紅眼的人臉上看出除暴戾和瘋狂之外的其他氣概。但隨著江戶太平時代的到來,遠離戰場喪失殺戮條件的武士,最終剩下的只有身為武士階級的傲氣而已。從“武士沒飯吃也要裝著剔牙”的傲氣,到江戶子“身邊不留隔夜錢”的豪放狂傲。這種傲氣,恰好是日本思想家九鬼周造在《“粹”的構造》中所定義的“粹”的重要特質。
自在的江戶子,象徵著江戶這座城市的慾望與熱情,這也是一股潛在的力量。自在意味著不受拘束,而在江戶城劃定等級秩序法度的上位者眼中,這自然相當於一種叛逆,是對秩序法度的越軌和挑釁。而江戶子也恰恰為自己觸碰禁忌的行為感到一種心跳式的歡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對衣著等級秩序的破壞。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幕府禁止底層町人穿著綢緞,江戶子就大搖大擺地把仿絲綢質感的綿緞子和綿縮緬穿在身上。既然下令禁止町人穿著刺繡,那就把刺繡改成染色印花好了。在幕府規定的服飾規制中,町人只允許穿著茶色、鼠色和青色這些黯淡的顏色。江戶子們便想出辦法,在僅有的三種色系裡踵事增華,創造出“四十八茶”和“百鼠”諸多顏色——真正是五顏六色的灰和七彩斑斕的藍。
對既定秩序暗度陳倉的挑釁,對禁忌規則陽奉陰違的對抗,從這種意義上說,叛逆,才是江戶子“粹”的真正意義。他們身居社會階梯的下游,身受上層有司重重法條苛律的束縛,但仍然在秩序的夾縫中活出了真正的自我,而不屈服於世故圓滑。他們才是這座城市真正的主人,是真正的江戶之子。
文明開化來了!江戶子哪裡走?
“你老家是哪裡?啊!東京?我真高興,我有伴兒啦……我也是江戶子哪!”
眼前這個“身著輕飄飄的薄絹短和服,搖著摺扇”跟自己說話的繪畫老師,讓從東京來到這個偏遠小地方當老師的哥兒內心浮起一陣不快:“這種人也算江戶子的話,那我真不願生在東京了。”
哥兒是夏目漱石的經典小說《哥兒》中創造的主人公,一名二十幾歲來自東京的少年,一個典型的江戶子:耿直、剛強、魯莽、不諳世事,也不通圓滑世故,卻被拋到一個偏僻的小地方,與一群世故圓滑的傢伙為伍。這群傢伙中也包括那位自詡“我也是江戶子”的繪畫老師,其本質不過是個虛偽阿諛之輩,卻故作風雅。被包圍在世故中的哥兒,縱使知道自己被人有意捉弄戲耍,但還是依從本心,縱意逞強,愛與恨都不加遮掩的坦坦蕩蕩——完全符合一個江戶子“粹”的標準。
小說刊載的1906年,距離江戶子誕育的江戶時代的終結,已過去了近三十八年。夏目漱石誕生的次年,1868年,德川幕府倒臺,明治維新開始。同年9月,江戶改名為東京,成為維新時代的中心。象徵江戶時代的江戶城堡的外門被拆除,兩側的塔樓也被拆毀。東京建造起了像鹿鳴館一樣西洋風格的洋館,參觀的法國作家皮埃爾·綠蒂將其謔稱為“法國鄉下的溫泉療養院”。
東京取代了江戶,文明開化取代了江戶傳統,甚至夏目漱石本人也可以稱之為“開化之子”,他在東京大學讀英文科,前往英國留學兩年,深沐西風。那麼江戶子這個陳舊的名詞在這個新東京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夏目漱石用他的《哥兒》給出的答案是,不僅必要,而且在這個拙劣仿效西洋文化的世故時代,江戶子的意氣,或者說是“粹”,更顯得尤為珍貴。那是一種敢於和世俗對抗的桀驁不馴的剛強,也是一種出脫於老於世故的浮華世風的青春叛逆精神。夏目漱石本人就是這樣一個剛強的江戶子。他筆下的哥兒可以說是自己的內心自況。1910年,政府抓捕審判幸德秋水等宣揚社會民主主義知識分子的“大逆事件”,讓他內心憤懣。當文部省軟硬兼施要授予這位國民作家博士榮譽,以收買民心時,遭到了夏目漱石的嚴辭峻拒。
這種江戶子特有的“粹”也存在於與他同道的其他知識分子身上,小說家永井荷風也是這樣一位江戶子。他比夏目漱石小12歲,完全是在明治維新的開化新風中成長起來。“大逆事件”發生時,他親眼看到五六輛押送犯人的馬車朝法院的方向而去。在多年後的回憶中,荷風對自己當時的表現深感痛苦:“小說家左拉曾為德雷福斯事件而四處奔走,為伸張正義竭盡全力。而同樣是小說家的我們,對於大逆事件卻沒有發表任何言論,為此我深受良心的譴責,痛苦不堪”。
作為一名江戶子,永井荷風面對的是比夏目漱石成長的明治時代更嚴酷的考驗,大正民主短暫的曇花一現,之後便是軍國主義的肆意橫行。1923年東京大地震對這座城市是一場毀滅性的打擊,江戶子所眷戀的江戶時代的餘痕,幾乎都在這場地震中遭到破壞。這場地震也激發出一種狂熱的民族仇恨情緒,狂熱分子散佈各種謠言,包括外國人制造了一臺地震製造儀,企圖毀滅日本。永井荷風這樣的江戶子只能再三緘口,以免遭到線民告發,被憲警逮捕。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越來越多的人,迎合時下流行的軍國主義狂熱,將極端思想偽裝成叛逆和不羈的義士之舉,煽惑民心將對權威的忠順當成惟一的美德,集體邁步走上戰爭之路。

由五社英雄導演的電影《二二六兵變》,講述了1936年安藤輝三、香田清貞、野中四郎、河野壽等八人為首的陸軍下級少壯派軍官商議,定於2月26日發動名為“昭和維新”的軍人武裝政變。
警鐘已經敲響,但陷入狂熱的人們卻渾然不覺。“鐘聲陣陣傳入耳朵,每當這時我不由憂心忡忡起來。我想,我可能是最後一個帶著和往昔的人們一樣的情懷傾聽這鐘聲的人了……”,1936年3月,永井荷風寫下這段話的七天前,東京爆發了“二·二六兵變”,軍隊暴走。東京的市民卻相信這些殺人者是心懷愛國的碧血丹心。
東京,已經不再是適合江戶子的“粹”生長的土地了。
撰文|李陽
編輯|宮子 李永博
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