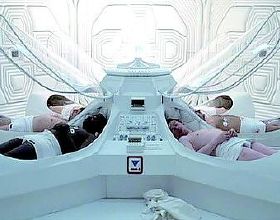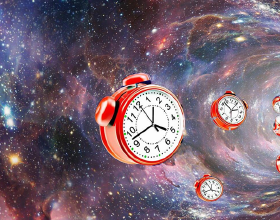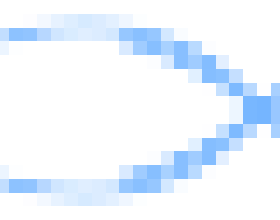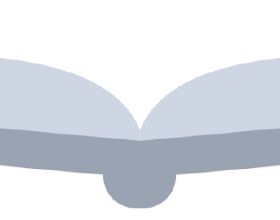以書信切入來研究作家,北塔有這樣的“執念”:作為史料,書信最大的價值就在於“信”,所謂“信”者“信言”也,“信”者“信史”也。
中國最早的現代作家書信合集應當是出版於1936年由孔另境編寫的《現代作家書簡》,魯迅曾為此書作序,序言中他對書信提出了較為辯證和公允的評判:“寫信固然比較的隨便,然而做作慣了的,仍不免帶些慣性,別人以為他這回是赤條條的上場了罷,他其實還是穿著肉色緊身小衫褲,甚至於用了平常決不應用的奶罩。話雖如此,比起峨冠博帶的時候來,這一回可究竟較近於真實。所以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的簡潔的註釋。”由此可見,相較於其他文體,書信是比較具有可信度的。
然而,書信雖可信,卻不意味著能無條件全信。首先,證實與證偽就是必不可少的環節。面對浩如煙海的信件,北塔坦言,自己要像警察探案一般,從裡到外,蒐羅儘可能多的蛛絲馬跡,整理諸多證人證物證詞。一條孤證,不足以輕易定論,要等到掌握了足夠多的可靠證據,才能真正拍板。“由於缺乏鐵證,暫時實在辦不成的,我會老老實實地承認並存疑,以待將來有更多有效證據浮出水面。”北塔說。
從事這項研究,不但要成為“警察”,還要成為考古學者。那些年代久遠、數十年無人問津的信件,與深藏於地下的文物別無二致,“我們要做的,無非是另一種形式的考古挖掘。”北塔說,這便是知識考古學的方法,比方說“發掘”某個詞,就是使它在茅盾書信中或者在茅盾的詞彙表、觀念庫中乃至在整個中國歷史文化語境中的位置和意義得以“重見天日”。趙樸初曾致信茅盾,信的開頭有一句話“承撥冗為鑑真和上像‘探親’撰詩,至為感佩”,稱鑑真為“和上”,而非“和尚”,是為什麼?北塔注意到這一點後,就翻閱了眾多佛學典籍和翻譯的外文文獻,先後排除了個人特殊稱謂、日本發明詞彙等種種猜測,最終在《慧苑音義》《百一羯磨》等佛經典籍中找尋到了“和上”一詞的本義是“親教師”,並釐清了“和上”與“和尚”的差異。
以上的工作,都是在文獻的範疇裡打轉,尋常的文獻研究也不過囿於此。但在茅盾書信研究中,北塔卻一次次地走出書齋,到田野裡尋線索、找答案。茅盾是浙江嘉興人,在與吳地方言人書信往來時,他常常會用到方言。“我雖然也來自吳方言區域,大部分方言我都能懂,但還是有一些我不懂或不太懂的,一是八九十年前的方言跟我這五十年裡所學到的不一樣;二是我的家鄉跟茅盾的家鄉畢竟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在舟船時代,恐怕得半天乃至大半天,相互之間的交通乃至溝通還是有一點點障礙或距離,這種語言文化的同中之異在一百年前肯定大於五十年前。”於是,田野調查的工作就無可避免,方言的年代差異和地域差異是進行研究時要跨越的兩道鴻溝,而尋訪家鄉老人和茅盾本人的師友就成了破譯方言密碼的兩把鑰匙。
就這樣,在書齋之內與書齋之外,書信從塵封的時間裡破土而出,給了後人重新認識茅盾的機會。(大眾日報日報客戶端記者 李夢馨 朱子鈺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