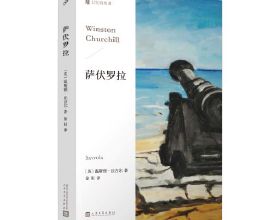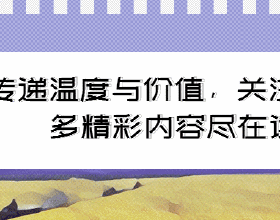文/蘇珊·桑塔格 譯/黃燦然
二十年前,世貿大廈的轟然倒塌對於蘇聯解體後西方中心的現代性程序無疑是沉重一擊,對於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場巨大的震動。美國以9·11為契機入侵阿富汗,開啟了漫長的反恐戰爭;而戲劇性的是,時逢9·11二十週年,美國在此刻從阿富汗撤軍,留下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奪政權,彷彿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點。二十年後的當下,在令人失語的痛苦中重溫那場知識界的震盪,有多少批判和反思還具有有效性?
澎湃思想市場推出“9·11思想考古”專題,嘗試回溯國際知識界對襲擊事件及其後美國與盟友發動的“反恐戰爭”的思考軌跡。專題收錄的文章和訪談既包含對襲擊事件的緊迫、即時回應,也納入了事件後各不同歷史階段的回望和反思。
鑑於二十年時間跨度之長,專題很難全面覆蓋知識界的回應,我們所“考古”的思想軌跡大致按照幾條線索展開:將襲擊事件置於美國自身暴行和製造災難的歷史、資本主義全球化和世界體系的脈絡中理解,追問襲擊產生的背景和根源;警惕9·11事件後國家權力的危險擴張——以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為名拓展監控手段、中止憲法權利、犧牲公民自由、鎮壓政治異見;反思“反恐戰爭”這場打著懲治邪惡、維護正義旗號的主權者對非主權者的“戰爭”;指出“文明衝突論”解釋框架的缺陷,駁斥西方對所謂“伊斯蘭文化”的刻板呈現,揭示西方對穆斯林世界複雜歷史現實的無知帶來的惡果……
這些線索之間既不界線分明也不彼此獨立,而是互相關聯、交織纏繞,學者們的具體分析因而往往同時勾連多條線索。儘管視角不一,但知識分子的根本關涉是一致的:如何重新構想世界以避免戰爭和衝突、找尋與他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襲擊引發的哀痛、驚愕、恐懼的民眾情緒被民族主義話語裹挾,繼而彙集成洶湧的戰鬥呼號和暴力狂熱之際,知識分子嚴守異議與爭辯的空間,“不合時宜”地履行批判和質疑的職責,在絕境之中留存希望。
我們儘可能為專題涵蓋的每一篇文章邀約相關譯者/研究者撰寫導讀,介紹思想家在9·11前後的問題意識脈絡並補充具體的歷史語境。本專題將在今年內持續更新,如有遺漏的重要視角,歡迎讀者投稿補充。專題由實習編輯毛超予協助共同策劃。
本文寫於9·11事件發生一週年之際,刊發於《紐約時報》(2002年9月10日),同年被譯作中文,發表於《書城》,澎湃新聞經譯者黃燦然授權,將此文收錄進“思想市場”為紀念9·11二十年策劃的“911思想考古”專題。
自去年9月11日以來,布什政府就對美國人民說,美國正處於戰爭狀態。但這場戰爭具有特殊性質。考慮到敵人的性質,這場戰爭似乎看不到終結。這是哪一種戰爭?
是有一些先例的。人們都知道,針對癌症、貧困和毒品這類敵人而發動的戰爭,是沒有終結的戰爭。永遠有癌症、貧困和毒品。也永遠有像發動去年(編注:2001年)那場襲擊的可鄙的恐怖分子和大規模殺人者——又有曾經被他們反對的人稱為恐怖分子、後來被歷史正名的自由戰士(像法國抵抗運動和非洲國民大會)。
當一位美國總統對癌症或貧困或毒品宣戰時,我們知道“戰爭”是一個隱喻。可有任何人認為這場戰爭——美國對恐怖主義宣佈的戰爭——是一個隱喻?但它是隱喻,並且是一個帶有強大後果的隱喻。戰爭是被披露出來而不是被實際宣佈出來的,因為威脅被認為是不證自明的。
真正的戰爭不是隱喻。並且,真正的戰爭都有開始和終結。哪怕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駭人、棘手的衝突,也有終結的一天。但這場反恐戰爭卻可以沒有終結。這就是一個徵兆,表明它不是一場戰爭,而是一種授權,用來擴大使用美國的權力。
當政府對癌症或貧困或毒品宣戰,它意味著政府要求動員各種新力量來處理該問題。它還意味著政府不能包辦一切來解決它。當政府對恐怖主義——由敵人跨國的、基本上是秘密的網路構成的恐怖主義——宣戰,它意味著政府允許自己做它想做的事情。當它想幹預某個地方,它就會干預。它不能容忍限制其權力。
美國對外國“糾纏”的懷疑,早已有之。但是,本屆政府卻採取激進立場,認為所有國際條約都有可能損害美國的利益——因為就任何事情簽約(無論是環境問題或戰爭行為或對待俘虜),美國都要使自己受約束,遵守一些準則,這些準則有一天可能會被用來限制美國的行動自由,使美國不能任意做政府認為符合美國利益的事情。事實上,這正是條約的作用:限制簽字國對條約所涉物件任意採取行動的權利。直到現在,任何受尊重的國家,都不曾這樣公開把條約的限制作為迴避條約的一個理由。
把美國的新外交政策描述成戰爭時期採取的行動,就可有力地制約主流媒體就實際發生的事情展開辯論。這種不願意提問題的態度,在去年9月11日襲擊事件後就立即變得明顯起來。那些反對美國政府使用聖戰語言(善對惡、文明對野蠻)的人士遭譴責,被指容忍這次襲擊,或至少是容忍襲擊背後的冤屈的合法性。
在“我們站在一起”的口號下,呼籲反省就等於是持異議,持異議就等於是不愛國。這種憤慨正是那些主持布什外交政策的人士求之不得的。在襲擊一週年紀念活動來臨之際,兩黨主要人物對辯論的厭惡依然很明顯——紀念活動被視為繼續肯定的一部分,肯定美國團結一致對抗敵人。把2001年9月11日拿來跟1941年12月7日(編注:珍珠港事件)比較,一直是揮之不去的念頭。
再次,美國是一次造成很多人死亡(這一回是平民)的致命突然襲擊的物件,人數比死於偷襲珍珠港計程車兵和海員更多。然而,我懷疑,在1942年12月7日,是否需要舉行大規模的紀念活動來鼓舞士氣和團結全國。那是一場真正的戰爭,一年後,那場戰爭基本上仍在繼續著。
而目前這場戰爭,是一場幻影戰爭,因此需要舉行週年紀念。這種紀念,可服務於多種目的。它是一個哀悼日。它是對全國團結的肯定。但有一點卻是明白不過的:這不是一個全國反省日。據說,反省會損害我們的“道德明晰度”。有必要簡單、清楚、一致。因此,將會借用過去時代的話語,這些話語,例如葛底斯堡演說,在當時能以滔滔雄辯來感染人。
林肯的演說不只是鼓舞人心的散文。它是大膽的講話,在真實、可怕的戰爭時期闡明國家的新目標。第二次就職演說敢於預告繼北方在內戰中勝利後必定形成的全國和解。林肯在蓋茨堡演說中所頌揚的自由,其關鍵是承諾把結束奴隸制作為首要任務。但是,當林肯這些偉大的演說被習慣性地援引或被套用於紀念活動時,它們就變得完全沒有意義。它們現在成為高貴的姿勢、偉大精神的姿勢。至於它們偉大的原因,則是不相干的。
這種借用雄辯造成的時代錯誤,在美國反智主義的大傳統中屢見不鮮。反智主義懷疑思想,懷疑文字。宣稱去年9月11日的襲擊太可怖、太滅毀性、太痛苦、太悲慘,文字無法形容;宣稱文字不可能表達我們的哀傷和憤慨——躲在這些騙人的話背後,我們的領導人便有了一個完美的藉口,用別人的文字來裝扮自己,這些文字現已空洞無物。說點什麼,可能就會惹來爭議。說話實際上有可能變成某種宣告,從而招來反駁。最好是什麼也不說。
我不質疑我們確有一個邪惡、令人髮指的敵人,這敵人反對我最珍惜的東西——包括民主、多元主義、世俗主義、性別平等、不蓄鬚的男子、跳舞(各種各樣)、裸露的衣服,嗯,還有玩樂。同樣地,我一刻也沒有質疑美國政府有義務保護其公民的生命。我質疑的是這種假戰爭的假宣言。這些必要的行動不應被稱為“戰爭”。沒有不終結的戰爭;卻有一個相信自己不能被挑戰的國家,宣稱要擴張權力。
美國絕對有權搜捕那些罪犯及其同謀。但是,這種決心不必是一場戰爭。有限度、集中的軍事行動,不應解釋為國內的“戰爭時期”。要抑制美國的敵人,尚有更好的、較少損害憲法權利和損害對大家都有好處的國際協議的途徑,而不必繼續乞靈於沒有終結的戰爭這一危險、使人頭腦遲鈍的概念。
責任編輯: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