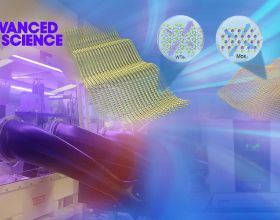以人劃線的株連法本來不對,但實事求是地講“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亦不無道理。實際上,湘雲的不尊婦“德”是大家都能讀出來的,只因看到她與寶釵過從甚密,便想當然地將她歸入寶釵一類了。這種分類法是否合適可以撇開不講,我認為真實的情況是,她曾經是崇拜寶釵的,但並不始終是這樣。
在相當長的一個時間內,她對寶釵有著真摯甚至是熱烈的仰慕愛戴之情。這位天真無邪的少女當面從不奉承她所敬愛的寶釵(與寶釵不同,她從未奉承過任何人),背地裡卻頗有“到處逢人說項斯”的味道,處處揄揚“寶姐姐”。第二十回湘雲當面指責黛玉說:
“……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我就服你!”黛玉忙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好的。我算不如你,她怎麼不及你呢?”還有,在三十二回湘雲對襲人的一席衷腸話:
湘雲笑道:“我只當是林姐姐給你的(戒指),原來是寶姐姐給了你。我天天在家裡想著,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就是沒有父母也是無妨礙的。”
真是對寶釵佩服到了五體投地的地步。在湘雲看來 ,“寶姐姐”簡直是個完人,一點“毛病”也挑不出來。愛惜友情、尊重寶釵到了極點,甚至偶爾發現寶釵行為有“不檢點”時,她也曲意迴護。第三十六回中寫寶釵坐在熟睡的寶玉身邊為寶玉做針線活計,被林黛玉瞧見:
“……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這般景況,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甚厚,便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不讓人,怕他言語中取笑,忙拉過他來到:“走罷……”
尊敬寶釵尊敬到連背後的一笑也捨不得,不但自己捨不得,而且唯恐別人取笑了寶釵!
但是,寶釵對湘雲又怎麼樣呢?
湘雲雖然生在鐘鳴鼎食的侯門,但實實在在只是一個“精神貴族”而已。父母過早的下世使她沒有真正享受過一般人都有的天倫之樂;依賴為生的叔父母對她相當苛刻,家裡的事一點也做不得主;每天做活到三更天,為寶玉做一點,家中的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連大觀園詩會一次小東道的花費也使她為難。她在境遇上便與薛家當家姑娘有極大的不同。寶釵固然也做一點女紅,但對於她來說那是點綴,是表明一個標準仕女全面修養的需要。而湘雲則頗有“勞動”的味道了。寶釵對湘雲,就是以大姐姐的姿態,用安撫慰問、替做東道這種大道理加小恩惠的手段贏得了湘雲對她的真心敬仰。
平心而論,寶釵亦未必是有心藏奸。她是在按她的哲學、修養和處世之道來處理一切人事關係的。對任何人,她都不自覺地分等級巧妙地討好,也確是討來了“好”。她是個只愁在“人人跟前失於應候”的人,並不特別歡喜湘雲。所以,從“沒時運”的趙姨娘到賈母王夫人無不認為她是誰也比不上的好人。
渾然不露心機的寶釵對湘雲是有成見的。在湘雲教香菱作詩及與寶釵夜擬詩題過程中兩次說教佈道式的批評不去說了,單舉二例看看她的胸中城府:
在第三十回中,寫湘雲至賈府,姊妹們經月不見,特別親熱。湘雲開口就問:“寶玉哥哥不在家麼?”寶釵當著賈母的面半真半假地加了一句“她再不想著別人,只想寶兄弟。兩個人癖性都好頑,都合式”,卻圓滑地補了一句:“還沒改了淘氣。”這話大概是不太合老太太的意,反而給了她一句“如今你們都大了,別再提小名了”;
第三十一回,為了金麒麟這段公案,林史二人不和:
寶玉笑道:“(雲妹妹)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他的金麒麟會說話。”一面說話一面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寶釵抿嘴一笑。
當時並無人打岔,怎麼會“諸人都不曾聽見”呢?這是作者的狡猾之筆。事實上是諸人都聽見了,因感到氣氛緊張不敢有所表示,唯獨寶姑娘忍不住“抿嘴一笑”。她笑什麼呢?是稱心如意,還是略帶酸味,抑為湘雲解嘲的笑呢?這件事假如發生在黛玉和她之間,湘雲會不會也來個“抿嘴一笑”呢?
寶釵的這種行事,坦率而粗心的湘雲一概沒有覺察,她雖然聰明伶俐,畢竟閱歷太少而且不夠敏感。最重要的是因為她與寶釵每次接觸的時間都不長,無法對這種不自覺的虛偽作出判斷。所以,在湘雲長期住進賈府之前,她對寶釵的愛戴一直是篤誠的。
湘雲終於長期住進了賈府。她不是像寶釵那樣,攜帶著雄厚的家資,滿懷“上青雲”的壯志走進賈府的。她是走出了一個政治失意、經濟衰落的家庭,命運之神把她像秋天的黃葉一樣飄送進大觀園中。她熱情地執意要求與“寶姐姐”住在一起,想在精神上從寶釵那裡尋求安慰。這個天真的姑娘哪裡知道“薛姑娘”的“冷”呢?
她的熱情很快遭到了寒流的襲擊。這股寒流我們無法判斷是如何襲(或浸)來的,但是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說明寶釵與湘雲的關係在前八十回中已經冷卻甚至凍結。
第七十回中,李紈的丫頭碧月有幾句話值得玩味:
我們奶奶不頑,把兩個姨娘和琴姑娘也賓住了。如今琴姑娘又跟了老太太前頭去了,更寂寞了。兩個姑娘今年過了,到明年冬天都去了,又更寂寞呢!你瞧瞧寶姑娘那裡,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冷清了許多,把個雲姑娘落了單……
這就費解,湘雲硬要和寶釵一處住,怕的就是“落了單”,怎麼能因為香菱出園,雲姑娘就“落了單”呢?碧月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觀察的,應當說是準確的,我認為這就是二人疏遠的證明。當湘雲只是如蜻蜓點水般在賈府做客時,她眼中的寶釵是無與倫比的好,真正長住下去,冷姑娘的道學氣味就會使她難以忍受。她的身份和教養決定她不會與寶釵公開鬧翻,但落單的境遇已被眼睛雪亮的奴隸們看出來了。
第七十五回“發悲音”,寶釵借母病為由要離開賈府這隻將沉之舟。說是等薛姨媽痊癒之後“橫豎”還要進來,但既然是回去小住數日,為什麼李紈要派人看房子她卻不讓,又何必囑李紈“把雲丫頭請了來,你和她住一兩日”呢?
值得注意的,她對李紈告辭,湘雲還矇在鼓裡。既然要走,為何不先和住在一起的湘雲打個招呼呢?這就說明,寶釵的“母病”完全是一種遁詞,我猜這兩個好朋友之間是爆發了感情上的衝突。
請看,兩人本在一起住,一個來找李紈,一個跑到探春那裡,而寶釵竟讓李紈派人去叫探春和湘雲一併來此“……到這裡來,我也明白告訴他(湘雲)”。這真有點“當面說開”的架子,平日溫厚可親的形象哪裡去了?
接著,眾人說了一會話便散了,“湘雲和寶釵回房打點衣衫,不在話下。”
什麼“不在話下”?為什麼竟無一語訣別?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這兩個分道揚鑣的朋友,各自沉默著收拾各自的衣物。往日“繾綣難捨”的感情已化作一團可笑的雲煙消散了。
道不同,則不相與謀。性格、境遇、思想上的嚴重分歧,如同一把利刃,割斷了她們本來就不堅韌的感情紐帶,她們終究是走不到一起去,只好“默默遵歧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