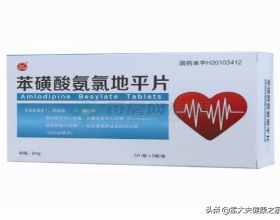好的家風,是小到一個家庭,大到一個國家的“傳家寶”。
好的家風是一盞燈,照亮後人前進的路;好的家風是一條路,指引後人走向光明;好的家風是一場春雨,滋潤後人茁壯成長。
我們祖上是木匠世家,祖上八輩沒有出過帶“官帽翅”的,父親復員回村,當了生產隊長和現金會計,算是入了“仕途”。而母親當年嫁過來時,只分了若干“傢伙什”。其中,有一架紡車、木工尺和老算盤,一來算是實用之物,二來在我的記憶裡深刻銘記。祖上沒留下什麼“萬貫家財”,但這三件“傳家寶”,各有各的故事,彰顯了父母家風嚴謹、持家有道、教子有方的清廉家風。
修正人生的“戒尺”
家裡有把木工尺,那是祖上留給後人掙飯的“營生”。後來讀了魯迅先生的《三味書屋》,我把它稱為“戒尺”。年頭已久,磨損嚴重,邊角殘缺,刻度模糊,但父親仍當成“寶貝”,閒來第一件事,就是一遍遍地擦拭,直到把尺子擦得鋥亮。
父親1946年參加解放軍,1950年,所在部隊轉編為公安部隊。1955年,公安部隊改稱為公安軍。1957年,公安軍撤銷,父親復員回鄉當了農民,憑著踏實肯幹的精神,又在部隊學過文化,很快當了村裡的生產隊長兼現金會計。
父親當過兵,從時間跨度上來說,應該稱得上“前輩公安人”。他是個很傳統的人,信奉“黃荊棍下出好人”的道理。這把木工尺,如同古代學生敬畏先生的戒尺一樣,讓我們對它也懷著深深的敬畏。
記得有一次,我和小夥伴去村東頭老趙家偷杏子,不僅偷了杏,還弄斷了好多樹枝。老趙兩口子找上門的時候,我還不以為然。老趙一走,父親關起門來,用那把戒尺狠狠“修理”了我一頓。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他一邊打一邊數落:“小時偷針,大時偷金,小時偷瓜,長大偷牛,我平時怎麼教你做人的!”
那次父親打我,是下了“狠心”的,正是因為這次“狠”打,使我對這次犯的錯永遠銘記在心。從那時起,那把尺子就在我腦海中劃上了一道“戒線”,讓我明白什麼事情能做,什麼事情不能做。
父親的身教我看在眼裡,父親的言傳我銘記心中。在父親的潛移默化下,我高中畢業後,順利考上了軍校,接著兩個弟弟也都上了大學。這在八十年代初期的農村來說,確實是個不小的“新聞”。
從軍校畢業後,我從最基層的排長幹起,後來進了機關,逐步走向領導崗位,慢慢手中有了一些權力。但在事關戰士入黨、考學、提幹、晉升等方面,我從不過問插手,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為官兵們營造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氛圍,力爭讓每個戰士都生活在希望中。
服役20年來,我6次榮立三等功,後來轉業到鐵路公安系統,迄今從警15年,我時刻做到退役不褪志、退役不褪色,堅決聽黨話、知黨恩、跟黨走,把火熱的青春獻給了溫暖的車廂,用愛心服務千千萬萬旅客,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業績,曾多次受到上級領導機關嘉獎,並榮立三等功。
在父親去世後,“戒尺”被我珍藏起來。現在想來,戒尺的使用次數雖屈指可數,但幾乎每次都對我的人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把戒尺的來歷和小時候的經歷講給女兒聽,在她看來雖然可笑、有趣,但在我看來,我更想把這把戒尺存在的意義帶給她,雖然,現在管教孩子,已用不著“戒尺”,但是心裡一定要有一把“戒尺”。小到夾菜、大到做人!隨著女兒的長大,各種壞習慣被糾正和改變,證明那把“隱形的戒尺”一直都在,並且一直在發揮著作用。
如今女兒很有出息,在國內一所知名大學畢業後,被德國一所世界名校錄取為研究生,研究方向是當今最熱門的人工智慧,希望她爭取學有所成,早日報效祖國。
能算人心的算盤
家裡有把老算盤,算珠被人手磨得發亮,這是爺爺臨終時留給父親的,並有遺言留下:算賬不能出錯,做人不能含糊,行得正,方能過得心安。
這把老算盤是一個時代的記錄,父親曾用它記賬,記工分,記載生產隊的日新月異,記著生產隊每家每戶的喜怒哀樂。
“下邊的當一,上邊的當五,一盤小小算珠,把世界算了個清清楚楚。哪家貪贓枉法,哪家潔白清苦,俺叫你心中有個數。三下五去二,二一添作五,天有幾多風雲,人有幾多禍福,君知否?這世界缺不了那加減乘除。”父親雖然離開我們了,可這一首電視劇主題歌,又勾起了我對父親的無限思念。
父親原沒有接觸過會計,從公安軍復員回鄉後,他經常看一些財務方面的書籍,勤奮好學,很快學會掌握了現金會計業務知識,還能熟練地達到精、準、快、細、嚴的工作標準。
記得我上小學時,一天夜裡,清脆的算盤聲又把我鬧醒。我知道,這是父親又在為尋找賬面上的差錯而通宵達旦,而這差錯可能只是“一分錢”。我建議父親第二天再查,父親並不理睬,母親說,你爸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帳不平他是睡不著的。我說,不就是差一分錢嗎?自己墊上就是了。這時,父親開口了,這賬上差一分錢,不一定就是少一分錢,一分錢好補,但賬不平的根源要找到,差一分錢,往往可能就是一大筆金額的錯賬,今晚上,不把一分錢的問題找出來,帶著問題睡不著覺。
在我心裡,父親有一顆菩薩般的心。有一次,快要過年了,生產隊派張伯去南陽買了頭肉牛,準備回來宰殺,分給社員過年。牛不好買,張伯到處奔波折騰,他曾在抗美援朝戰場上負過傷,身體吃不消,途中多了一些住宿、吃飯的花銷。父親按規定標準核賬,賬目肯定不平。按常理,父親應該找張伯要錢,但他不忍心,卻忍心對我們兄弟仨的壓歲錢下手了。
那年月,我們兄弟每人最多也就是五角的壓歲錢,這是孩子們一年裡最大的期盼,是一個孩子過年時最大的幸福和快樂。可是誰又能犟過父親?大年三十晚上,我們乖乖地拿出壓歲錢替父親“平了賬”。賬平了,父親緊鎖的眉頭舒展開了。
秉承爺爺的教誨,父親當會計30多年,始終用著這把能算人心的老算盤,不僅把賬目記得清清楚楚,更讓自己安心、社員們放心。有部分社員,包括大隊幹部不相信我父親“分文不貪”,曾多次突擊查賬,結果一點問題沒有,令大家心服口服。對此,父親是極為坦然的,老算盤賦予他“人生清白”的力量。
溫暖人生的紡車
家裡還有一架紡車,我記憶猶深。紡車是母親專用,她是位農村婦女,大字不識一個。母親生前囑咐我“不佔公家一分錢便宜”,從她這句話上,能看到爺爺、父親的影子,清廉傳家,才能久遠。
記得我剛懂事時,生產隊還沒有隊部,父親的辦公桌就在家裡,隊裡現金經常放在抽屜裡。我和弟弟從不拿抽屜裡的一分錢,就是因為母親時常告誡我們,那錢是公家的。
那年月,家家戶戶都到生產隊按人口和勞動力稱“口糧”。每個月去稱口糧,生產隊的保管員為了拍父親的馬屁,總想多稱一點給我家。但是,母親心裡有數,每次都睜大眼睛盯著稱,生怕人家多稱了。有一次,大姐去稱口糧回來後,母親有意稱了一下後,果然發現多了3斤,就連忙去找保管員,帶著三分火氣,和他說:不能佔公家一分錢便宜,你懂不懂?說著就把多出的口糧全部退了,嚇得保管員不敢吱聲,打那以後,這種事情再沒發生過。
母親注重教育我們從小養成節儉的良好生活習慣,她言傳身教,從點滴做起。母親吃飯時一丁點兒也不浪費,吃到最後還要掰一塊硬餅把碗裡的菜汁擦乾淨。我們的衣服和鞋襪都是“接力”著穿,大的穿舊了,再給小的穿。
母親小時候跟姥姥學會了一手過硬的紡織、漂染、縫紉技術,為了掙點零錢補貼家用,也讓我們穿得好一些。我記得從入冬到春耕,不論白天夜晚,母親似乎都在不停地搖動紡車。每當我從夢中醒來,總能看到母親坐在木墩上,一隻手均勻有力地搖著紡車的把手,一隻手在另一端牽線收線,隨著身體有節奏的後仰前傾,一條細實的棉線從手指間抽了出來,密密匝匝地纏在了紡車的錠子上。每次勸母親早些休息,她總是說,你們睡吧,我不困。
在我們村裡,母親是紡線織布的能手,成堆的棉絮,經過母親紡、染、織後,就變成了各種花色的棉布了。母親用它們做成衣服、床單、頭巾等生活必需品,除滿足一家人的需要外,主要還是到集市上出售貼補家用。母親織的布花樣新穎,剪裁的衣服總是很合體。過年時,我們姐弟5個都能穿上嶄新的棉衣棉褲。而母親很少給自己添置新衣服,她總是說,你們姐弟5個是她的“臉面”,孩子們穿得光鮮漂亮,當孃的就感到很體面。
當時年幼的我,尚不能理解母親是多麼的辛勞,是母親的不畏艱辛和父親的勤勞,才使我們姐弟有飯吃、有被蓋、有衣穿。現在,一想起這些,就忍不住熱淚盈眶。
如今,母親謝世已經20多年,伴隨她一生的紡車也被時代淹沒,可是那節奏均勻,抑揚頓挫,錯落有致的紡線聲,卻穿越了時空,傳承至今。那根一頭牽在母親手中,一頭牽著紡車的銀線,牽動著母親多少殷殷的目光。她那紡線織布的身姿連同那架“勞苦功高”的紡車,永遠地定格在了子女們的心中。
(作者單位:威海市公安局地方鐵路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