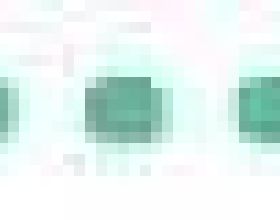【青年學者論壇】
與平安時代就被日本詩人推崇的白居易相比,日本詩人對於李白、杜甫的學習起步略晚,約始於五山文學初期。虎關師煉(1278—1346)在《濟北詩話》中稱“李、杜上才也”,開日本詩人學習李、杜之先河。日本學者青木正兒認為虎關言及李、杜之詩,雖深受宋人詩話影響,“但比之平安時代以後那種醉心白居易而輕視李白、杜甫的詩眼,甚為懸隔”。黑川洋一(1925—2004)《杜詩在日本》也以為虎關師煉深入研讀杜詩並顯示出獨特的見識,是日本杜詩研究的開山之祖。李、杜詩由是開始進入日本詩人的學習視野。江戶時代(1603—1867)是漢學的復興時代,也是李、杜二人對日本詩壇產生影響力的鼎盛時期。李、杜二人對江戶詩壇之影響主要體現在江戶時代對李、杜詩集文字的整理、刊刻以及詩人對李、杜的學習和評價。
漢籍東流一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議題。江戶時代中日商船來往增多,船載漢籍超越以往時期。李、杜詩集到達日本後,經藏書機構與學者選擇,或直接翻刻、抽印、抄錄,或加以註釋、評點後重新出版,產生了數量巨大的和刻本,加快了李、杜詩集在日本的流通和傳播。
筆者統計,江戶時代最為流行的和刻李白詩集主要有《分類補註李太白詩》與《李太白絕句》兩種,其中前者最少經過兩次刻印;而杜集則至少有《杜律集解》《杜律五言集解》《杜翰林考正杜律五言趙注句解》《杜工部七言律詩分類集註》《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即《杜詩集註》),以及《杜律集解》《刻杜少陵先生詩集註絕句》《杜工部七言律詩》《闢疆園杜詩註解》《杜律集解詳說》《杜律詩話》《杜律評叢》《杜詩偶評》《杜律發揮》《杜工部集》《杜律詳解》十餘種。其中明代邵傅所編的《杜律集解》,雖然在國內難覓蹤跡,但在日本至少翻印九次;又清代沈德潛所撰《杜詩偶評》,至少翻印四次。據鍾卓螢博士論文《李白詩文在日本江戶時代的影響與詮釋》統計,江戶時代舊藏書目所載李杜合集有十餘種,筆者統計和刻李、杜合集至少有《李杜絕句集註》《李杜絕句》《李杜絕句集》《李杜四聲韻選》《李杜詩法精選》《箋註李杜絕句集》等,此外又有和抄《李白詩》《李杜絕句選》《李詩抄》等。和刻李、杜詩文集的數量和品種既可以最直觀地反映當時社會對李白、杜甫詩集的需求,也可見當時詩人對於李、杜的態度。
在日本學習李白、杜甫早期,二人在日本詩壇的地位基本相當。日本昌平坂學問所舊藏兩部日本南北朝時期(1336—1392)刻本《唐朝四賢精詩》,即為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四人詩選。此書版刻樣式,頗有元刻遺風,或據元本重刊。和刻《唐朝四賢精詩》書中李、杜同列“四賢”,表明了當時日本詩人對李、杜並稱的認識。但在當時杜詩比李詩在詩僧中擁有更多的受眾,吉川幸次郎(1904—1980)《杜詩在日本》描述了十三四世紀僧侶們熱衷杜詩並以學生為物件編寫杜詩講義的情形,這種方式前所未有;又如當時的禪宗僧人義堂周信詩宗杜甫,喜讀《杜工部集》,詩風雄壯。
江戶早期,李、杜二人往往被並稱,但杜詩在日本詩界的傳播更為深遠,因此詩人對杜詩的呼聲高於李詩。被朝鮮人稱為“日本的李杜”的石川丈山(1583—1672)以盛唐詩、中唐詩為正宗,曾建“詩仙堂”,四壁懸掛包含李、杜二人的中國漢、晉、唐、宋詩人畫像,石川將李白尊為“詩神”,杜甫尊為“詩聖”。江戶早期林羅山(1583—1657)可謂學習杜甫的重要人物。林氏非常欣賞杜詩,創作了大量與杜甫、杜詩相關的詩文,其生前藏書,首頁必鈐長方形陰陽印“江雲渭樹”,印文即出自杜甫《春日憶李白》:“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林羅山以“江雲渭樹”為印文,既出於對李、杜友情的認可,更表達了對杜詩的喜愛。林家第二代大學頭林鵝峰《唐宋百花一詩》明確提出“以李杜為最首者,以為詩家之冠也”,認為李、杜不分伯仲。
日本詩人對於李白的認識和學習主要吸收了李白“嗜酒”與“謫仙”等特徵。如江戶畫家與謝蕪村(1716—1783)繪有《醉李白圖》等人物像,申發了李白“斗酒詩百篇”的故事。江戶中後期詩人藪孤山(1735—1802)作《擬晁卿贈李白日本裘歌》,“代”千年前的晁衡贈詩李白,節選如下:
長安城中酒肆春,胡姬壚上醉眠新。長揖笑謝天子使,口稱酒仙不稱臣。忽思天姥駕天風,夢魂飛渡鏡湖東。百僚留君君不駐,紛紛餞祖傾城中。我今送別無尺璧,唯以仙裘贈仙客。仙裘仙客一何宜,醉舞躚躚拂綺席。昂藏七尺出風塵,已如脫籠之野鶴。從是雲車任所至,弱水蓬萊同尺地。西過瑤池逢王母,雲是日本晁卿之所寄。
又青山佩弦齋(1808—1871)作《李太白觀廬山瀑布圖》詩曰:“筆下有神驅迅雷,香爐峰畔紫煙開。天公不惜銀河水,直為謫仙傾瀉來。”以上兩首詩歌對李白詩歌典故多有化用,有明顯的李白詩歌風格。
從江戶時期和刻李、杜集的品種和數量可見,李白對江戶詩壇的影響力要小於杜甫。有學者認為,因缺少權威的、流行的通俗註解本等原因,李白詩歌無法廣泛傳播與普及,因而江戶時代日本詩人評價李白時難有充足的認識。杜集的大量傳播,使得江戶詩人更加便捷地獲得杜詩文字,因而杜詩表現出比李詩更深刻的影響力,學界對研究江戶時代詩人如何學習、評價杜甫,也更容易找到詳實可靠的資料。友野霞舟(1792—1849)《錦天山房詩話》反映了杜甫在當時日本詩壇的地位:“元和以來(1615後)從事翰墨者,雖師承去取不一,大抵於唐祖杜少陵、韓昌黎,於宋宗蘇、黃、二陳、陸務觀等。”江戶詩人熟悉杜詩文字,如詩僧秦冏《幽居適四首·其一》“園收錦裡先生果,廬接東陵處士瓜”化用杜甫《南鄰》詩“錦裡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慄未全貧”、《園人送瓜》詩“東陵跡蕪絕”、《喜晴》詩“往者東門瓜”等句;又江戶晚期詩人奧野小山(1800—1858)《初冬雜詩》“三冬耽學狂方朔,一飯思君老少陵”亦是靈活運用杜甫“一飯不忘君”之典。江戶晚期詩人對杜甫和杜詩也有批評的聲音,如對於杜甫的“苦吟”,長野確(1783—1837)《松陰快談》以為“杜少陵是甚巧,蓋由苦吟得之”,而詩人冢田大峰(1745—1832)則對此表示反感,以為杜詩“多悲嘆窮屈,而少雄邁條暢,且苦於吟哦,而巧出新奇”,以為杜甫之詩,缺少如李白詩歌之飄逸雄壯。這些批評,反映了江戶詩人在普遍學習杜甫的潮流中對李、杜詩風之思辨。
“學詩莫如唐,有華且有實”,江戶時代並重李、杜的詩人也不在少數。江戶前期詩人伊藤東涯(1670—1736)是典型代表,其《讀杜工部詩》對杜甫生平經歷以及詩歌成就相當概括:“一篇詩史筆,今古浣花翁。剩馥沾來者,妙詞奪化工。慷慨憂國淚,爛醉古狂風。千古草堂來,蜀山萬點中。”伊藤不僅熟悉杜甫,他亦有研習李白詩歌,今日本實踐女子大學藏有其《李詩抄》,為李白詩歌抄本。又雨森芳洲(1668—1755)《橘窗茶花》提到其案上所置詩集,以陶淵明為首,李、杜為二,韓、白、東坡為三,認可李、杜詩風。江戶後期出於對盛唐詩的尊崇,詩人往往並重李、杜,如日本詩人芥川丹丘(1710—1785)《丹丘詩話》以為李、杜詩風各有長處,他對李杜優劣問題提出:“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各學其性所近,亦詩道之捷徑也。”此為江戶後期詩人對李、杜二人較為公允的評價。
李、杜二人對江戶詩壇的影響貫穿始終。雖然明清兩代李白詩集的東傳、和刻李杜合集的刊行,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和刻李白詩集在數量和品種上的差額,但杜甫對江戶詩壇影響超過李白是不爭的事實。有學者認為,江戶時期日本對杜集的刊刻集中在早期,但筆者以為江戶後期,雖然初刻文字少了,但如《杜詩偶評》等書多次重印,仍然可以說明江戶後期對杜詩文字旺盛的社會需求。江戶詩壇對於杜甫詩歌的偏愛,也反映了當時日本詩學在學習漢詩、選擇詩歌典範時對杜甫的重視。
(作者:由墨林,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