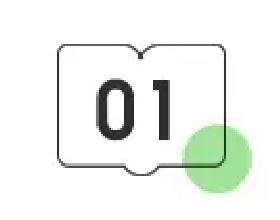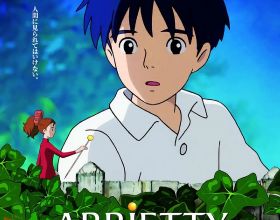因《奇葩說》而成為“網紅教授” 新作《西方現代思想講義》受追捧
劉擎:生活除了KPI,還有心靈之旅
一個夏日的午後,北京37攝氏度的烈日驕陽,眾多年輕人渴望透過哲學獲得“清涼境界”。劉擎教授在這一天走進了北京一家商場,在熙攘人群的圍觀中,與讀者們對談世界。
商場一層的中庭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空間,物質的濃郁氣息就在左右漂浮著,電梯吞吐著消費者湧入湧出,二層、三層的購物者好奇地向下俯視著會場,所有的感官都被稀釋,人似乎變得渺小了。就在這樣魔幻的時空中,劉擎教授的講座讓人想起2000多年前蘇格拉底走進雅典市場與民眾討論的情景,他儒雅的聲音讓人們匆忙的步履有所停頓,紛雜的思緒被片刻地聚焦在一處,人們聽到了“哲學”的名字。
劉擎是中國目前思想史領域最好的老師之一,他在華東師範大學講授了15年的現代思想課,從2003年開始,每年年末撰寫的《西方思想年度述評》被哲學家陳嘉映評價為“特別值得讀,國內沒有第二個人能夠寫出來。”因為《奇葩說》第七季,劉擎更是從學者成為大眾新“愛豆”,最新出版的《西方現代思想講義》書名雖然聽著頗為高冷,卻成為粉絲們的必須入手之作。
劉擎教授謙和低調,但也很“生動”。他會對接受記者採訪時間短而抱歉;會在聽到有年輕人喜歡哲學而且考上哲學系時,情不自禁地提高音調說“太好了”;也會在深夜讀到一篇令他感動的文章而有朗誦出來的衝動。種種樣子,都是劉擎。就像他說,所謂“真實的自己”,這個說法本身是有問題的,它好像是給出了一個單數的真實的自己,其實每個人是多面的,當然這個多面有主次之分。
對於自己走紅後,外界賦予他的更多標籤,劉擎表示他很認同《自我的本質》一書作者的觀點:“一個人的自我,其實你並不是你以為的自己,也不是別人以為的自己,你是你以為的別人眼中的自己。”
劉擎說自己參加過很多活動,《奇葩說》只是其中之一,但沒想到會有這麼大的影響,讓人們以“網紅教授”來標籤他,但就他個人而言,自己仍然是一個大學老師和學者,“我在《奇葩說》上跟大家的交流交鋒,仍然是在學者教授這個主要框架的延伸。”
人的生活是要有意義感的,哲學就是在探索生活到底怎樣才更有意義
6月19日下午,得到圖書和西西弗書店在麗澤天街聯合舉辦了《劉擎西方現代思想講義》分享會,“思考無用的問題,能給你帶來什麼”是劉擎教授這次想和大家討論的話題。
劉擎表示,所謂有用的問題,就是與人的生物性生存最基本相關需要的那些問題,但是人和動物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區別。區別在於人不光生存,還會思考自己的生存,“我們不僅做事,還會想自己怎麼做事,這是人與生俱來的反思意識和反思能力,是一個人內在的精神結構。”
劉擎認為,這些問題,從維持生活基本需要的角度來看是無用的,但它卻是重要的,因為人的生活不是一個純粹動物意義上的生活,不是能夠維持自己的生物性生存就行了,人的生活是要有意義感的,“我們是動物,但是我們是要追求意義的動物。”
當生活順利沒有遇到問題的時候,人們通常不會特別明確地反思自己的生活。如果遇到問題了,第一步的思考也是“就事論事”地解決問題,未必是哲學性的思考,什麼時候會出現哲學性的思考呢?劉擎講解說:“是發現一些現成的求解方式,不足以回答我們的困惑或者焦慮、不滿、不適感,這時候我們就進入了哲學的階段。這些問題不會因為難以回答就消失了,如果你能徹底忘掉不再關心這些問題,你真能做到的話,恭喜你,你要麼變成了神明,要麼就變成了動物。”
所以,劉擎表示,哲學就是在探索我們的生活到底怎樣才更有意義:“這是一個難題,它的難在於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沒有一個普遍有用的答案,它是高度情景化的,需要自己探索和思考,而且這個答案經常可能會被否定和改變。”
雖然困難,但是劉擎教授認為人們需要哲學思考,他舉例說,某IT公司一位職員內心很不快,因為和他同時入職的一位同事在過去三年晉升了兩級,他只晉升了一級,而且這個小夥伴比他還小九個月,“我們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些KPI(重要績效指標),以及和KPI相關的維度上,而生活是豐富的,生活還有別的東西,有櫻桃的滋味,有心靈之旅。在一次訪談裡,我說在內卷和躺平之間有很多中間地帶,我覺得這是可能的。但是,它是困難的,因為你需要支援,你首先需要自己的支援,你要給自己一些信心,你要有一個獨立於現在特別主流的評價模式。我覺得這是重要的,而哲學思考就是會幫助你建立自己的、不同於主流支配性標準的標準。”
一面是太爽了,一面是太難了
這是現代人精神狀態的特質
很多年輕人吐槽壓力大,不快樂,而劉擎教授在《西方現代思想講義》中的哲學講述無異於一盞明燈,令人頗有醍醐灌頂之感。
劉擎在書中強調了現代性和現代人兩個概念,現代性是指現代生活的一種制度性和觀念性的條件,它是一個處境。其高度理性化帶來的後果使得傳統的、神秘的、不能被理性所把握的那些存在變得要麼被忽視、要麼被邊緣化、要麼就變成非常少的神聖道德的東西。總之,理性成了主導。
而現代性的理性化,是一個不全面的理性化,哲學家韋伯認為工具理性占主導地位,價值理性就變得非常多樣,於是這個理性是不平衡的理性。這樣的一種處境對現代人造成負擔。
在傳統生活當中,人們雖然生活手段和方式非常有限,但意義感的方向非常明確,而在現代則是有好多條路,但是你的方向找不到。劉擎教授說:“以前是有意義、有方向,但是沒路可走,現在是路非常多,但是我們的方向找不到了。理性講究效率,效率就要分工。每個人只是整個大產品的一部分,分工合作。所以,我們生活在一個區域性當中,我們找不到意義了。”
在劉擎教授看來,現代人有很多自由的選擇,原則上可以做很多事,你可以換各種工作,到不同的地方生活,甚至不喜歡自己的性別也可以去變性。你可以結婚、離婚,其中的障礙越來越小。但是另一方面,現代人又有很大的負擔,太難了:“第一,你做改變要有能力,這是一個困難,第二 ,你想離職,想創業,想分手,但你不知道這樣的自由選擇對不對、好不好,沒有充分的把握,你的判斷沒有一個更高的存在來加持你,你要獨自承擔這個判斷的風險。一面是太爽了,一面是太難了,這是現代人精神狀態的特質。”
我是誰的難題在於你找不到自己
所有這些問題,劉擎教授認為都不是表面看來這麼簡單的事實層面問題,“它的問題都是背後的、事關人生的意義,是自己到底要追求什麼樣的生活,以及我是誰的問題。關於‘我是誰’,它的困難不在於你聽從了別人而忘掉了自己,不是這麼簡單。以前好多流行說法是‘我要做自己’,其實不是這麼回事,困難的是你自己靠自己,你是找不到自己的。我看過一本書叫《自我的本質》,作者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說法,他說你是誰呢?你並不是你以為的自己,也不是別人眼中的自己,你是你以為別人眼中的自己。所以,自我的構成是你自己的主觀想法和你想象的別人對你的想法的一個綜合產物。自我是一個非常麻煩的問題,認識你自己是非常麻煩的一個問題。”
劉擎教授表示,我們並不是有表層的自我和真實的自我兩個自我,我們自己是非常豐富的,“我們有多個面向,第一,我們在歷史性上,是一個時間的存在,我們由童年、青年,發展到現在。我們在歷史上有不同的樣貌和狀態,你怎麼說過去的我是我呢?我們的成長當中發生過一些事件,造成一些裂痕或者改變,它需要你重新調整甚至重建自我。我想每個人都是經過這樣的事件成長起來的,所以,這個自我是一個挺複雜的事情,要把它整合起來。”
第二,劉擎教授認為,在每個時刻,人是有不同面向的。“我在書裡說,每個人年輕的時候都會經歷理想主義澎湃的夜晚和現實主義覺醒的清晨。你每年年初的時候會立一個flag,我建議大家下一年再立flag的時候,去對照一下上一年的flag有多少是完成的。人是蠻複雜的。所以,一個真實的自我並不是說你放縱的那個自我就是假的,或者說放縱的自我‘是更真實的,我們在當下的此刻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關於自我有各種各樣的理論,劉擎比較認同“敘事性的自我”。“就是你能關於自己講出一個相對完整的故事。也就是說你如果要忠實於自己,你要明白自己的話,你要把自己的故事講清楚。為什麼那麼多複雜的過往,仍然是你的一部分?那些過往的經歷、事件,在你心中,在自我的構成當中,佔據什麼樣的地位,發生什麼樣的影響?失戀了意味著結束嗎?它一直影響著你。無論是好的體驗還是創傷性的體驗,它依然在不同的時刻,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你。那麼,如果你能夠在此刻,在如此多的想法、需求、關係當中,將所有事情整合成一個故事,就意味著有了一個相對完整的自我,在這個意義上是真實的自我。”
劉擎強調,在沒有完成故事的時候,這個自我是不存在的。過去的一次工作、一次戀愛的意義,會在未來的不同時刻對你產生不同的意義,所以,這個故事是可以重新編輯修改的,“如果最後,你的言行、你的經歷、關於自己,你可以講一個精彩的、動人的、有意義的故事,那你就過了有意義的人生。”
小學同桌給我上了第一堂哲學課
對於一個人應該什麼時候開始學哲學,劉擎教授表示,當小孩子可以與人交流時, “哲學課”就應當開啟,“我有個朋友現在在做兒童哲學的普及,他們從小學一年級甚至幼兒園就開始了,透過做遊戲來讓孩子們親近哲學。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好的。”
劉擎教授認為應該具備哲學的敏感性,他講了自己與小學同桌的兩個故事。一個是他去同桌家,“那時我大概10歲,我發現她父母的關係特別好,在1970年代那是非常罕見的。在他們家吃完飯,她父親打水進來,她母親洗碗。她父親就從後面抱住她媽媽,我同學不高興地說他們破壞了勞動的生產率。我覺得同學的話好高階。我就想,他們破壞了家務勞動的生產效率,但贏得了什麼呢?很久以後,我讀到一個經濟學家叫阿馬提亞·森,他說當我們指效率的時候,我們總是指某物的效率。但是,這件事情對於X的效率並不等於Y的效率。比如說你們現在996加班了,對於你來說你的工作效率可能提高了,但你的睡眠效率就下降了,你自己閒暇的時間就少了。我突然想到我小時候就有了這個敏感,當那個同學說她家的勞動生產效率下降了,我覺得她父母贏得了別的東西。這就是哲學思考,讓我們看到生活的多樣性,人生的目標本來有的多樣性。但是,在工具理性主導的世界裡,我們很容易被單一化。”
劉擎說小時候的自己好勝,還有虛榮心,考試會提前半小時交卷,但是經常會出錯誤。有一次數學考試的時候,他提前20分鐘交卷了,結果因為他寫括號的時候寫了一半,忘了另一半,得了98分,“那次老師叫我‘括號先生’諷刺了我,我同桌就笑了,我覺得她在譏諷我,我很不高興。要看她的考卷,她不給我看,我就很長時間不理她,我覺得她肯定是比我低才不會給我看,後來我才知道,她是100分。我突然第一次感到非常羞恥,我後來對那個女生非常尊重,我覺得她很尊重我,知道我好勝心很強,所以寬待我,她好了不起。我覺得她給我上了哲學的第一課,就是那種沉默的溫和的力量,而我跟她相比就像不懂事的小男生,很張揚。所以我覺得哲學需要一種敏感性。”
溝通的意思不是我同意你
而是我們彼此可以理解
有一位讀者向劉擎傾訴他與父親的隔閡,講述他為溝通父子關係所做的努力,但效果不大,他為此請教同樣是父親的劉擎。劉擎首先直言,“不要認為現在你開始努力了,問題就能解決。就像人家說吃了五個餅才飽,你不能直接吃到第五個餅,這一切都在那個程序當中。”
劉擎表示,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在哲學層面上是他心理論,哲學家迦達默爾在60歲的時候寫了《真理與方法》,提到我們不可能站在別人的視角來考慮問題,因為你不可能成為別人,你不可能真正忘掉自己站在別人的視角。迦達默爾提出了“視域融合”,“他說我們可以建立一箇中間地帶,像一座橋一樣,我們試著藉助自己的經驗去理解對方的視域,然後彼此接近,雖然最終我們也不能成為對方,但是,我們可以主動積極地呼叫自己的經驗理解對方,比如說當你有了孩子的時候就可以理解自己的父母。”
劉擎建議這位讀者與父親一起做一件事情,“我建議你,我們停止跟父親談論,和父親做一件他特別喜歡的事情,做一件他嚮往但是沒有做成的事。這是我人生的教訓,我從小就喜歡跟人家說話,但有的時候發現說話是有侷限性的,要一起做些什麼。繼續去嘗試,當你和父親深刻理解,收穫和解的時候,你不光是修復了你跟父親的關係,你也修復了你跟這個世界的關係。”
現代人標榜個性,總是“我以為”,“我覺得”,而在劉擎教授看來,當你說“我認為”的時候,你已經不可能是一個完全孤立的自己的意見,你的意見是社會、是歷史輻射給你的。“我們現在之所以多元化,並不是因為我們脫離了社會,是因為這個社會高度複雜、高度多元。我們每個人從全球性的資訊觀念當中汲取不同的部分,所以造成我們大家有區別,有多樣性。但這不意味著我的這個想法是無中生有獨創的,沒有人有辦法獨創一個自我。”
所以,劉擎表示,當說“我以為”“我認為”的時候,這個陳述本身已經攜帶了社會性的資訊。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主觀之間的那個區別差別並不是沒有完全共同的平臺。“雖然我是用‘我’這個單數第一人稱來表達的,它總是隱含著一個複數的第一人稱,它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多元價值不意味著無窮的價值,我們是有限的,我們有限的價值彼此是可以溝通的,溝通的意思不是我同意你,而是我們彼此可以理解,相互尊重平等的基礎上,求同存異,這是我們的理想。”
而對於那些覺得自己無力改變工作壓力大、競爭激烈等現實環境,只能無所作為的那些人呢,劉擎教授也給予鼓勵:“我們並不完全被這個世界的結構所決定,我相信人是有自主性的,否則的話,我們就是一個決定論式的人。我認為人的努力是可為的,而努力是需要人的觀念指引的。”
文/本報記者 張嘉
來源: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