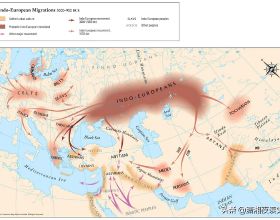在諸多中國史前考古學文化中,分佈於環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是耀眼的星辰。近年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新發現,使良渚文化所反映的社會組織形態、文明程度引發了新一輪討論熱潮。考古學界普遍認為,良渚文化已進入了早期國家階段。以良渚古城為中心的良渚遺址聚落群,顯示了其在整個良渚文化分佈圈內的核心地位。大型的水利工程、恢宏的古城、以琮璧為核心的玉禮器、神秘繁複的神徽影象,昭示著良渚文化的繁盛發達,是新石器時代屹立在東亞大陸的一支重要文明。對於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良渚文化扮演了關鍵性角色。
任何一種文明都有其自身的特質。那麼,良渚文明的特質是什麼?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稻米和玉器。
稻作經濟與社會複雜化
良渚文化所在的長三角境內河流縱橫交錯、湖蕩眾多。良好的水資源條件和適當的水資源管理對於稻作農業的發展極有裨益。從馬家浜文化開始,經崧澤文化,到良渚文化時期,稻作農業發展已較為成熟,當時已進入了犁耕農業階段,良渚人在水田中種植水稻。考古工作者在多個遺址(如吳縣草鞋山遺址、臨平茅山遺址、餘姚施岙遺址)發現了水稻田。臨平茅山遺址田塊的平面形狀有長條形、不規則圓形、長方形等多種,面積從一兩平方米到三四十平方米不等,田塊之間有隆起的生土埂。施岙遺址良渚文化稻田發現了由縱橫交錯的凸起田埂組成的“井”字形結構,顯示出良好的水田管理。

良渚文化玉璧,現藏於良渚博物院(左);吳家埠遺址出土良渚文化玉琮(右)。 葉一念/供圖
水稻田的出現及其規模的增長,加上有效的管理,帶來了稻米產量的提高。經考古發現,良渚古城中心的莫角山周邊出土了近40萬斤碳化稻穀,如此大的體量,可以窺見良渚文化稻作農業的發達程度。良渚古城和水壩均屬於大規模的公共工程,需要巨大勞力支出,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襯出工程建設背後的經濟基礎。
穩定發展的稻作農業帶來了稻米產量的提高,並引發了人口的增長。相應地,社會分工程度也更高,部分手工業專門化(如琢玉、髹漆、製陶等)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倘若沒有稻作農業的發達、稻米產量富足的保證,良渚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玉器工業,就會“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社會分工的過程也相應伴隨著社會分化,不同的人員依據各自專長所從事的專業也各有不同,帶來的結果,包括對生產資料的佔有、分配以及社會認同、地位和權力都會不同。
簡言之,稻作農業的發展在社會生產和生活領域會引發連鎖反應。社會群體之間人口構成或職業的“異質性”出現了,社會內部獲取財富和地位的“不平等”也形成了。而這些脫離“均質”和“平等”狀態的所謂“異質性”和“不平等”,正是麥奎爾(Randall H. McGuire)對“社會複雜化”所作定義的兩個關鍵概念。因此,稻作農業發展的成功與否和所在區域社會的複雜化程序有著密切聯絡。在漫長的歷史程序中,圍繞稻作、稻米而形成的生產、生活方式的文化認同也會不斷積累和固化。“飯稻羹魚”便是這樣的普遍認識。實際上,稻作農業的精耕細作一直是江南經濟的後盾,是塑造江南文明的重要因子。
玉器與文明
如果說稻米是滿足良渚先民生存的物質基礎,那麼玉器則具備物質和精神雙重層面的意義。良渚人開發、琢刻玉器既是生產力、物質生活層面的進步,也是追求身份地位和精神超越的體現。玉石既在審美的層面被開發使用,同時又具有宗教象徵的意義。
良渚文化是在崧澤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不但繼承了崧澤文化的玉器工業,又較廣泛吸收了凌家灘文化、紅山文化的治玉工藝、造型設計,開發出以琮、璧為代表的高度發達的玉禮器體制。玉琮、玉璧以及廣為分佈並表現出統一規範的神人獸面紋影象模式,反映了良渚人在藝術審美、影象設計、原始宗教信仰的開發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詣。事實上,正是良渚文化中數不勝數的玉器數量、種類、影象呈現了她的複雜化和文明化程度,同時也反映了良渚文化具有自身特色的複雜化模式,即如李伯謙所言的良渚文化是神權、軍權、王權相結合,但仍以神權為主的模式。毫不誇張地說,良渚文化發達的玉器是今天我們認識良渚文明,尤其是其精神文明的重要媒介,自然也是良渚文明的關鍵特質。如何理解良渚玉器和它所表徵的社會複雜化之間的關聯?我們認為,主要可以從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三個角度入手。
經濟層面,如前文所言,稻作農業是良渚文化的經濟基礎。經濟力量是植根於日常生活最深的一種權力資源。發達的稻作農業,反映了完善的水資源管理機制和成熟的社會分工模式。穩定的收成帶來了社會穩定,也會為區域社會的領導者帶來績效合法性。經濟力量增強後,人類創造和累積其他財富的能力也相應增強。體現在玉器製作上,自馬家浜文化開始,玉璜、玉玦等玉器種類已經出現,到崧澤文化時期,玉器工業進一步成熟,玉器種類開始增加,從簡單的單體玉飾發展出成套配件,工具也開始玉禮化。到良渚文化時期,玉器種類繁多、配伍複雜、等級分明,達到了史前玉文化的巔峰。
政治層面,政治權力的擁有者具有或大或小的支配權。張忠培認為,依據財富和權勢,良渚文化居民自下而上可分為四個等級。第一等級是掌控政權的神王;第二等級是掌握軍權的人;第三等級是具有行使軍事職能權力的兼職戰士;第四等級是下層從事農業勞動的居民。不同階層、等級的人員和玉器擁有方式的關聯度是非常突出的,不同群體和人員間圍繞玉器存在著競爭與合作。貴族階層透過一系列玉禮器的生產、分配和使用確立了禮儀制度,掌控了政治、經濟和軍事權力。因此,玉器是體現社會複雜化“異質性”和“不平等”特點的貴重物品。
意識形態層面,不同於石器、銅器和鐵器,玉器不能作為生產工具而使用,不能促進生產力和直接帶動經濟效益的提高。玉為人類所喜愛,首先是因為玉是一種光彩之物。玉,石之美者。“石之美”,強調的正是玉的光彩,包括顏色、亮度。玉之美,會讓人產生視覺上的愉悅,進而將人類的感知引向神秘的領域。這並非虛言,《山海經·西山經》中謂:“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御不祥。”楊伯達曾提出,玉之美是衍生事神之舉的土壤。牟永抗也曾論說:“玉之所以能夠在中華民族的心理上造成如此深刻而長遠的影響,其原因之一是因為這種被賦予‘山嶽精英’的礦物,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誕生起了催化酶的作用,從而將隨著文明而來的政治權力,牢牢地包裹在了神秘的袍套之中。可以說超越自然屬性的玉和政治的神秘化共同熔鑄了中華民族的心理素質。”很多文獻和人類學資料都表明,人類的確是將玉當作非凡之物來對待的,玉在人類的巫術—宗教經驗中是有意義的,玉具有神聖力量的潛質,成為人神溝通的媒材。
一旦玉器成為人類精神信仰領域的神物、靈物,就意味著另一層意義的“異質性”和“不平等”出現了,因為只有少數人能夠擁有玉器,並且利用玉器來和神靈世界溝通。張光直有一個著名論斷。他認為政治、宗教、藝術是結合在一起的,作為通天工具之一的藝術,是通天階級的一個必要的政治手段。包括青銅器、玉器、象牙器、漆器、木器、陶器、甲骨等,它們是古代薩滿在與祖先和神靈相溝通時所使用的工具。為了保持和神靈世界的交流,玉器不斷地被生產。與神靈世界有關的象徵物也被創造。就良渚文化而言,最典型的是“神人獸面紋”。
考古學界普遍認為,良渚人設計製作的這種統一規範的影象模式,表明他們在神靈崇拜方面,幾乎達到了類似一神教崇拜的程度。神人獸面紋無疑是一種影象象徵,具有布林迪厄所說的象徵權力。良渚人創造這種影象,既有他們對於宇宙、歷史、神話的認識,也在這種影象規範化的設計、分配、傳播過程中,傳遞和塑造了意識形態的權力。神人獸面紋在環太湖地區的廣泛存在表明其受到普遍的認同和崇拜,反襯了這種影象所承載的意識形態權力。這種意識形態權力還擁有一種合法化功能。比如,良渚權貴利用玉器和神靈世界建立了聯絡;或者玉器上琢刻的是神靈的影象。良渚權貴把握和操縱著這種意識形態權力,就進一步為他們贏得了政治權力、經濟影響力以及宗教主導權。
與此同時,良渚社會與其他區域的史前社會應該也存在著競爭。玉器的大量製作、玉器種類、神人獸面紋的開發設計,表明良渚人要發展出獨具特色的“文化產業”。這是一種雙向“超越”,良渚人既試圖超越其他地區的玉器工業,同時在滿足物質生存的基礎上,曾經努力建設一個屬於他們的精神世界,這個世界是從凡俗中來,又架構在凡俗之上的神聖世界。顯然,從良渚時期及良渚衰亡之後的玉禮器擴散情況來看,這些權貴們成功構築了自己的神聖世界,並向外進行了文化輸出,餘音繞樑,千年不絕。
從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三個角度統合理解,我們就能明白良渚玉器及其反映的禮制是如何調節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以及如何構建超自然的途徑與另一個世界進行溝通的。這些正是良渚社會文明化或複雜化程序中的內容。
成也米玉,敗也米玉
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在大致繁榮興盛了一千年後,盛極而衰。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先行者約瑟夫·坦特(Joseph A.Tainter)分析過二十多個由簡單社會進化到相對複雜的社會後走向崩潰的案例,並對此做了解釋。如今,良渚文化的解體也為研究世界古代文明的崩潰增加了新的案例。
關於良渚文化的解體,已經有相當豐富的討論。總結起來,大致有兩個方面:其一,是災變論。良渚文化分佈在環太湖地區,屬於近海、臨江、多水環境。從水災視角去分析史前文化的解體是完全合理的。俞偉超早先認為,4000多年前的洪水氾濫導致良渚文化的種種設施被摧毀,農耕之地常年淹沒,文明發展停滯了。很多環境學者透過尋找環境證據,也來解讀良渚文化的衰亡。可持續發展是今人分析良渚文化解體時不容忽視的原因。其二,是從良渚社會機制中尋找原因。以神權模式為特徵的良渚文明在玉器這類奢侈、威望性物品上投入過多,雖然對維護良渚權貴的政治統治有幫助,但同時也消耗了大量的社會成本。當社會的剩餘產量不斷投入維持複雜系統運轉而非供養民生時,維持系統運轉邊際支出必然掏空社會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根基不存,則社會崩壞,以玉器為中心的禮制無以維繫,社會複雜化程序停滯。
綜合來看,當經濟力量、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力量配合得當,社會結構會被賦予極大的穩定性。反之,若這幾種權力資源之間的辯證性互動出現不平衡,社會的正常運轉便會受到威脅。良渚文明的兩個關鍵性特質是稻米和玉器。這兩種物質相當於良渚文明的兩個著色劑,米和玉的“閃亮”和“黯淡”恰好對應著良渚文明的“興”與“衰”。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長江下游社會複雜化及中原化程序研究”(20&ZD24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師範大學文博系;武進博物館)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徐峰 施建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