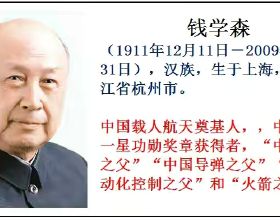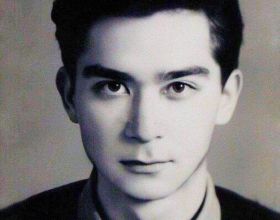這是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實驗室拍攝的劉永坦(2018年12月25日攝)。新華社記者王松攝
當白髮蒼蒼的他登臺領受2018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時,劉永坦——這個名字才廣為人知。
2020年8月,他將800萬元獎金全部捐出,用於國家電子資訊領域人才培養。
這一生,他只專注於一種國之重器——新體制雷達的研究。“只要國家有需求,我的前行就沒有終點。”85歲的劉永坦說。
從零開始,他幹了一樁“驚天動地事”
1990年4月3日,某地雷達實驗站。
時間彷彿在此刻靜止。一個紅色圓點,出現在一臺裝置的顯示屏上。
紅色圓點,代表著雷達監測條件下的目標。
人們開始忙碌起來:記錄資料、核對資訊、小聲交談或者大聲驚呼……目標確認!
人群中央,那個戴著眼鏡、臉曬得黝黑的人,熱淚縱橫。他身後,雷達天線陣迎風矗立。
他,就是主持這項科研工作的劉永坦。在這片滿目荒蕪的海岸線上,他帶領團隊奮戰多年,終於使我國新體制雷達實驗系統首次實現目標探測!
新體制雷達能突破傳統雷達探測“盲區”來發現目標,是海防戰線上決勝千里之外的“火眼金睛”。20世紀80年代初,少數幾個掌握該技術的國家牢牢把持著對海探測的資訊優勢,中國始終難有突破。
“怕家國難安!怕人民受苦!怕受制於人!”
1981年從海外留學進修歸來後,這“三怕”就重重地壓在劉永坦心頭。他深知,真正的核心技術,任何國家都不會拱手相讓。
從零開始!45歲的劉永坦義無反顧,向中國的科研“無人區”進軍。
10個月後,團隊建起來了,一份20多萬字的《新體制雷達的總體方案論證報告》出爐了!
“沒有電腦,一頁稿紙300字,報告手寫了700多頁,寫廢的紙摞一起就有半米高。”團隊首批骨幹成員之一、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張寧回憶說,劉永坦帶著他們沒日沒夜地寫了幾個月,一直寫到手指發麻、手腕痠痛,連雞蛋都捏不住。
一場填補國內空白的開拓性攻堅戰正式拉開帷幕。
當時,雷達實驗站的選址位於一片荒蕪地帶,批覆的經費不足,發射機、接收機等模擬系統和作業系統也十分落後。
團隊裡有人打了蔫兒,劉永坦話語鏗鏘:“如果沒有難點,還叫什麼科研!”
選址地遠離人煙,科研人員住在四面漏風的簡易房子裡,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干就是幾個月。
生活不便,他們經常用冷麵包充飢;交通不便,他們頂風冒雨,單程徒步3公里往返駐地和雷達站。每到天黑路過一片墳地,就用手電的光柱給自己壯膽。
1989年,新體制雷達實驗系統建成,中國人用8年時間,趕完了西方國家二三十年的路。1991年,新體制雷達專案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劉永坦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94年,他又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屆院士。
隨後,劉永坦帶領團隊從實驗場轉戰到應用場,著力解決新體制雷達實驗系統的實際應用轉化。

劉永坦(前右)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實驗室鑽研雷達技術(2018年12月25日攝)。新華社記者王松攝
劉永坦已是兩院院士,很多人勸他“歇歇吧”“別砸了自己的牌子”,他卻堅持:“科研成果不能轉化為實際應用,就如同一把沒有開刃的寶劍,中看不中用。”
設計——實驗——失敗——總結——再實驗……劉永坦領著團隊進行了更加艱辛的磨鍊,攻克了一個又一個難題。
2011年,具有全天時、全天候、遠距離探測能力的新體制雷達研製成功並投入實際應用,攻克了處於國際領先地位的核心技術。
一生不悔,他為祖國“永坦”永不停歇
美麗的海灘,海鷗不時高亢鳴叫。挺立的雷達天線陣也像這聰明、勇敢的精靈,永不停歇捕捉著來自遠洋的訊號。
在劉永坦看來,它們彷彿早已有了生命,是團隊中的“特殊成員”,凝結著很多人畢生的心血和夢想。他常跟人說:“我們團隊的特點就是不服輸、不低頭、不怕別人‘卡脖子’,大膽往前走。”
這又何嘗不是劉永坦自己的人生寫照?
1936年,劉永坦出生在江蘇南京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教師。
他出生後的第二年,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父親給他起名“永坦”,不僅是對他人生平安順遂的祝願,也是對國家繁榮昌盛的企盼。
從南京到武漢,從宜昌到重慶,劉永坦的幼時記憶,充滿了飛機扔下的“茄子”(炸彈)、被血染紅的江水、顛沛流離的逃難……
到了十一二歲,時局漸穩,劉永坦才有了一張安穩的課桌,開始如飢似渴地學習知識。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讀到幾本關於愛迪生、牛頓等科學家的少年讀本,邊看邊想:為什麼愛迪生能發明電燈,牛頓看到蘋果掉落能發現萬有引力,可我卻什麼都沒發現?
大科學家的故事彷彿打開了一扇窗,讓他看到了一個充滿神秘的未知世界。這個少年一會兒想搭梯子上天摘星,一會兒又想下海捉鱉,各種奇思妙想猶如潮湧。
昏暗的菜油燈下,母親常常教他誦讀古詩詞,陸游的《示兒》、岳飛的《滿江紅》,劉永坦跟著母親一字一句,抑揚頓挫。

劉永坦在家中看書(2018年12月25日攝)。新華社記者王松攝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他至今記得,母親每每讀到這句詞時那激動的神情和略帶顫抖的語音。
父親從不干涉他的志向,只一句話:“科學可以救國。”
那時他還不知,這種無法言說卻令人血脈僨張的感受,就是日後影響他一生的“家國情懷”。
1953年,劉永坦以優異成績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後作為預備師資被派往清華大學進修兩年。1958年,劉永坦回到哈工大參與組建無線電工程系,挑起了教學科研兩攤任務。
1965年,劉永坦主持並提出了國家“單脈衝延遲接收機”研製的總體設計方案,只可惜,“文革”打斷了這項科研任務,這個醉心於科研的青年插隊落戶到當時的黑龍江省五常縣。
插隊的經歷,讓他落下了嚴重的腰病,卻也鍛造了他堅韌的品格。此後無論順境逆境、時代變遷,他對科學的求索不變,少時的報國之志不改。
1979年6月,劉永坦登上了飛往英國的航班。他是“文革”結束後,中國第一批公派出訪的學者。
那時,在英國埃塞克斯大學、伯明翰大學的雷達技術實驗室,中國學生大多做的是科研輔助工作。
“我是一名中國人,我的成功與否代表著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形象。”
劉永坦心裡不服,他鉚足了勁,在實驗室裡度過了無數個不眠的日夜。
他的導師曾三次挽留這位來自中國的學生,因為“其科研成果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很出色”。
“跟你同期來的中國學生,有的已經同意留在英國了。”最後一次,面對導師的勸說,劉永坦依舊淡淡一笑,微微頷首:“再次感謝您,人各有志。”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如今,耄耋之年的劉永坦,依然沒有停下腳步。
在他的設計推動下,“21世紀的雷達”將在航海、漁業、沿海石油開發、海洋氣候預報、海岸經濟區發展等領域大顯身手,造福於民。
“一項任務完成了,就要開始下一項,只有研製出效能更好的產品,才能給國家交上滿意的答卷。”他說。
一輩子一件事,他始終“燃著一把火”
從最初的6人發展到30多人,劉永坦在自己的母校——哈爾濱工業大學建起了一支“雷達鐵軍”,帶出了新體制雷達領域老中青三代人才的“夢之隊”。

劉永坦(右二)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實驗室鑽研雷達技術(2018年12月25日攝)。新華社記者王松攝
他們中很多人,本可以站在講臺上成為教授,卻甘願跟著“坦院士”,紮根在偏僻清冷的海邊。
同事們說,劉永坦個子高大,看起來更像個大俠。學生們說,劉老師身上有一把火,點燃了每個人的“核心”。
團隊討論,大家七嘴八舌,“坦院士”總是靜靜坐在一邊,耐心傾聽,最後再總結髮言,尊重並吸納每個人的意見。
“他是干將,是帥才,更是父兄。我們敬重他,更不能辜負他。”張寧說,“坦院士”發自內心地深愛著這份事業,關愛著年輕人的成長,每當團隊有人科研進步或職稱晉升,他都會特別開心。
唯獨對家人,劉永坦有太多說不出的虧欠:到農村插隊,妻子毫無怨言相伴相隨;長年在外地,妻子一人撐起整個家,不讓他分心……
他們的家中,沒有豪華傢俱,最多的就是各類書籍和科研資料。他的書房裡,一塊閃閃發光、刻有“金婚之喜”的銀盤,赫然與那些獎章並列擺放著。那是2010年11月,學校送給劉永坦與馮秉瑞這對哈工大“科學伉儷”相伴50週年的禮物。
小小細節,藏著大科學家獨屬的溫情,更襯出他超脫凡俗的精神追求。
40年前,他本可以像大多數人一樣,選擇“更好走的路”:沿著西方既有路線做更容易出成果的研究,或者直接“下海”賺錢。
可是,他甘坐“冷板凳”,多少單位高薪聘請,都被他一一謝絕。即使在1991年和2015年兩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後,他依然低調無名地奮鬥在一線。
去年8月,他將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800萬元獎金全部捐給哈工大,助力學校培養人才。
今年9月,以他名字命名的本科“永坦班”迎來第一批“00後”新生,這是他寄予厚望的後輩……
劉永坦卻並不在意這些盛譽。“我們那代知識分子都是這樣,只想為國家做點事,國家的需要就是我們的需要,國家的需要就是我們個人的追求。”
中國科學院院士、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韓傑才說:“一輩子一件事,劉院士始終燃著一把火。”
統籌:王曙暉
記者:吳晶、陳聰、屈婷、楊思琪、王松、王鶴
編輯:王薇、冷彥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