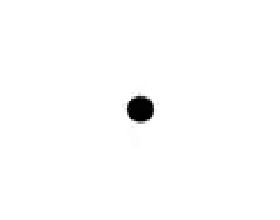前言
日軍在侵華戰爭期間,為了掠奪勞動力從事重體力勞動,在全國各地建立了很多的集中營。
集中營裡所有的俘虜,在進入集中營之前,都是先被抓進日本的憲兵隊,在那裡又被一個一個帶進設有各種刑具器械的拷問室中,被各式刑具折磨得皮開肉綻。他們必須供出誰是共產黨、八路軍或幹過有損於“皇軍’’的破壞活動。
不知有多少人因此而當場斃命。僥倖活下來的人,當他們被送進集中營時,以為鬆了一口氣,卻沒想到更悲慘的命運還在前邊虎視眈眈地等待著他們。在這裡日本人已為他們打開了無數條死亡通道,時刻準備把他們送入另一個世界!
這些集中營所關押的有共產黨幹部、抗日村長、八路軍、有抗日的國民黨士兵、有失去日軍信任的偽軍、還有被逼承認是八路軍的平民百姓。還有的是被日偽人員以賺錢為名誘騙來的青壯年。
王立風在被捕前是冀中軍區第十分割槽的譯電員,1940年日軍掃蕩時不幸被捕,被關押在位於石家莊的石門集中營。僥倖生還後他向外界披露了集中營內屈辱、殘酷的非人生活。
出早操
隨著尖厲的哨聲劃破了集中營清晨的寂靜。
“起床, 起床!”手持棍棒的漢奸看守們一邊吆喝著,一邊把那些戰俘們一個個趕起來。他們被推搡著走出牢房,到操場上排隊、點名、升旗、上操。
每天這個時刻,集中營裡一天中的第一個環節便開始了。全體俘虜按班次排隊,由各班長清點人數,然後向總班長報名,總班長再向日本隊長中村報告。他們一個個全都對上司畢恭畢敬,恭敬到近乎諂媚。然後日本中士班長木弟二從戰俘隊前走過,再次核實各班長所報人數的準確性,直到確認無誤,這才例行公事地記錄在他隨身所帶的筆記本上。
每天早晚兩次點名,不管你有病與否,只要能動,就得到操場上集合,除非一動不能動的,由總班長批准才能留在牢房裡。王立風在進入集中營前雖然被打斷了一條腿,但也被難友們攙扶著來到操場上。
操場上黑鴉鴉一片足有三四千人。
人們全是破衣爛衫、蓬頭垢面,身上的衣服都成了布條條,一縷一縷地掛著,又黑又髒的棉花翻露在外面。有的身上披著紙片,腰中繫著草繩,而胸膛卻遮蓋不住,任憑寒風的侵襲。
有的人打著赤腳,站在冰冷的地上,凍得他們一會兒抬起右腳,一會兒抬起左腳。他們的腳,凍得又紅又腫,凍掉腳趾的,爛了腳跟的,裂著口子,淌著膿血。
有的人把棉衣裡的棉花撕出來綁到腳上,以御風寒。這些人雖然大都是青壯年,但因飢餓、酷刑和傷病的折磨,大都骨瘦如柴,動作遲緩。
他們從被關進集中營開始,從來沒洗過一次臉,臉是灰黑色的,頭髮也滾成了氈子。他們站在那兒,形同一具具會動的骷髏,呆滯的目光,木訥的神情,說明了日本侵略者對他們從肉體到精神上長期的虐待和摧殘。
整隊點名開始了,各班口令聲不絕於耳。
在集中營中,每個人都沒有名字,只有被編成的代號,例如078、079號。被點名字的人必須大聲答到,聲音如果小了,就是一頓劈頭蓋臉的猛打。
“立正,升旗!”中村一聲令下,日本太陽旗緩緩升向集中營灰色的上空。
此時全體戰俘勞工必須面向日本本土方向行鞠躬禮,腰一定要彎到九十度,如果達不到要求,隨時都有槍托、棍棒向你背上掄過來。
升旗完畢,由總班長帶隊呼喊口號,什麼“日華親善”、“擁護新政權”、“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等等。口號要喊得整齊、響亮。如果誰張的嘴不大,喊得不起勁,被日本人看見,一頓毒打不說,還要被罰再喊十遍二十遍,直到他們滿意為止。即使這樣,有的人趁敵人不注意,只高舉手臂張大嘴巴,卻不出聲音。他們對日本侵略者的仇,豈是一個恨字能形容的!
喊完口號,接下來是分班跑步、做操。病號不能跑步,也得在操場邊上站好隊看著別人上操。誰要跑不好就要捱打,哪個班跑得不整齊就要受罰。
此時菜園班的張二醜就正在受罰。張二醜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看上去有40多歲,今天是第一次上操,因不會做“齊步走”和“左右轉”的動作,被漢奸班長叫出來單獨訓練。
班長接連喊著“向右轉”、“向左轉”的口令,嚇得張二醜渾身顫抖、手足無措,越害怕越做不對。每錯一次,班長就劈頭蓋臉地打,直打得他口鼻流血、神志恍惚、呆若木雞,最後竟連“齊步走”也不會了,一側的手腳同時向一個方向擺動起來,狠毒的漢奸班長更凶地抽打他,直到他倒地不起。
無論是炎熱的盛夏還是寒冷的隆冬,每天早晨,他們必須拖著羼弱的身子去承受持續兩個多小時的“點名”的折磨。許多人跑著跑著,一頭栽到操場上暈了過去,一盆冷水當頭澆下,又使他們甦醒過來,第一眼看到的永遠是日本人兇惡的面孔。殘酷的現實每時每刻都在告訴他們,這裡離另一個世界實在不遠了。
吃飯
“開飯了!”
隨著一聲吆喝,兩個值日的俘虜把抬來的飯桶放在地上,大家圍成一圈,各自伸出自己的“飯碗”, 像乞討似的等候班長的“施捨”。
這是王立風他們從被抓至今,4天來吃的第一頓飯。 他們早已飢腸轆轆、頭暈目眩、前胸貼後背了。
班長開始給每個人分飯,每人半碗摻著沙子、黴氣沖天的高粱米飯,一飯勺水。人們沒有碗筷,早來的人揀了日本人扔的罐頭盒子當飯碗,用兩根樹枝作筷子,一些晚來的人沒有吃飯用的東西,乾脆用手抓著吃。
王立風他們新來乍到,當然沒“筷子”也沒“碗”。班長分飯時,有的用衣服前襟接著,有的雙手捧著。有的人動作慢了點兒,一下子沒接住,班長特意把飯扣在了地下,他們趕忙從地上捧起來,連土帶飯吃了進去,最後把地上的米粒也一個個揀拾乾淨了。
集中營裡的規矩,分飯後不能馬上吃,得等班長把飯分完,下令讓吃時才能開始吃飯。看著“碗”中的那點兒飯,肚子餓得“咕咕”叫,胃中越發火辣辣的難受,口中酸水直冒。只聽班長一聲令下“開吃”,人們三口兩口便扒拉完了,這飯是什麼味道,很少有人能說得出來。
菜一般是沒有的,偶爾做一次, 也是熬胡蘿蔔或發黴的蘿蔔葉,連一絲油腥也看不到。這樣的伙食,雖然不至於馬上把人餓死,但也談不上讓你活下去。
由於長期吃不飽,營養不良,許多人患了浮腫病,臉胖胖鼓鼓的,雙腿腫得又粗又亮,肉皮崩開了,往外冒著黃水,兩條腿像灌了鉛似的沉重。即使這樣,他們還必須拖著羼弱的身子,每天去幹十幾個小時繁重的勞役。有的人幹著幹著兩眼一閉,頭一栽便永遠地倒了下去。
飢餓自始至終伴隨著集中營內的戰俘勞工們,並且已超出了人們的忍耐限度。為了活命,他們吃老鼠、爛菜葉,甚至吃衣服裡的棉花套子。有的人到伙房裡運出的煤碴堆裡撿飯渣和爛菜吃。
在石門集中營圍牆西邊有一片菜園,菜園班的俘虜每天由日本兵押著來這裡幹活。在這裡勞動,日本兵看得很緊,唯恐俘虜們偷吃蔬菜。就是地裡的一些菜幫子、爛菜頭也得讓俘虜們拿回來交給伙房。
為了活命,為了一口吃的,有多少人被日本人打傷致殘,又有多少人為此而丟掉了性命。
一次,郝蘭所等幾個人被指派到日軍倉庫裡倒洋灰,看到倉庫的牆上釘著一張馬皮, 他們就偷偷割下一段馬尾巴,用罐頭盒煮湯喝。正煮著被日本兵田口發現了,一聲招呼四五個日本兵圍了上來,舉起手中的木棒就打。香川用手中的木棒,狠狠地向張振臣的頭上打過去,頓時血流如注,蓋住了他整個面頰。他搖晃一下身子,“咕咚”一聲倒了下去,身子抽動了兩下之後就一動不動了。
兇殘的日本兵打累了, 又把他們幾個反綁雙手,吊在集中營內壕溝邊的幾棵大柳樹上。這幾棵大柳樹,是集中營裡的絞刑架,每天都有人被吊死在上面。郝蘭所被捕前是我八路軍一個排長,還沒等把鬼子趕出中國,自已反到成了他們的階下囚,本來就窩著一肚子火, 如今為了一截馬尾巴又被吊在這兒,他實在忍受不了這樣的屈辱,破口大罵道:
“放我們下來,我們有什麼罪!你們這些狼心狗肺的強盜,我遲早要宰了你們!”
日本兵田口正牽著狼狗巡邏,聽到罵聲,立即放開手中的狼狗,指著郝蘭所說了聲“咪西、咪西!”那狗立即竄上去,一口下去,從郝蘭所腿上連衣服帶肉撕下一大塊來。
一口、兩口......郝蘭所被咬得遍體鱗傷,鮮血淋淋,罵聲漸漸地微弱了下來。
田口一聲口哨,帶著他的狼狗揚長而去。
當晚郝蘭所便含恨死去了。
其他三個人,一直吊了四天三夜,直到全沒了氣息才讓拉屍隊拖了出去。
日本人把戰俘的生命視同草芥,殺死一個人如同捏死一隻螞蟻那樣隨意,那樣輕而易舉。
喝水
在集中營內,比飢餓更難受的是沒有水喝。每天兩頓飯,只有在吃飯時每個班給半桶水,人多水少,每人只能喝上兩三口,整個集中營是一個飢渴的世界。
日本人不讓人們喝生水,說是為了戰俘的“健康”,然而他們又不給開水喝,讓人們忍受這無水的煎熬。
這些殺人不眨眼、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惡魔,披上一件華麗的袈裟,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樣子,說什麼“講衛生”、“為了戰俘們的健康”,只不過是掩蓋他們無端摧殘戰俘的一塊遮羞布罷了。
戰俘們每天超強度的勞動,大量的出汗,體內水分損耗大大超過常人,依靠日本人給的那幾口水怎能補充得上呢?
有的人渴得實在受不了,就到廁所去揀尿冰吃。
由於長期大量的缺水,許多人得了腎炎、膀胱炎和尿道炎,經常尿血,身體受到極度摧殘,許多人為此而喪失了生命。
石門集中營的院子裡,靠操場東邊的廚房附近有一口壓水井,渴得發瘋的人們經常冒著生命危險去偷水喝。從外面勞動回來趁日本人吃飯之機,各牢房派出身體較好、跑得快的人去偷水。看到一個牢房有人去偷水,其它牢房也紛紛出動,偷水的人在井邊亂成一團,你擠我搶。有的人到了井邊,顧不上裝水,先趴到地下喝灑到水窪裡的水。每到此時那些看守也蜂擁而出,揮舞著棒子劈頭蓋臉地向人們身上亂打,直到把偷水的人驅散。
喝不上水,不僅僅是石門這一個集中營,其它集中營也是如此。
陳克恭,1942年12月被關進了青島體育場集中營,他回憶當時缺水的情形時說:“渴比餓更難受。渴極了人們乘“放風’之機, 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齊擠向水龍頭搶水喝,只要水龍頭一開啟,有些人便靠上去用嘴喝,有些人則用手捧著喝,還有些人趴在地下喝。日偽軍每次都是用棍棒強行將人驅趕走,但即便這次趕走了,下次“放風’時又來。這裡管事的日偽人員,便想出了一個壞主意,在每個水龍頭下面的水池裡倒進糞水。但我們這些渴得不要命的人,哪裡還顧得這些!每當‘放風’時, 人們仍然一窩蜂地湧向水龍頭處搶水喝。”
在這幾大集中營中,喝水最困難的當屬塘沽集中營了。
塘沽集中營周圍是一片鹽鹼灘,沒有淡水。集中營做飯還得到外面去拉水,每天拉的淡水只供做飯用,哪管你戰俘們有沒有水喝。吃的飯是窩頭加鹹菜疙瘩,湯水全無。渴得人們嗓子裡直冒煙,舌頭都轉不過彎來。
冬天人們就吃房簷下的冰溜子和地上的積雪。近處的積雪吃完了,就偷著到較遠的地方去吃。有的人腳凍爛了出不去,又渴得難受,就爬到廁所吃尿冰;尿冰吃光了,他們就在廁所裡等著,等有人撒尿時央求人家把尿撒到自己嘴裡。
曾被關押在塘沽集中營的張文泉撰文回憶說:“一次我到廁所撒尿,就見幾個人趴在地上,哀求往他們嘴裡撒。聽著他們的哀求,我這心裡像錐刺一樣難受,可恨的日本人把我們的同胞們折磨到如此地步,連最起碼的生存條件都不給我們。當時我真恨不得手中有一挺機槍, 把那些侵略者全部都殺死!”
“面對自己的難友, 我無論如何做不出來,便對他們說:‘你們等著。’冒著被日本人抓住的危險,我跑到集中營邊上沒人敢去的地方,攥了兩個大雪球,分給他們幾個人吃。他們幾個人千恩萬謝,眼裡流出感激的淚水,而我的心裡卻在滴血。”
結語
生活在集中營內的中國同胞,連生命都無法保證,更別提人權與尊嚴。
僅倖存者王立風所在的石門集中營,從1938年建立一直到日本戰敗投降的2000多天時間裡,共計死亡20000餘人,平均每天死亡100人左右,可以說日軍所建立的集中營,完完全全就是一個食人魔窟,一個冷血、殘忍、毫無人性的食人魔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