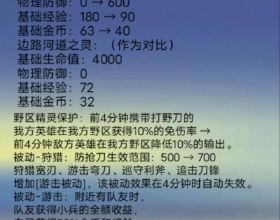一九九三年的梅雨時節,空氣悶熱潮溼,腳邊有蚯蚓蠕動,操場主席臺上老人正慷慨激昂地演講,十歲的我卻昏昏欲睡,又必須強作精神,以防被走過的老師看出思想開了小差。只聽臺上的人慷慨激昂地說道:
“小朋友們!你們今天能在這裡學習文化知識,一定要好好珍惜。想當年,這松木場可是殺人的刑場,是亂葬崗呀!”
這番話彷彿一道徹骨的寒冰,令人霎時清醒。我不禁抬頭四望。這個時刻就像是某個過去與現在的時空交匯點,那些被掩埋在腳下的陳跡,在恍惚之中,陡然變得清晰起來。儘管只有那一剎那。
第一道陰影
這是一座種植著雪松、法國梧桐和一串紅的校園,三面被居民樓包圍,後者建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六層樓,妥帖而溫暖,看不出任何異樣。另一個方向稍遠些是寶石山,穿過葉片,隱約能望見山上保俶塔的塔尖——每一個杭州人都知道,保俶塔是西湖的地標。
我的童年有一半時間在松木場地區度過,它充滿市井氣息,又毗鄰雨奇晴好、人人嚮往的西湖。所以,當十歲的我從前輩口中第一次聽說松木場曾是刑場和墓場,感受到的恐怖和震撼不言而喻。
從那以後,松木場在我心裡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它當然仍是我的樂園,但夜裡從興趣班下課、獨自穿過黑黢黢的巷弄,或者在寶石山南麓曲折往復的無人小徑玩耍時,我都能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陰森,彷彿有什麼無形的東西就在我身旁咫尺。第二年,我甚至在學校附近見到一位過世不久的親人,他微笑著和我迎面擦肩而過。那是一個陽光明亮的下午。
所有這些異象,也許不過都來自心底的自我暗示。但此後我陸續聽聞了一些松木場的都市傳說,甚至連我學校那幢外觀莊嚴的主樓,也被同學相傳有身穿血衣的清兵出現在走廊盡頭——那時清宮劇大行其道,也許是熒屏裡的哪個形象在好事的同學心中留下了長久的投影,但這些傳說仍比數十年後的種種荒誕的網路創作——比如“松木場河西怪童”“三號樓的水聲”——要更真實、更恐怖,至少對我來說如此。
“看見的,熄滅了;消失的,記住了。”
十歲那年,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是靜止的:房子不會舊,人不會老,漫畫永遠會有下一集。如果那時已經明白了時間是可以溯流的長河,那麼我就會發現,松木場並非一直是我感知到的樣子。
從有記載以來,松木場就不是杭州城的一部分。和所有古城一樣,杭州曾用城牆劃定城市邊界。而松木場在城外西北一里,水道綿延,是蘇、錫、嘉、湖等地民眾來杭進香的泊船碼頭,一度形成著名的香市。《徐霞客遊記》寫遊杭,“抵棕木場(即松木場),甫過午。令僮子入杭城。”松木場就像今天繞城高速外寫著“杭州歡迎你”的巨型廣告牌,一看到它,杭州市區就在前方不遠了。
清人吳農祥在《松木場香市》中寫到,“松木場邊看水生,綠楊紅樹隱商城。上方鍾罄珠林回,十里笙簫畫舫明。”直到1929年的《西湖遊覽指南》提及松木場,還提及“春時進香靈竺者,多泊船於此”,令今人仍可想見舳艫往來、香火繚繞的勝景。
但我想在此指出,松木場另有一段鮮為人知的過往。朱元璋洪武初制,要求各地設厲壇,以祀無主孤魂。杭州的厲壇就設在城外西北郊、松木場的金祝廟。每年清明、中元和十月朔這三大鬼節時要辦城隍會,市民從吳山城隍廟裡請出城隍像,在香花幡仗、笙簫鼓吹中游行、表演、祈願、狂歡,一直將城隍迎到厲壇,安撫那些無主孤魂。
金祝廟的廟志也記載,弘治年間錢塘縣令曾收集路邊和燒人場的“有頭男婦七百一十有七”及“無頭有骨不能計數共一十五棺”。它們被“集之於金祝廟前”,縣令率僚屬“親詣躬視”,祝禱後將之合葬。《錢塘縣祭遺骸文》寫道:“厲壇有祀,享之而已,何曾得一抔之安?”
美國學者梅爾清在《躁動的亡魂》中提到,“建造墓冢來埋葬、紀念無人認領的屍體,是對道德及政治價值的認可,同時也是情感撫慰。”然而松木場多孤魂的印象,不免在此處住民、乃至城內杭人的集體潛意識中暗自生根。對孤魂的記憶與想象,正是所有松木場怪談的源頭。
民國時,厲壇毀了,人間權力更迭如走馬燈,孤魂野鬼大概從此無法得救。松木場西段興建多批公墓,更闢出一塊處決人犯的刑場。無人認領的屍體就地掩埋,臭氣熏天。東段村鎮的香市也早因河道淤塞而蕭條。所以,儘管離杭州城只有一里之遙,但在老輩人持守的成見中,松木場既不是我童年那種市井花園,也不是近年房價高企的市中心一線學區老破小,而是荒涼可怖的鄉下地方。
上世紀中葉起,一切又變了。松木場河左近溼地被填,建省府辦公樓及宿舍。刑場遷往別處,新組建的杭州大學選址在刑場原址北,原址一帶建宿舍(現杭大新村)供教師居住。倖免於戰火的公墓多被徵遷。更西邊的浙江省第一公墓改建成浙江大學黃龍洞新校(現玉泉校區),松木場成為浙大師生進出杭城的要道。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松木場河被徹底填平,河道及周邊建起現代化的住房,松木場和杭州城的一里罅隙,被城市擴張初期的巨手草草撫平。
異界-時空
松木場是個有趣的案例,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介紹其歷史,是因為它暗藏了中國城市化程序中某一類都市傳說的來龍去脈。幾十年來,建成區的邊界飛速拓展,原本的近郊相繼變成城市新肌體,位於其中的私人墓地或年代久遠的公墓往往被徵用,新建住宅或商業設施;合規的公墓也可能被保留在新住宅邊上,令後者成為墓景房。同一片土地,過去死者長眠,如今生者寄居;或死者與生者為鄰。人與鬼的時空界限不再分明,植根於土地歷史的都市傳說便從這縫隙中生長出來。
但不是所有的新肌體都能結出異色的果實。大多數近郊鄉村沉默著被城市吞噬,沒有留下任何文化方面的記錄。美國民俗學家布魯範德指出,相信並講述都市傳說者“是當代社會中那些最為見多識廣的民眾——青年人、都市居民、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松木場的種種野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幸運地依託此地文化水平較高的新住民——國學家、大學生、機關幹部、技術人員及其家屬們所創作和口耳相傳的。他們在上世紀後半葉徙居而來,心照不宣地打造出一支民俗學意義上的文脈。
進入新世紀後,存世者大都選擇賣掉房子,搬到更嶄新、更宜居的區域,這支文脈也就隨之斷絕。那些流佈於前網際網路時代的傳說——例如松木場墓場舊址的某五星級酒店施工時曾挖出很多半腐的屍體,有工人拿腿骨打架嬉鬧,開業後客房就時常鬧鬼——由於較為零碎,缺乏整理,一旦當年的居民都不再以它為談資,便幾乎湮滅無聞。而網路上傳播較廣的“河西怪童”,文學創作痕跡明顯:從停車位、小區保安等元素以及行文習慣分析,應該是本世紀論壇時期的作品,和刑場、墓場等上世紀的歷史記憶已無關聯。
墓景房?都市傳說的空間想象
中國人認為,與死者為鄰會招致不祥。在志怪小說還沒有氾濫的年代,《三國志》記載的小故事已經暗示了這種心態:一位縣令因家人頻繁驚恐和生病,找來名卜管輅求救。後者認為,縣令宅第邊緣的地底埋著兩個持武器的死者,兩人的鬼魂白天浮游,晚上就來作祟。縣令按管輅說的位置掘出了骸骨,遷葬後家人都痊癒了。
原來,生者將宅第建在死者的埋骨之處,即使不知情,也會受鬼魂報復而全家得病。一千多年後的《聊齋志異》裡那位商人之婦更為無辜:她全然不知自己住的是少女自縊的凶宅,被那少女的鬼魂引導自縊而死。

《聊齋志異》,作者: [清]蒲松齡,譯者: 於天池(譯註) / 孫通海(譯),版本: 中華書局 2015年5月
生者所知有限,即便溯流而上,他們能觀測到的生活也自有其起點;陌生死者的生前事顯然超出了生者能夠掌握的時間線。死者鬼魂作祟,更像是故意對生者施以懲罰——因為生者無視了歷史。看來鬼魂不好惹,孔子的金句“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從這個角度理解也未必算錯。
在很多其他文化裡,無論和死者共享時間的墓景房,還是和死者共享空間的凶宅,都未必是大忌。拉雪茲神父公墓早已成為著名景點,附近的巴黎市民非但不視為不祥,相反還引以為豪。東京街頭也常能看見成片的墓地,這當然是城市擴張的後果,但政府無權強制屬於私人或寺廟的墓地遷走,它們才得以長留在城市新腹地,成為繁華寫字樓和住宅間的風景。反正神道傳統也令不少日本人相信,無論草木山石還是死者,都有機會成神守護一方,生活在墓地周圍的人不但不會遭報復,反而會受到庇佑。
近幾年,連凶宅在日本都漸受歡迎。不論自住還是投資,無非圖個便宜:跳樓自殺,九五折;兇殺,五到六折。在老齡化、孤獨死和房屋空置等社會問題面前,即使日本盛產的凶宅類都市傳說,也有令人深思的新解。
最後的活標本
松木場不是六本木。未來漫漶不清,過往正在褪色——房地產調控新政令學區房的光環漸趨黯淡;民間傳聞與論壇創作縱然曾於歷史縫隙中野性生長,也終將覆沒在網際網路新時代的音浪裡。也許,和所有被城市化程序同化了的肌體一樣,松木場只要當下。
至少杭大新村仍值得提一筆。這個小區和一路之隔的CBD同樣建於松木場刑場原址,曾住過夏承燾、姜亮夫等學者,如今卻破敗不堪。這種破敗已經持續了將近二十年,斷瓦頹垣隨處可見,有一幢矮房的外立面隱約可見毛澤東時代的大字標語。許多樓棟整幢空著,有些成了危房,“五好家庭”的門口貼著封條。極少數屋子似乎還住著人,我沒有見到他們,但他們在陽臺上將鏡子倒過來懸掛,據說是為了辟邪。
我靠近其中一面照妖鏡,正要觀察它,鏡子裡驀地閃過一個黑影。
時間凝住了。
我驚惶地轉頭——那是在枯枝和零落電線間跳躍的一隻小松鼠。
這一幕,便是松木場異聞錄最後的活標本。而一公里之外的西湖景區,來自各地的抖音和小紅書網紅們正忘情地錄製街拍短影片,笑容甜美。
接本局園林管理處林管字第二〇三一號報告為:“松木場花圃後面有反動統治時期所建置反動軍隊八十八師陣亡紀念牌坊兩座(一座系石頭的一座系磚頭的),另孤山路七星墳有竺氏墓道牌坊計三座,擬予拆除並將材料作為修建風景點用。上項牌坊是否可予拆除,拆下材料是否可用為修建風景,報請核示意憑辦理”
報告
杭州市人民政府 建設局局長,餘森文
(本文完稿次日,杭州市相關部門釋出規劃公示,推薦杭大新村為市歷史文化街區,並於近日獲批。)
撰文 | 張哲
編輯|李夏恩;張婷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