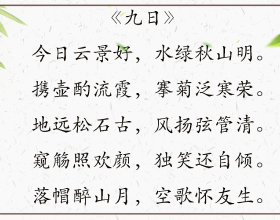喬是我的老熟人。
他跟我有好幾層關係。我小學兩年的同學,高中一年的同學,小時侯同一個院的鄰居,還有他算是我母親的同事。
近幾年,從母親嘴裡,以及從住在北京的王家姐妹那裡,不斷地聽說了喬的事。
我多年未見喬,忽然聽說他殺了人的事,很是震驚。當然,也是才知道那時他已經修佛多年。
喬跟我在二中的高一(1)班同學一年,高二分班時我去了文科班,他留在理科的1班。他高考不利,一連考了四年,也才上了電大。畢業後進了我母親所在的郵電學校上班,他專業不對口,最終進了學校的保衛科。記得某年在郵電學校的傳達室門口,見過他,我們並無交談,匆匆而過。
北京的王家姐妹,同樣是我們郵電學校家屬院的發小。她們家甚至跟我們家就住隔壁。她們姐妹仨,我家姐倆,從前熟得不能再熟。她家老大扶也是一連考四年,不過她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畢業後留在北京,成了自由編劇。三妹羽頂替他父親進了郵電學校,行政部做文員。她跟喬於是也成了同事。羽管喬叫“喬哥”。羽在郵電學校被關閉了之後買斷了10年的工齡,也來北京,學習寫劇本,混跡於大姐的圈子。她把喬的事用了編劇的本事,添油加醋,想象加虛構,講給我聽。
喬學佛多年,吃齋,常避谷。他本是高度近視的。我還記得他上高中時笑眯眯地眯著一對近視眼看人的神態。他其實是個極好的男孩。高高的,長得周正,兩腮有方的稜角。他進出樓,見了長輩都禮貌地打招呼。看到誰家樓上搬糧袋什麼的,還總熱心幫著抬。他跟我高一同班。班上有優秀女生玲,是班團支部書記。忽一日對我臉紅相告,她非常崇拜一人,我問是誰,曰“喬”。我知道,喬跟玲同屬那種學習刻苦,思想上進,品德好的型別。在當時,是那種很“紅”很靠近“黨”的那種學生。惺惺相惜是可以理解的。
母親也是喜歡喬的。常誇“喬這孩子很好”。還提到喬有好文筆,在郵電學校校刊上發表的文章寫得如何生動。可有誰會想到喬竟然出了那樣的事。
喬不知何年信了佛。羽和扶也都是佛門居士。她們姐妹稱讚“喬哥有慧根”,學佛進步很快。家裡貢獻的果品放幹了,自己從來都 不會去拿來食用。神奇的是,多年修佛之後,時常眯縫著的高度近視的雙眼,都恢復了正常視力,且眼神十分明亮有神。
出事之前喬去了青海的塔爾寺。回時就帶了一僧人回家,在家吃住,每日一同打坐。一夜,二人入定已久,忽聞外面有高聲喧譁,喬被打攪,出門觀看端的,原來樓道里失火,有人喊救火。喬回得家裡,就變了臉色,厲聲對打坐的僧人說,“我看到你的心壞了”,於是就找了把刀,要挖開僧人的胸膛,聲稱“我要換一顆心給你”。僧人反抗,叫喊,當時的場面被剛好趕過來的喬的妻子看到。他家住一樓,從後窗可以看到裡面。喬同時切自己的胸膛,要把自己的心掏出來換給僧人,兩人都血乎啦啦的。僧人最終是死了的,喬沒事。一時間,樓外警笛聲響成一片。119,110,120的車全都趕來了。
人們說,喬是那天走火入魔了的。喬只關了幾天,就被放了出來。據說他二哥走了關係,弄了一份精神病診斷給喬,公檢法也有熟人,於是給撈了出來。喬依然上班,依然到各家收電費。可終於不再被允許收電費。因為有人反對,說一個殺人犯進到人家家裡,說不定什麼時候再出什麼事呢,誰不害怕啊。
他父母無法面對來自鄰居們的閒言碎語,很快離開,躲去了外地。喬終於不堪壓力,遠走南京。前些年我春節回去,碰到在樓後收拾花圃棚架的喬父,看起來很悽苦,提起兒子喬來只有嘆氣。為人父母,自己的人生或樂或苦,已經承擔了;孩子的苦痛還要長在自己蒼老的枝上,疼痛延續不已。其沉重其無奈其刻骨啃齧之狀令人唏噓。
我問及喬的近況,說是喬在南京的一個小雜誌社找到一份工作。
2009年3月24日於廈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