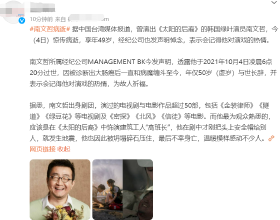鄭洞國曾是國民黨將領,他一生共做過兩件極具爭議的事——
第一件事是:遼瀋戰役中,他竟在給蔣介石發完“來生再見”的電報後,並未自殺,而是選擇了投誠共產黨;第二件事是:他深愛第二任妻子陳碧蓮,卻在妻子求複合時堅決拒絕。
這兩件事,不止普通人無法理解,就連鄭洞國的子女最初也很不能理解。
鄭洞國是湖南石門人,他是黃埔第一期學員。
抗戰爆發後,他先後率部參加了臺兒莊會戰、武漢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等著名戰役,且戰功卓越。後來,他又調任中國駐印軍新一軍軍長,並率部會同盟軍收復緬北。
也因為戰功赫赫,抗戰勝利後,鄭洞國越發受到了蔣介石的器重。1945年,他被委任第三方面軍副司令、代總司令等職。
1948年3月,鄭洞國駐守的長春成為一座孤城:東北人民解放軍收復永吉、攻克四平後,對長春採取了久困長圍的方針。此時,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所率的國軍只有十萬人,而解放軍則有幾十萬。
在這種情況下,鄭洞國等要想按照蔣介石的命令“突圍,以減少無謂傷亡”,幾乎已不可能。
但“不可能”也要嘗試,於是,鄭洞國數次率部進行了突圍,可每次他們都遭受了痛擊。突圍部隊回來時都感嘆:“共軍太能打了”。面對這種情況,鄭洞國一籌莫展。
150多天的軍事圍困和經濟封鎖後,國軍六十軍倒戈,新七軍投降。
此時,時間已經到了10月20日。 此時,國民黨敗局已定,可鄭洞國卻依舊在“堅守”在中央銀行大樓內。他這最後的堅守,和他同年同月出生的對手肖勁光大約看明白了:他一輩子戰功赫赫,肯定寧可死也不肯投降。
肖勁光猜對了。就在20日晚,鄭洞國就給蔣介石發了最後的電報,電報內容極其具有文人氣息,大意是“來生再見”,具體電文如下:
“新七軍死傷慘重,已轉移陣地,以中央銀行為據點。職等一秉革命犧牲精神,誓流最後一滴血,以報黨國,決不有負鈞座付託之重。”
也因為懂得鄭洞國的這一心理,即使勝利已在眼前,肖勁光卻只“圍而不攻”,他這樣做,自然是想給他一個“體面投降”的機會。
蔣介石接到這封電報後喜形於色,此時的他深知:國軍極其需要樹立典型。在遭受遼瀋戰役的大敗後,能樹立一個“自殺殉國”的典型,無疑可以很大地鼓舞士氣。
可就在蔣介石等著鄭洞國“自殺殉國”之際,準備於第二天凌晨自戕的鄭洞國卻發現,藏在枕頭下用來自殺的手槍不見了。不用說,他的手槍定是部下在得知他意圖後“拿”走了。其目的,自然是阻止鄭洞國做傻事。
對於當時的國軍和鄭洞國部下而言,他們早已厭倦了內戰,他們深知:內戰和昔日的抗日完全不同,它的目的僅僅是鞏固腐敗的蔣家王朝的統治。
鄭洞國的手下拿走他的槍,無異於逼迫他“投誠”。此時的他還未放棄“殺身成仁”的想法,他開始在屋內到處找能了結自己生命的器械。此時,一直守在門外的衛隊長文健和四名衛士聞聲跑來。
在他們的阻攔下, 他終於沒有“自我了斷”。
當天凌晨4點,銀行大樓外槍聲四起,可無論是東北野戰軍還是國民黨軍,他們的所有子彈全部都只射向天空。原來,他的副參謀長楊友梅等人,已與共產黨談妥,當日朝天放槍,佯裝抵抗後放下武器……
鄭洞國幾乎在半推半就之下參與了一切,因為他們並未真正抵抗,所以,他們的性質也不一樣:非投降,而是投誠。
關於這段,鄭洞國自己在回憶錄中是這樣講述的,他說:
“被擁向樓下,來到一樓大廳後,我怔住了,大廳里布滿了解放軍,我一切都明白了,面對這木已成舟的事實,我只得勉強同意放下武器,聽候處置。”
長春發生的一切,蔣介石自然知情。他對鄭洞國的選擇極其氣憤,但他卻依舊不肯放棄這次“樹典型”的機會。
於是,鄭洞國投誠三天後的10月24日,南京國民黨《中央日報》發表了《鄭洞國壯烈成仁,三百官兵全體殉職》的悼念文章。
這篇悼念文章被見報、被廣播時,鄭洞國正神情沮喪地在肖勁光司令員的宴席上悶頭喝酒。此時的他心裡別提有多鬱悶了,畢竟他已知道:自己已經被蔣介石“宣告死亡”了。
或許也正因此,後來,他曾提出了三個投誠要求:
“一是不能把他投誠的事情見報、廣播,只當他已經戰死了;二是他不參加我軍組織的公開宴會活動;三是不會出任政府職務,以後就做個平民百姓。”
從以上種種可見:鄭洞國絕不同於其他的國軍將領,他實際更像一個文人,相比普通殺伐決斷果敢甚至有些莽撞的武將,他更加謹慎,而他的謹慎則源自他“深於思考”的文人特性。
根據後來鄭洞國在回憶錄《我的戎馬生涯》裡的講述,他當時提出這三個要求時,就想了很多。在講述他拒絕出任政府職務時,他的表述是:“我對共產黨不瞭解,我並不知道他們的宗旨是什麼。”
鄭洞國沒有想到的是,他投誠後的要求,共產黨全部滿足了他。
國民黨的悼念文出來後,鄭洞國的妻子陳碧蓮也得知了丈夫的“死訊”,她為此痛哭了幾日。得知丈夫並未自殺而只是投誠後,她自然欣喜不已。經歷丈夫“死而復生”後,陳碧蓮的心理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在此之前,陳碧蓮和丈夫的關係可以用“生死相許”來形容。鄭洞國先前在雲南抗日時,她就曾不遠千里前往軍中。在軍中,美貌的陳碧蓮還主持軍中慈善募捐舞會,並被軍中上下美譽為“怒江之花”。
1943年,鄭洞國駐印度時,陳碧蓮也不遠萬里乘飛機飛越駝峰航線,來印度與他相會。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裡,她不管不顧的追隨,無疑深深感動了他。也正因此,即便妻子不能生育,他也從無怨言,他甚至還同意抱養了陳碧蓮弟弟的女兒為養女。
妻子問他對於自己不能生育有無遺憾時,已與故去妻子生育多個子女的他說:“沒關係,我已經有了很多孩子了,往後,有你和女兒(養女)就夠了。”
1945年,鄭洞國和陳碧蓮及女兒定居在了上海,彼時,他正擔任京滬衛戍副司令。此間,兩人的感情更是恩愛有加。
鄭洞國駐守長春時,知道形勢嚴峻的陳碧蓮還於1948年9月,滿含深情地給丈夫寫通道:
“桂庭(鄭洞國字):幾個月來為了你的安危,使人時刻不能忘懷,寢食不安。桂庭,令人衰弱與憔悴的不是歲月,而是憂愁,數月來我身體壞透了,較前更消瘦多了!桂庭,你們被困在這孤城,到底要緊不?”
言辭間,陳碧蓮流露出的全是對丈夫的牽掛之情。所謂“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大抵如此。
在最困難的時候收到妻子的信件,無疑讓鄭洞國心頭一暖。在這封信裡,陳碧蓮還巧妙地透露了自己對丈夫駐守長春的態度,她說:
“你真太大意了,你不顧性命在幹,這是為了哪種?上天保佑你平安。應該很平安,因為你向來對人都好,心更好,應該有好報:秋風起,更愁人也……”
陳碧蓮這話是在告訴丈夫:我只要你平安,其他的諸如榮華富貴一類,我全不在意。
真實情況果真如此嗎?陳碧蓮果真只要丈夫平安嗎?答案似乎並非如此。
鄭洞國投誠後,便第一時間同解放軍將領抵達了哈爾濱。冬季的哈爾濱天寒地凍,與上海的溫潤是天上地下的區別。可在這種情況下,陳碧蓮第一時間趕到了哈爾濱同丈夫團聚。妻子的這個舉動,溫暖了鄭洞國的心。
也正是這一次北上,陳碧蓮感受到了北方的寒冷。一年多後,鄭洞國回上海治胃病,她亦隨之前往。
投誠後的鄭洞國因為一直做老百姓,所以他有了大量的時間,期間,想整明白國民黨為何會失敗的他,開始閱讀《毛澤東選集》、《馬克思主義》等。深入瞭解共產黨及其思想後,他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他認為:
“在改善民生和爭取民心方面,共產黨確實做得好,而且發自真心,不是國民黨可比。”
與此同時,共產黨將領的艱苦樸素作風和親和態度也深深感染了他。過去,在國民黨陣營時,大家都流行攀比,誰要是穿戴不好,那是要受鄙視的,可在共產黨這兒,艱苦樸素被認為是美德。
毛澤東主席在一次與他見面時,親自為他點菸的細節,更是讓他感慨萬千,他意識到:這是蔣介石絕對不可能做到的。而在與肖勁光等昔日對手打交道後,他更是深深為他們的謙和為人所折服。
思想發生改變後,鄭洞國對新社會和人民軍隊也有了不一樣的看法,慢慢地,他也萌生了要繼續發揮光和熱,為國家做貢獻的心思。
1952年,請求為國家繼續做貢獻的鄭洞國被安排在水利部門工作。當年6月,他告訴妻子:自己要定居北京,並任水利部參事和全國政協文史專員。
得知訊息後,妻子陳碧蓮竟怎麼也不肯和他一同前往了。無論丈夫和母親、弟弟如何苦勸,她也死活不肯北上。而她不肯北上的理由竟然是:北京太冷了,水土不服。
無奈之下,鄭洞國只得一人前往赴任。
鄭洞國絕想不到,妻子不肯前往的背後,實與她已經習慣了優越生活有關。鄭洞國出生在普通人家,他的父親靠種地和兼做裁縫養活他們一家。幼年時,他經常因為吃不飽飯、營養不良而生病,好在他成績優異,並在幾經波折後考入了黃埔一期。
相比鄭洞國,陳碧蓮的家境絕對稱得上“小資”,她是民國數得上名的“名媛”之一。
她的父親陳鴻藻為日本中央大學法學畢業生,曾官至江西省參議員,退出政壇後,他曾任廣州大理院推事(即今法院院長)和中山大學教授,又開辦多家律師事務所,是民國有名的大律師。
家境優渥的陳碧蓮不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生活上也從未吃過半點苦頭。嫁給鄭洞國後,她的生活也得到了全方位的保障。
可轉眼,因為丈夫投誠,他們的日子一落千丈,這讓早已過慣舒適生活的陳碧蓮很不習慣。在哈爾濱的那段日子,已經讓她深刻體會了“艱苦”二字的含義,這也是她談“北上”色變的原因所在。
另一方面,陳碧蓮與丈夫雖已結婚近二十年,可她身邊始終有追求者。加上他們並沒有生育子女,所以她在關鍵時刻有了離開丈夫的想法。
妻子的這些心思,鄭洞國也有所察覺。但他總覺得:妻子遲早會接受事實,隨他北上。
然而,就在鄭洞國還在寄希望於妻子改變主意北上時,他卻意外收到了妻子寄來的一張離婚協議書。
開啟協議書後,他發現:妻子早已在上面簽了字了。此時,距離他們分居剛剛一年時間。看到離婚協議書的那刻,鄭洞國正在新崗位上磨合,妻子在這時候寄來離婚協議書,無異於給他致命一擊。
鄭洞國知道,這份協議書:他只能籤!這是他最後的尊嚴。
簽字時,他努力不讓自己的淚落下來。簽完字的當天下午,他看著窗外的夕陽發了很久的呆。他想到了自己被蔣介石“宣告死亡”的事,如今,他又再次被妻子“宣告離婚”。他突然有一種說不出的悲涼:那種自己的人生完全不被自己掌控的悲涼。
好在,遭遇各種“心死”後,鄭洞國終於在新中國再次迎來了人生的高光時刻。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主席親自提議他為國防委員會委員,他還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和家宴招待。鄭洞國還在此後連續擔任了數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委,他還擔任了黃埔同學會副會長。後來,他更是擔任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副主席。
事實證明:是金子,在哪裡都會發光!到此時,被國民黨宣告死亡的鄭洞國,終於重獲新生!
與鄭洞國離婚的一路順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妻子離婚後的人生坎坷重重。
陳碧蓮離婚後迅速嫁給了一個鐘姓資本家,最初,他們的小日子過得還算不錯。可60年代,她的丈夫被捕入獄,出獄後,他不僅沒有工作還貧病交加。兩口子一度只能靠陳碧蓮離婚時分得的財產勉強度日,後來,他們甚至被逐出上海,並住到了蘇州鄉下。
第二任丈夫病逝後,陳碧蓮只得和弟弟陳澤森一家回到了上海,她在此間一直過著孤獨、困苦的生活。
另一邊,與陳碧蓮離婚後的鄭洞國在離婚三年後與35歲的顧賢娟結成了連理,兩人還生養了一個女兒鄭安玉。
顧賢娟容貌過人,她溫柔體貼,對丈夫的照顧更是無微不至。可因為身體不好,結婚僅僅17年,她便因病離世了。
到此時,即1972年。鄭洞國和陳碧蓮便都恢復了單身。得知訊息後的陳碧蓮趕忙從上海趕到了北京,此時的北京依舊寒冷,可她卻再也不覺得冷了。
再見時,兩人已經分別二十多年。四目相對時,雙鬢已斑白的兩人望著對方熟悉又陌生的容顏,終於忍不住抱頭痛哭。
正在這次見面時,陳碧蓮提出了復婚的請求,她的請求也得到了兩家兒女的一致支援。陳碧蓮和雙方兒女都看得出來:他還愛著她。可讓他們意外的是:他死活不同意複合。
當子女不解地去追問父親理由時,一向隨和的他竟會面露不悅。
這次會面後,陳碧蓮悵然若失地回到了上海。此後20年裡,他們一直有往來,她甚至常透過前來上海的鄭洞國子女及孫輩,給他帶她做的紅燒牛肉。每次她都說:“可一定要帶到,你們祖父最喜歡吃我做的紅燒牛肉了。”
與陳碧蓮有過交流的鄭洞國孫子鄭建邦也認為:祖父其實是想與她複合的,只是,他們之間總有東西擋著。他曾感慨說:
“陳碧蓮以她美麗清純的愛情,優雅時尚的風采,以及開朗灑脫的性情,曾那麼輕柔地沁潤著祖父這位鐵血軍人的心靈,這恐怕是他生命中的任何一位女人都不能企及的!”
鄭洞國無疑是愛著陳碧蓮的,每次子孫們談起她,他都豎著耳朵聽著,唯恐錯過一點點細節。可一談到複合,他便閉口不言。
後來,眼見陳碧蓮的日子過得艱難,在她以“鄭洞國前妻”身份向組織請求照顧時,他亦出手相助,併為她謀得了一個還算體面的工作,從而解決了她的生活問題。
從這些都可看出,鄭洞國心裡一直有她,否則,從來不肯“開特例”的他,為何會為她“破例”呢!鄭洞國愛卻不肯複合的原因,依舊與他身上的文人特性有關。
文人除了“善於思考”外,還有一個特點:他們都視尊嚴為生命,所以他們始終信奉“士可殺不可辱”。妻子在他最難的時候選擇離開,並迅速嫁給有錢人,對於當時落魄的他而言,無疑是一種侮辱。鄭洞國對妻子的愛越深,她這種行為對他的侮辱便有多深。
第三任妻子死後的二十年裡,鄭洞國再未有過任何感情。
1991年1月27日,獨身20年的鄭洞國在北京辭世,享年88歲。年75歲的陳碧蓮得知訊息後特地從上海趕來,見他最後一面。
當時的北京依舊寒風刺骨,陳碧蓮不能不想起自己昔日與他離婚時說過的那句:“北京太冷了”。
鄭洞國去世11年後的2002年,陳碧蓮對著前來看望她的鄭建邦含淚道:
"我這輩子最值得留戀的時光,是與你們祖父20年的婚姻生活;這輩子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當年不該與他離婚。"
說這話時,陳碧蓮已經86歲了,此時距離他們離婚也已經整整半個世紀了。聽到這話時,鄭建邦感慨萬千。
後來的鄭建邦每每回憶起祖父和陳碧蓮的種種,都忍不住感嘆:“相愛卻不能相守,真真造化弄人啊!”
但回頭看,弄人的又何止是造化?說到底,阻止鄭洞國再次接受陳碧蓮的,從來不是造化,而恰是愛!越愛,越容不下傷害,越愛,被傷害後的恨便也越難消。鄭洞國過不去的坎,何嘗不是紅塵男女都過不去的坎呢!
電影《One Day》裡有一句臺詞:“我還愛著你,但我們不能在一起了,因為我不喜歡你了。”這話的意思是:“你依然在我的腦海裡,依然佔據著很重要的位置,但是我對你再也不抱任何幻想,關於你的一切再也沒有了期待。”
想想,鄭洞國和陳碧蓮,不恰也如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