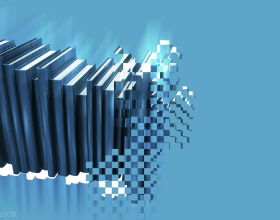一個冬末清晨,我頂著風雪被莫名其妙地吆喝到學校。與我談話的是學校的郭校長,看上去他年富力強,卻戴著一頂深灰色的咔嘰帽,披一件褪了色的黑棉褂,脖子裡只系一顆紐扣,走起路來兩個空袖筒一擺一擺的,好像自鳴鐘裡的擺。
沒到學校前,就聽村裡人說,郭校長是個好人,尤其是在抓教學上是把好手。我想如果能在這樣的領導下工作,倒是件樂事,起碼自己能學會點東西。
“村兒裡讓你來當代教,這是個機會。上午第一節課我去你教室,你準備一下吧!”郭校長惜言如金,他沒有注意到我的沉思,只用極簡練的語言道出了原由,並順便安排了工作,使人在絲毫沒有準備的情況下,踏上了他為你鋪設的軌道。
我接的是一位女老師的班,她因為生孩子,臨時替他代幾天五年級語文。讓人措手不及的是第一次上講臺,校長便要聽課,不能不使人有點心慌。
說實在的,我的確想把這節課講好。因為第一影響很重要,何況我一家三代都從事教育事業,平時家庭的薰陶和耳濡目染,我深深地愛著教育這一行。在沒有任何付出的情況下,上天竟賜給了我如此良機,我多麼渴望透過自己的努力教好第一節課,以求得孩子們的信任和學校的認可。
有道是:心有靈犀一點通。我驀然地想起了在城內教書的父親。他是個小有名氣的老語文教師,在治學上頗受人尊崇。我遂不顧風雪交加,便大步流星地疾進在茫茫的原野上。
從村裡到城裡相距七八里路,我任憑逆風撲面、雪粒入眼,懷揣課本,一股勁地往前奔著。不足半個小時,我便到了父親的辦公室,剛好他端了兩個熱窩頭正準備吃飯。當他聽說,村裡讓我當臨時代教時,竟喜不自禁,嘴裡還低低地哼起了我從沒有聽過的小曲子,我從父親的神態裡看到了上蒼的安排,恰好是老一輩的祈盼和欣慰。
父親見我急不可待,便非常麻利地將碗推到一邊,雙手捧書,全神貫注地如此這般,把我要講這一課的整個教學過程,非常詳盡得當地敘述了一遍。我不由的唏噓了一聲,茅塞頓開,便要起身,父親沒有攔我,順手塞給我一個半溫的窩頭,他把我一直送到校門口,看我沿著大路徑直而奔。偶爾回頭,我看見父親像鐵人一樣,在茫茫的風雪裡,一動也不動地站在校門口向我揮手。霎時,我鼻子有些抽搐,眼睛酸澀,不知是淚珠還是雪粒順眼角滑了下來。我使勁地啃著窩頭,消失在茫茫飛雪中。
當我急急忙忙地趕到學校時,清脆的預備鈴聲剛剛敲響,我稍微整理了一下衣著,撥拉了一下被雪團浸溼的髮梢,胸有成竹地跨上了講臺,進入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初為人師的角色。
課至半酣,我突然發現深灰色咔嘰帽下的郭校長,他坐在了最後一排,微翹起的二郎腿上端放著一個紅旗本,用一隻手捏得嚴嚴實實,另一隻手握著一枝鉛筆,偶爾飛快地記著什麼。一雙極有精神的大眼睛,像黑暗中發出的兩道電光直射黑板。我唯恐與他的眼神對視,只是默默地告誡自己:沉著冷靜就接近於成功。
我一字一板地重複著父親的“傑作”。無意中發現,班裡的孩子們儘管衣著不整,但他們卻精神抖擻,一個個伸直脖頸,屏息靜聽,或嚴肅,或微笑,或凝思,或體味。我雖然從郭校長的神態裡讀不出什麼,但卻從孩子們目光裡不難破譯,我這第一次走上講臺不至於丟醜。
課後,我主動毫不隱諱地告訴了郭校長,講課前去討教父親的經過。他照舊沉默,只是低頭笑了笑。繼而,他在一次村幹部會上極力推薦了我,致使我這絲毫沒有社會關係又不懂世事的初生牛犢,竟在那位女老師產假期滿回校後,沒有丟了飯碗,還覓到了一份合適的永久的工作。我衷心地感謝那難忘的第一次走上講臺與對我有知遇之恩的郭校長。
作者簡介:賈北安,山西省作家協會會員,縣作協名譽主席,縣老年人體育協會常務副主席,《老年體育》報、《門球週報》駐縣新聞主任。著有詩歌、散文集《賈北安文集》《故鄉月》《故鄉雲》等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