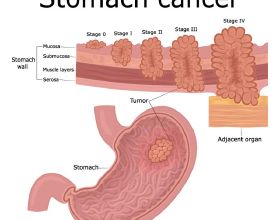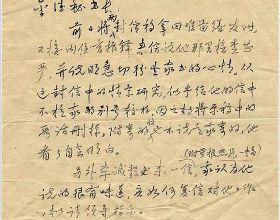楊振寧先生農曆100歲生日之際,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和夫人翁帆編著的《晨曦集》(增訂版)。該書收錄了楊振寧多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既有他放棄美國國籍的宣告,也有關於大加速器、高能物理等熱點問題的專論,兼及研究生培養等多方面的社會議題。書中也收錄了親人、同事、友人、媒體人和學生所撰文章,對楊振寧先生的成就和貢獻進行了充分的介紹和評述。
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9月29日,“中華讀書報”官方微信公眾號釋出了翁帆女士撰寫的文章《與楊振寧先生一起走過的日子》,這篇文章也是這一版《晨曦集》的後記。
翁帆在文中介紹:“新版《晨曦集》中另有兩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都是從幾幅舊照片談起。一篇是楊先生的發小與摯友熊秉明先生撰寫的《楊振寧和他的母親》。我記得初次閱讀後,對熊先生的佩服之心油然而生。讀者可以從熊先生對幾幅照片的描述中,看到熊先生作為藝術家與哲學家細膩而敏銳的洞察力。另一篇是李昕先生的《從楊振寧的幾幅照片談起》。李先生從歷史的角度講述楊先生的家國情懷。李先生的分析客觀而中肯,足見其作為一名資深文化人與出版人的修養。”
值得一提的是,翁帆在文中記錄了與楊振寧一起生活時的幾個細節,例如楊先生在香港時喜歡開車:“對先生來說,開車四處‘探索’是閒暇時的一大樂趣。我們最快樂的回憶之一便是自己開車穿梭於香港的青山綠水之間。香港給人的印象通常是高樓林立,其實香港的綠化率很高,達到70%以上。”
翁帆記錄:
楊先生喜歡開車,在85歲時才把開車的任務移交於我,在此之前,是他負責開車。那時親戚朋友常勸他不要開車,可他自己樂在其中。他在香港開車的確有過危險。香港車輛是靠左行駛,曾經兩次他在左轉彎時把車開到錯誤的一邊,迎面的大巴司機急得指著我們大罵。幸好那時大巴那邊是紅燈,所有的車輛停止不動,不然後果不堪設想。
那時我們開著一輛十多年的老車。楊先生第一次帶我翻越山林到沙頭角時,上山走了一段路後汽車的空調便失靈了。香港的夏天非常悶熱,開著車窗還是很難受,但是後來每每回想起來卻覺得十分有趣。楊先生的秘書跟我們提過好幾次:“換一輛吧。香港已經沒有人開這麼舊的車了!”後來,我們的確換了一輛新車,在前一輛車第十七個年頭時。
楊先生沒有因為自己不開車了而停下步伐。我剛拿到駕駛執照,楊先生就要我開車“上山下鄉”。那時初生牛犢不怕虎,我拿駕照沒有多久就開車上了太平山頂。通常汽車開到山頂廣場就會停下來,那次楊先生建議開到山頂。繼續往上走,路只有一個車道那麼寬,路的一邊是沒有遮攔的陡峭山坡。遇到下山的車時,只能其中一方退到稍微寬敞的地方讓行。這段路程對新手來說會感覺如履薄冰,可是已經走到一半,無法回頭,只能硬著頭皮往山上走。後來我問楊先生當時擔不擔心,他說一點都不擔心。
又有一次,我們開車上大帽山。大帽山是香港最高的山,海拔900多米。開車上大帽山並不困難,只是當我把車停到山上停車的位置時,我把油門當成了剎車踩,汽車突然向前加速。車位前面兩三米就是山崖,附近站著的幾個人都驚叫起來。幸好我反應快,立即換踩剎車,逃過一場災難。只是過後每每想起都心有餘悸。楊先生卻不當一回事,過一段時間他又提議上大帽山,被我堅定地拒絕了。楊先生笑話我道:“當初你和同學到內蒙古大森林揹包徒步,我還以為你很有冒險精神,沒想到你原來膽小如鼠!”不管他怎麼軟硬兼施,我再也沒有上大帽山。
相比之下,開車下鄉的記憶輕鬆明快很多。楊先生第一次請我吃飯是在西貢郊區海灣邊上的一個港式餐廳。餐廳有一排圓桌沿著沙灘一字排開,沙灘窄而綿長,人與海是如此地近,可以聞到海水鹹鹹的味道。海灣裡常有人練習風帆,再遠一些有白色的遊艇點點,再遠一些有大大小小的島嶼。後來,這裡成為我們最愛去的地方。十多年來,我們一有空便到這裡,面朝大海,看盡了這個海灣的春夏秋冬和日月星辰。
我最喜歡的戶外運動是劃橡皮艇。我喜歡在這個海灣裡划著橡皮艇到遠處的小島,沿途看臉盤大的水母,聽深深的海水撞擊岩石發出的深沉的咚咚之聲,猶如鐘鳴,讓人緊張而興奮。小島上沒有人煙,唯有白色的貝殼鋪滿地面。
楊先生只到過最近的一個小島,去遠處的島嶼我則不敢帶他同行。那邊的海水不如海灣裡那般平靜,手機也沒有訊號。有一次,他在岸上喝茶看報,我出海很久沒有返回,手機又聯絡不上,急得他差點報警。
西貢海灣在香港新界的東部。我們也喜歡開車一直南下,到香港島南面的石澳村看海。石澳的海邊有座小山,上山沿途可見巨大的岩石,海面廣袤無邊,景緻相當壯闊。回程我們通常會經過赤柱和淺水灣。有時在赤柱的大排檔喝一杯冷飲,有時在淺水灣大酒店喝個英式下午茶。
另一個我們常去的地方是新界北邊的鹿頸路。鹿頸路隔著海灣與深圳鹽田區相望。鹿頸路沿岸有紅樹林,海灣的小島上有成群的白鷺。運氣好的時候,會看到白鷺翩翩起舞。看完白鷺,我們在村裡的大排檔吃走地雞飯,老闆總會拿出自己收藏的好茶請我們品嚐。
楊先生總說,在香港不開車的話會錯過太多的美好。的確,香港的自然環境得天獨厚,就連沿途的自然風光也百看不厭。郊外的路徑和設施通常非常便利,又絲毫沒有破壞大自然的美感,一切人工干預恰到好處,不多不少。一路走來,總覺得十分舒暢。那些年,我們走遍了香港的山山水水。
現在,茶餘飯後談起那些時光,我們還總能體會到走在香港鄉村路上的明朗與舒暢。事實上,不僅在香港,在世界很多地方,我們都曾開車走過。我們曾在黃石國家公園(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和大提頓國家公園(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開車走了四天,那時還是楊先生開車,我拿著一份地圖當導航。我們合作完美,四天下來把兩大公園走了個遍,一路順暢。我們也試過自伯克利(Berkeley)開六個小時的車到太浩湖(LakeTahoe),那一次經歷也是非常難忘。
那時太浩湖區已經連續下了一週的大雪,我說去太浩湖太危險了,可楊先生堅持要去。那天,楊先生開完會已是下午4點,我們租了一輛車,從伯克利出發前往太浩湖。一兩個小時後,我們開始進入山區,雪又下了起來,越下越大。天也開始黑了,山裡的路已經積了一週的厚厚的冰雪,而我,從沒在大雪中開過車!楊先生提醒我:不要急轉彎,不要緊剎車。我謹記這兩點,在大雪中勻速前進,緊握著方向盤的手都握出汗來。更要命的是,我們租的車不是四輪驅動,而是一輛最最普通的小型轎車。我們怕湖區可能因下雪封路,就開啟收音機收聽路況,可是汽車無線電功能太差,或者是天氣惡劣的緣故,聲音極不清晰,只斷斷續續聽到重複著的“Highway×××...dangerous”(×××公路……危險)。
直到路經特拉基小鎮(Truckee),我們在快餐店問了一對從相反方向過來的夫婦,才知道前方的路沒有封,可以繼續前進。當我們抵達太浩湖邊上的酒店時,已經是晚上10點鐘。
第二天清晨,當我推開陽臺的門時,便知道太浩湖以她最美麗的姿態回報了我們的一路驚險。湖水藍得發綠,雪厚厚地覆蓋著屋頂,堆成柔和的曲線,長長的冰柱從屋簷垂掛下來。我們走在湖邊的路上,一腳踩下去,雪快及膝蓋。四處靜闃無人,只有時不時從松柏上掉下來的雪塊發出啪啪的響聲。
那些年,我們還試過在夜裡開車到火山附近,看噴發出來的熔岩流入海里。那些時光,都是源於楊先生喜歡四處探索的冒險精神。如果沒有楊先生的堅持,我大概會少了很多有意思的經歷和體驗。
有些初次和我們見面的人問我是不是物理專業,是不是楊先生的學生,我有時這樣回答:不是,他沒有教我物理,他教我開車。
欄目主編:張武 文字編輯:李林蔚 題圖來源:IC PHOTO 圖片編輯:徐佳敏
來源:作者:澎湃新聞記者 嶽懷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