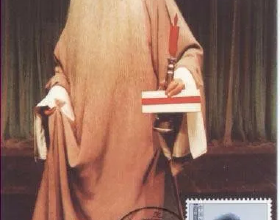前言
1989年清明,在北京西郊八寶山革命公墓陵園、一位頭髮灰白,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捧著一束親手栽培的鮮花來到原國防部副部長、空軍第一任司令員劉亞樓上將的靈前。
她的腳步很輕很輕,就像當年生怕打擾正在運籌帷幄的將軍。“亞樓,我看你來了。安娜媽媽的心願也已了卻,你可以放心了。”她的聲音很輕很輕,就像當年生怕驚醒因勞累過度和衣而臥的司令員。
她掏出手帕輕輕地拂去骨灰盒上的纖塵,就像當年為凱旋的親人拂去戎裝上的征塵。她把鮮花放在靈前,默默地凝視著鑲嵌在骨灰盒正面那張異常熟悉、倍感親切的遺像。
24年了,24個清明,每年清明她都會來這裡送去無窮思念,捧起不盡回憶。此刻,她那思緒的風帆又沿著歲月的長河溯流而上,回到了44年前那個大雪紛飛的冬夜……
“這位是劉亞樓同志,這位是翟雲英同志”
她第一次見到劉亞樓是在1945年歲尾的一個夜晚,姑娘時年18歲,正是豆蔻初開的年華。
在她那個年代,18歲已是婚嫁的年紀,多少痴情男子向這位出水芙蓉一般水靈的姑娘投去多情的目光,渴望她能丟擲繡球。但是姑娘自有擇偶標準,她理想中的“白馬王子”,應是一個英俊高大、威武瀟灑的真正男子漢。可是呆會兒將要見到的男子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此時的她異常緊張,因為王書記一會兒要給她介紹一位陌生的男子。就在這時,門外響起了停車聲和腳步聲,隨之房開被推開。
“這位是劉亞樓同志,這位是翟雲英同志,我們縣的婦女代表,一個十分能幹的女將”。王書記一邊熱情地招呼客人坐下,一邊笑著向雙方作著介紹。
“翟雲英同志,你好”。劉亞樓邊說邊伸出結實有力的大手。姑娘抬起頭,只見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正注視著自己,胸口禁不住突突地跳動起來。
眼前這位叫做劉亞樓的男子留給她的第一印象,就是英俊高大,威武瀟灑,一副大將風度。
劉亞樓作為一位在沙場逐鹿中屢操神券的虎將,在個人感情上卻屢屢受挫,發生了兩次裂變,幾年來一直是孑然一身。
一位哲人說過,任何一個單獨的男人或女人都是不完整的,他們都只是一個圓球的一半。只有男女雙方結合起來組成一個圓球,才能在生活的道路上滾滾向前。
劉亞樓也是一個凡人,他也有七情六慾,也需要女性的溫柔和體貼,需要另一半圓球的支援。而這一次,翟雲英進入了他的視野,他立刻就被姑娘的俏麗所吸引。
幾天後,兩人又在王西萍家中見面,這一次的翟雲英不再像上一次那麼羞澀了。她靜靜的坐在劉亞樓的對面,而劉亞樓也十分喜歡這位有著異域風情的姑娘,但兩度的婚姻裂變迫使他十分謹慎小心,他不希望在他的生活中出現第三次愛情危機。
“小翟,日本鬼子雖然投降了,但是蔣介石發動了內戰。我是個軍人,要上前線打仗,而打仗是要流血、死人的喲”。
“這我知道,革命總會有流血犧牲的。我的爸爸就是犧牲在日本鬼子手中的……”姑娘望著亞樓,敘述起自己的家史。
翟雲英的父親叫翟鳳岐,是1911年由東北逃亡到俄國去的華工。開始到遠東的海參崴、後來幾經輾轉,由遠東的赤塔、伊爾庫斯科到斯維特洛夫斯克,一直過著悲慘的苦力生活。
1917年,他親自參加了列寧領導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蘇聯國內戰爭中,為捍衛年輕的蘇維埃政權,參加中國苦力組成的中國獨立營,同自衛軍進行殊死的戰鬥。
這個營作戰英勇,曾得到列寧的表揚。後因他腰部中彈負傷,才調離開戰場,返回莫斯科,被分配到工廠當包裝工。
在那裡,他愛上了一位普通的蘇聯女工——安娜·卡茲米洛夫娜,翟鳳岐在蘇聯改名為崔發,蘇聯頒發的護照上就用的這個名字。
1925年,他們結了婚,成了家,過上了自由幸福的生活。1929年4月份,安娜·卡茲米洛夫娜隨丈夫崔發攜帶在莫斯科出生的兩個孩子(翟雲海,蘇聯名叫安德烈,1926年生於莫斯科;翟雲英,蘇聯名叫塔瑪拉,1928年生於莫斯科)回家省親。
崔發為人忠厚老實,非常孝順,回來是探望母親的。他母親因為想念這個逃亡在外的兒子,天天哭,最後哭瞎了眼睛,求人傳口信告訴崔發。
崔發得知這個情況後,心急如火,恨不得一下子飛到母親身邊,於是,便下決心回國。
回國後不久,就趕上“九一八”事變,簽證時間也過了,就這樣留在了國內。
崔發身上一直遺留著白匪軍射擊的子彈,因在危險部位,無法切除。留在國內後又遭到日本特務的百般刁難,工作無著患病死去。
說到這,崔雲英聲音哽咽,兩行熱淚滾滾而下。劉亞樓靜靜的聽著姑娘的敘述,心裡也捲起股股熱浪。他打心裡欽佩這位永遠不能謀面的老人,同時為姑娘深明大義、通達事理而暗自高興。
坦誠的交談讓他們的心貼得更近了,劉亞樓覺得時機成熟,便向翟雲英袒露了自己的心意。但當時劉亞樓35歲,翟雲英只有18歲。
一個正值豆蔻年華的妙齡少女,嫁給一個比自己年長17歲,且兩度結婚的男子,這不免會引起人們的議論,但對此翟雲英並不在乎,從小在苦水中泡大,很早就跟母親一起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擔的她,凡是都很有自己的主見,不會被這種世俗偏見所影響。
就這樣,1947年5月1日,由韓光同志主持,劉亞樓和翟雲英在大連舉行了簡樸而熱烈的婚禮。蜜月尚未度完,劉亞樓就奉黨中央之命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參謀長。
軍人的妻子,註定是要吃很多苦的,劉亞樓奔赴設在雙城的前線指揮所,翟雲英留在哈爾濱,兩人天各一方,過起了戰地的牛郎織女生活。
面對著別人夫婦雙人雙出,孤單的翟雲英曾試著對劉亞樓提出過“意見”,希望他能陪她呆上一會兒,哪怕是一會兒,她也心滿意足了。
但即使是新婚妻子這一點點可憐的“奢望”,也引得劉亞樓對她發了第一次火:
“前方那麼多部隊等著我。我是去管幾十萬人還是來管小家庭,管你?”
一嗓子就把翟雲英的眼淚吼了下來。她並不是委屈,而是深深地後悔,後悔自己給丈夫心中添了麻煩;後悔自己的想法對不住前方那麼多同志,更後悔自己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一個從小獨立慣了的苦孩子,怎麼竟溜出這麼句沒骨氣“家屬”的憨話來。
1948年春天,身懷六甲的翟雲英突然得了一種怪病,鼻腔流血,屢治不止。她深知丈夫軍務繁忙,責任重大,不想讓丈夫擔心。
所以她一直都沒有告訴劉亞樓,也不讓別人告訴。但她的病情一直在惡化,沒辦法,羅榮恆的妻子林月琴趕忙給前線打電話將劉亞樓喊了回來。
看著臉色煞白,有氣無力,病懨懨的妻子,這位淚不輕彈的硬漢雙眼發潮。
“為什麼沒有早一點告訴我?”
“我不想影響你的工作。”
“哎——你啊!”劉亞樓愛憐地撫摸著妻子的秀髮,重重地嘆了口氣。
劉亞樓四處奔走,八方求醫,最終找到一位經驗豐富的德國醫生。經過醫生的精心治療,最終將翟雲英從閻王殿門口救了回來。
“我怎能在國事活動中去處理家事呢!”
全國勝利後,劉亞樓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當時中國空軍一無所有,一切從零開始建設。繁忙的工作使劉亞樓無暇顧及妻子和孩子。
翟雲英也希望丈夫可以陪陪自己,但劉亞樓的確很忙,忙不完的工作,處理不完的軍務,看不完的檔案,開不完的會。
但好在黨內素有長者風範的羅榮恆夫婦常將她請到家中,一起吃飯,一起說笑。一次,翟雲英剛剛被林大姐叫到飯桌上,羅榮恆就笑呵呵地開了口:
“雲英啊,你是孤身從大連來的,在哈爾濱也沒有個朋友。我這兒就作你的孃家吧。亞樓如果有不對的地方,你就來告訴我,我好批評他!”一句話說得翟雲英激動萬分。
做妻子的還能說什麼呢?如果說雲英對其他事情都能理解,但有一件事情她卻無法理解。
安娜媽媽(翟雲英母親)從1929年來到中國以後,即和蘇聯的親人失去了聯絡。幾十年來,老人苦苦地思念著故國的親人,渴望和親人團聚。
每當亞樓去蘇聯訪問或會談,翟雲英都希望劉亞樓可以兼顧一下。憑亞樓這樣的職位,如果說一句話,請蘇聯有關方面查詢一下,也許不難找到。
但亞樓卻說:“國家和家事相比,國事重要,我怎能在國事活動中去處理家事呢!”為此,翟雲英不知抹了多少回眼淚。
不過安娜媽媽被接來團聚後,翟雲英再也不孤獨了。大弟弟也直接考入了何長工在佳木斯辦的“軍大”;小弟因年紀尚小,便仍留在安娜媽媽身邊。
翟雲英也正式進入了民主聯軍辦的一所學校,不久,又被批准轉正為中共正式黨員。
翟雲英所進的哈爾濱外國語學校設在馬家溝,延安俄文學校是它的前身。那年十萬幹部挺進東北。“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時,它被鞏固進來,從延河岸邊搬到松花江畔。
因是隨軍辦學,所以入校就等於入了伍,一律實行供給制。為了適應戰時體制,劉亞樓親兼這所學校的校長;另有兩位校長都是女同志,一對名副其實的“老專家”、“老革命”。
教員大部分是俄國人,也有中國人和“半俄國人半中國人”。李立三的夫人李莎也在這裡教學,並曾擔任翟雲英的老師。
功課很緊張,但生活也很愉快。
劉亞樓不常回來,若回來每次都會帶回一大堆“溫暖”,給安娜媽媽買塊布料;給小弟弟帶支鋼筆;還要給翟雲英帶些好吃的。
並且再三交待,等星期六雲英回來再吃!週末,翟雲英回來了,還熱心地領來一幫同學。大家吃著劉亞樓從蘇聯戰友那兒帶回來的糖,嘻嘻哈哈地鬧個沒完,還硬拉著劉亞樓這位“留學生”教俄語,親熱非凡。翟雲英幸福極了。
1948年6月15日,翟雲英生下了一個大胖小子。
為了紀念這段在哈爾濱戰鬥、生活的不凡經歷,劉亞樓給孩子起名為濱濱,大名劉煜濱。
兒子出生後,劉亞樓仍很少回家。翟玉英知道,丈夫是在為千千萬萬個大家而戰,她理解丈夫,但也擔心丈夫。
翟雲英深深記得,一次劉亞樓回家來時,正趕上敵機轟炸哈爾濱,只見劉亞樓當院挺立,高聲招呼大家快進防空洞隱蔽,自己卻像個炸不爛的鋼人一般,毫不在乎。
翟雲英在洞口連叫了他幾聲也得不到反應,氣得哭了起來。
有一次,很久未聞劉亞樓的音訊,可把她急壞了。她徑直跑到林大姐家,吞吞吐吐地透露了擔憂。林大姐立即拿起電話找到羅榮桓,向政委控告了劉亞樓忘記結髮之妻的“錯誤行為”。
電話中羅榮桓哈哈大笑:告訴翟雲英,沒有事,沒有事,亞樓出事我負責!”
得知丈夫一切平安,翟雲英總算放心了。但放心只是一時的,所以過了幾天後,當葉群和林月琴一起約她去看望丈夫們時,她便欣然同意了。
到了雙城後,她心中的一點點怨氣也沒了。那時,司令員林彪身體不好;政委羅榮桓又因癌症丟了一個腎。自然,軍事指揮之餘的日常值班重擔就落在了年富力強的劉亞樓肩上。
當她見到丈夫時,發覺劉亞樓的雙眼熬得通紅。參謀人員悄悄告訴她,參謀長已是三天兩夜沒閤眼了。
想想丈夫前要照顧幾十萬部隊,後要顧自己和兒子,翟雲英不禁對他產生了一股深深的憐惜之情。
翟雲英的家隨部隊搬到瀋陽,住進了一棟二層小洋樓裡。大弟弟隨所在單位遠行了。同來的有七八歲的小弟弟、安娜媽媽懷抱裡的煜濱和一個警衛員。
一天晚上8點多鐘,全家剛剛吃完晚飯,翟雲英正和安娜媽媽在樓上照料濱濱。突然“砰”地一聲,樓下分明開了槍。
“有敵人!”翟雲英猛然站起,飛身衝下樓去。安娜媽媽則一下子撲在外孫身上。
樓下的情景使翟雲英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警衛員一手持槍一手握布呆坐床上;小弟弟滿腿是血癱倒在地。原來警衛員擦槍時不慎走火,擊中了小弟弟腿部。
好在這一槍未打在要害處,未能妨礙小弟弟後來成為一名飛行員。可這一槍卻使全家留在了瀋陽,陪小弟弟養傷,不能繼續隨部隊南下了。

圖丨劉亞樓(左二)與葉劍英(右一),陳丕顯(右二)楊成武(左一)在天安門城樓
全家走不了,翟雲英就帶上孩子一個人走。她要去尋找遠在槍林彈雨中的丈夫,去陪伴他,照料他,與他共同走向勝利的明天。
“在這個家裡,我有三件事沒有做好,請你幫我做完”
1948年,劉亞樓司令員和翟雲英結婚後,因為戰爭形勢迅猛發展,一個戰役接一個戰役,劉亞樓開始吃不下飯,睡不著覺。
由於極度勞累,他的身體在一天天消瘦。翟雲英看到這種情景很心急,她想盡一切辦法,想分擔他的勞苦,卻又無能為力。
正在這個時候,上海華東醫大招生,部隊準備選送一批醫務工作者去深造,為部隊培養一批自己的醫生。劉亞樓得知這個訊息後,首先想到的,是讓翟雲英去學習、深造,掌握一門為人民服務的本領。
翟雲英知道這個訊息時,在腦子裡閃過深造的念頭,但很快便打消了這種想法。她覺得,司令員工作如此繁忙,應該留在他的身邊,照顧他,為他分憂,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她把自己的思想活動,這種入情入理的抉擇都向羅榮恆元帥彙報了,也取得老首長的支援。她心想,這種想法也不一定會符合司令員的心意,她滿以為,一提出來,司令員準會立刻同意。
最後的決定,完全出乎翟雲英的想象和估計。一天晚上,劉亞樓找翟雲英談話,他說:“你想留在我的身邊,照顧我,這種心情我非常理解。我又何嘗不希望自己的親人待在自己的身邊呢,當然我也這樣想過。”
說到這裡,劉亞樓拉著翟雲英的手,凝視著她那猶如一潭清澈湖水似的眼睛:“幾天來,我經常反覆思考,覺得這樣做
是妥當的。你很年輕,今年才23歲,精力充沛,應該學習,要抓住這寶貴的年華,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多掌握一點本事,將來會有用....總之,不該因為我,影響你的前程!”
翟雲英深知劉亞樓的脾氣,凡是他經過深思熟慮決定的事情是不會輕易改變的。他不是那種出爾反爾的人。她不爭辯了,聽從了他的安排。劉亞樓用詼諧的口吻風趣地說:
“雲英啊!有本事才能有飯吃,沒本事將來可就沒飯吃啦。要知道,我這個空軍司令可是靠不住的.....一旦我去見馬克思,你就得靠自己的本事掙飯吃啦......”接著他爽朗地哈哈大笑起來。翟雲英也會心地微微一笑。
歷史和時間再次驗證了劉亞樓司令當初以開玩笑口吻說出的預言。
1965年初春,劉亞樓感到身體極度不適,經檢查肝癌已到晚期。在病篤沉重之際,他把妻子叫到床邊,一雙乾瘦的手輕輕地撫摸著她的臉龐。
“阿英,我們在一起生活了近20年,你跟我吃了很多苦。你是一位好妻子、好母親,我從心底裡感謝你。如果說這些年我為黨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點成績,和你的支援是分不開的。我們在一起的時間恐怕不多了,你不要難過,死是客觀規律,誰也不能違背。在五次反圍剿中,在長征路上,在反法西斯前線,我沒有想到能活到今天。能看到革命勝利,看到人民空軍一天比一天壯大,祖國一天比一天富強,我已經心滿意足了。在這個家裡,我有三件事沒有做好,請你幫我做完。第一把孩子撫養長大,讓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第二好好贍養我的老父親,為他養老送終;第三務必幫安娜媽媽找到失散的親人,在這件事上我對不起她老人家,請她能諒解。最後我希望你做一個堅強的人,正直的人,像高爾基所說的‘大寫的人’。”
1965年5月7日,劉亞樓離開人世,時年55歲。
此時的翟雲英年僅38歲,中年喪偶,使她陷入生活的低谷,但她並沒有消沉,她將一腔愛傾注到三個孩子和兩位老人身上,認真地執行了亞樓臨終前的囑託。
她精心把三個孩子撫養長大,後來大兒子浜浜在中央新聞記錄電影製片廠工作,二女兒紅紅和小女兒珍珍均是軍隊幹部。
對劉亞樓的父親,她每月都會按時寄去生活費,後來自己沒辦法繼續寄錢給老人,她仍囑咐孩子按時寄錢寄物。
1978年老人壽終,她率子女風塵僕僕,親赴武平奔喪,料理後事,替丈夫盡孝道之情,被亞樓家鄉的人民傳為佳話。
劉亞樓交代給她的第三件事雖說費盡周折,但辦得非常漂亮。
1986年後她曾多次投書蘇聯紅十字會請求協助查詢親人。功夫不負有心人,她終於等來了回信。
她的舅舅早在1937年就已經離世,表哥一家都健在。聽到這個訊息,母女倆萬分激動,當即寫信邀請表哥一家前來北京。
蛇年之首,皓首白髮的米哈依洛維奇老人一家來到北京,時隔60年,95高齡的安娜終於在北京與親人團聚,了卻了一樁心願。
“亞樓,你要我辦的事我都辦完了,沒有辜負你的期望,安娜媽媽的心願也已實現,你可以放心了。”翟雲英凝視著劉亞樓的遺容心中默默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