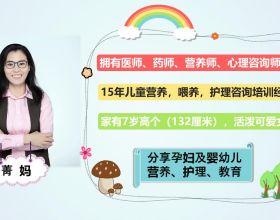“我是不可能離開這個湖的。我死後就埋在那裡。”老吳指著山坡上的土堆說。
我與老吳的初次相識,是在去年的夏天。
那是我第一次來支嘎阿魯湖釣魚。
支嘎阿魯湖原名水西湖(又名洪家渡水庫),水域面積達80平方千米,被稱為貴州第一湖。
“支嘎阿魯”這個拗口的稱呼,據說是彝族文化中極具影響力的一位神話傳奇英雄的名字,他在彝族人的心目中相當於漢族人的黃帝,是他們共同崇拜的祖先。
傳說支嘎阿魯在其故鄉黔西北曾經沐浴過的一片水澤,現在變成了一大神湖,就是我眼前的支嘎阿魯湖。
景色太漂亮了,湖水也乾淨,不過,在支嘎阿魯他老人家的洗澡水中長大的魚兒,對我這名遠道而來的釣友的態度就很不友好了。
那日,我在湖邊枯坐了一上午,除了偶爾一兩尾小白鰷或小馬口,目標鯽魚竟然一條未見。
就在我強烈懷疑那裡的魚兒搞地域歧視的時候,有個聲音突然從身後傳來:“釣到幾個鯽殼咯(貴州當地人把鯽魚叫鯽殼[ke])?”
這突如其來的一聲把我嚇了一跳,我扭頭一看,來人是一個老者(貴州當地人習慣把上了年紀的老人家叫“老者”,非不敬也),估摸60多歲的樣子。
他上身穿一件泛黃的白衣,下身一條黑色的褲子,褲管挽到小腿肚,腳蹬一雙皮鞋,已經髒得分不出顏色。
一頂破舊的草帽下,瘦削的臉上佈滿了皺紋,像一截帶皮的枯樹樁。他笑眯眯地看著我,話音中略帶些沙啞:“還是‘空軍’哦,你看嘛,魚護都沒下。”
我有點心虛,忙問道:“你們這點,釣魚收不收費喃?”
“收啥子費哦?沒聽說過釣魚還要收費的。你從哪裡來的?”老者用力地擺擺手,笑著問我。
“成都過來的。”我答道,心裡莫名有些慚愧。在成都周遭的大小水庫,釣魚收費是個常態。
眼前這個笑眯眯的老者,與那些穿著馬甲開著快艇呼嘯而來的收費員看來不是同一個型別。
他只是一個當地放牛的老農吧,我猜想。
“成都好,成都好啊!”老者說著,一屁股就坐在我釣椅太陽傘的陰影裡。
“重慶的人,也愛到我們這點來釣魚。”他說。
我沒接話,開始目不轉睛地盯著浮標,好期待這個時候能突然來個大黑標,讓咱給成都釣友長點臉。
然而,浮標卻如同焊在湖面上一樣,紋絲不動。倒是有水鳥從平靜的湖面掠過,氣氛一時有些尷尬。
半晌,老者打破了沉默。他指著湖面浮標的位置說:“你釣的那個地方,下面全都是草。”
“哦,是嗎?”我淡淡地應道,有點不以為然。
釣了一上午,抽了上百竿,我已經大概知道水下的情形。即使有草,也不會長得太高,畢竟沒有結束通話幾副子線啊。
“是的呢,就是我家牛吃的那種草。”老者慢條斯理地說,抬手指向不遠處,幾頭黃牛,正悠閒地咀嚼著湖邊平地上的野草。
有可能哦,草被牛啃過了,所以不會掛子線,我暗自尋思著。
“那個位置是個斜坡,陡得很。向前出去就是另一塊田,要深好幾米呢。”老者又說到。
完了,我打了那麼多的窩料,估計都滾到遠處的深田裡了,我暗暗叫苦。
老者仍笑眯眯地看著我,見我不說話,他俯身撿起兩粒小泥巴,站起來,向我釣點左邊的湖面扔去,說:“這邊位置下面有幾塊亂石頭,是我以前栓牛時用的。”
“這個下面呢,”他又向我釣點右面扔了一粒泥巴,“這裡以前有人挖了個土灶,有個大坑”。
老者這一番指點讓我知道,自己今天這屁股是徹底坐歪了。
水下這樣的地形地貌,打多少窩料也留不住魚啊,就是神仙也得“空軍”啊。
我內心戲碼正在激烈上演之時,老者又悠悠地說了一句:“你釣的這下面,沒得魚。”
這輕描淡寫的一句,徹底擊碎了我最後的倔強。
我再也顧不上外地釣友應該有的矜持和尊嚴了,趕緊從釣椅上起身,遞上一瓶礦泉水,說:“大哥,哦,不對,大爺,來喝水!大爺,你貴姓呢?”
老者也不客氣,接過水,咕嘟喝了一大口,答道:“免貴,姓吳。”
老吳是個熱心腸。
他說,這段時間漲了水,很多地方水下都是草,釣魚的位置不好找。
他又說,釣鯽殼魚要到有進水溝的地方,山上的水流下來嘩啦啦地響,魚會聽著水響,到灣子裡來“板籽”。水越響的地方,大鯽殼魚越多。
他還說,這水庫又叫洪家渡水庫,下游有個發電站,蓄水放水,落差大得很。如果不清楚地形,很難釣到魚的。
他不光說,還把我帶到一個叫“大溝”的灣子裡,然後向水面扔了一顆小石頭,指著泛起漣漪的那個地方,淡定地說:“你就釣這個點”。
我茫然地看著水面上一圈圈的圓環,猶如看著一個射擊的靶子。
看著我略顯遲疑和迷惑的眼神,老吳笑眯眯地說:“這下面是塊大青石板,我前幾天中午就在那上面睡瞌睡呢!”
投資界的大神查理·芒格說:“釣魚的第一條規則是:在有魚的地方釣魚。釣魚的第二條規則是:記住規則第一條。”
我沒親眼見過做股票的查老釣魚,但在去年夏天,在支嘎阿魯湖邊放牛的老吳卻讓我對這個道理有了真切的領悟。
那天下午後來所發生的事的細節,我已經記不清了。
我只記得,我在老吳“欽點”的位置——就是那塊他前幾天睡午覺的青石板上,打下了幾把窩料,將信將疑地等待過後,那種“久旱逢甘露,他鄉遇大鯽”的喜悅便像火山噴發般充盈著我的大腦。
後來,有釣友垂涎三尺地問我:“當時什麼感覺?”
我故作淡定:“也沒啥,就是1斤多的黃金鯽,連了18竿而已。”
釣友吞了吞口水,說:“我不信!”
直到我給他看了看當時的部分魚獲照片。
是的,當時的情景,的確有些夢幻。
驕陽斜照,青山倒映,湖面上閃爍著金燦燦炫目的光,耳畔是山溝的流水在嘩嘩地響。
魚兒吃口之瘋狂,讓我一度有了在養魚塘“斤釣”的錯覺。
不過,為了繃面子,我還是強壓著內心的狂喜,故作鎮定地裝出一副見過大世面的樣子;而老吳也在旁邊樂呵呵地看著我一竿又一竿地狂拉大鯽魚,似乎一切都是那麼稀鬆平常。
後來,魚口稍微慢了下來,感到手臂有點痠痛的我,帶著滿心的歡喜和感激,和老吳愉快地聊了起來。
也許是好久沒跟人聊天了吧,那天的老吳,話特別多。
春夏秋冬,水漲水落,老吳牽著他的牛,在支嘎阿魯湖畔慢悠悠地走過。這湖邊、山坡、水下的每一寸土地,每一道溝坎都回蕩過老吳哼過的山歌。
春天,水庫給灌溉區放水春耕了,以前被淹沒的層層梯田露了出來,很快長滿了青青的嫩草。天剛亮,老吳便牽上牛,從坡上慢悠悠地晃盪到谷底,青草把老牛的肚子脹得滾圓滾圓的。
清明前後,第一場大雨如約而至。高原上的雨下起來傾盆如注,山坡上的水溝很快變成了黃色的瀑布。
山洪夾雜著泥土,呼啦啦地注入湖裡,水位迅速漲起來了。
老吳在山上屋簷下看著雨,看著湖,他知道,只要雨一停,重慶的、貴陽的、遵義的,四面八方的釣魚人就會像趕場一樣,來趕這個一年中最好的釣魚時節了。
端午過後,天氣漸熱,水位也穩定了。湖水在高原的烈日照射下變得清澈湛藍,像極了藍色的寶石。被湖水淹沒的草地裡,各種蟲兒、牛糞、蚯蚓,把魚兒喂得飽飽的。
魚兒不咬鉤了,釣魚的人也就來得少了。那些夏日的午後,老吳會牽著牛,尋個湖水淹過的淺田,讓牛兒在水裡打滾泡澡,自己則找個陰涼的石板,美美地睡上一覺。
老吳說,這坡上以前是個寨子,住著十幾戶人家,有彝族,有布依族。你看到那些壘好的石塊,就是老屋的屋基。
老吳說,我們現在坐著的位置,以前是條小路,逢場的時候,寨子裡的男女老少就會背起揹簍,吆喝著牛,順著這條路下山,過河,到對面的集市上去趕場。
老吳說,坡上高處有一處泉眼,那裡接的泉水啊比街上賣的礦泉水還好喝呢!
老吳還說,山脊樑上有個土堆,寨子裡死去的人就埋在那裡,一眼就能望見這個湖。
老吳沉浸在他的敘述裡,像個孩子般手舞足蹈地講著。他口中的那些喧囂熱鬧的畫面,像電影鏡頭一般,一幀幀地浮現在我的眼前。
“哎,可是現在,都不在咯,都不在咯!”老吳說完,嘆了口氣,變得沉默。
我轉頭看向他,水面折射的陽光,打在他滿是皺紋的臉上,他眯縫著眼看著湖面,一動不動,像極了一座烏木雕塑。
後山坡上傳來個婦人的呼喚聲,老吳說,是他家婆娘在叫他呢。他懶得應。
“她曉得我喜歡跟釣魚的在一起吹牛玩耍。”老吳說。
“那你自己喜歡釣魚不?”我問。
“不得行咯,老了,看標眼睛不好用了。”老吳繼續說,“以前我兒子最喜歡釣魚咯”。
我正想往下問,突然看見一個大頂標,我趕緊提竿,沉甸甸的一尾大鯽魚上鉤了。
抄魚入護,我好奇地問老吳家為啥沒搬遷走呢?
老吳說,他家也屬於搬遷範圍,最高水位線剛好到他家屋前的玉米地裡。政府也補償了,城裡也有了安置房。不過,一年後,還是搬回來住了。
“婆娘不識字,城裡過不慣。我也喜歡這裡,空氣好,還能放牛。”老吳說。
“我是不可能離開這個湖的。我死後就埋在那裡。”老吳指著山脊上那個土堆。
“政府不攆你啊?”我問。
“哪會呢?當官的都是我學生,他們不敢管我的!”老吳說。
“你是老師啊?”我有點驚訝。
“嗯,退休快10年咯,現在也沒啥事,每個月8000多塊的退休工資,生病住院啥的都能報銷”,老吳說,“其實我們兩個老的,真花不了啥錢,政府這錢,發的有點多。”
看得出,老吳說這話時,真誠的眼神裡,有些落寞。
快樂的時光總是短暫,眼看太陽快落山了。
我看魚獲也夠多了,就這,發個朋友圈,足夠那幫城裡的釣友們流一地哈喇子了。
收拾東西時,我要送幾條鯽魚給老吳,老吳說什麼也不肯要。他說他家的魚多得吃不完呢。幾番推辭後,老吳把魚護裡的小白鰷、小馬口帶走,說回去弄了餵狗。
告別老吳,我登上了來接我的小船,跟船工老楊聊起老吳。楊師傅說,老吳是他們這一帶最有文化的人,哪家有個難事,都會去找他問問。
“他兒子呢?”我想起剛才沒來得及問的問題。
“喏,在那兒!”老楊指了指遠處山上的土堆說道:“那年徵地,打架,打得兇的呢,唉!”
“啊?是這樣啊!”
馬達轟鳴聲中,我趕緊回頭看了看岸上的老吳。
夕陽的餘暉照著他的背影,老吳揹著手,挽著褲腳,吆喝著牛,慢悠悠地往山坡上走著,身畔隱隱牽著一個忽長忽短的影子,在老吳的右前方也慢悠悠地往山坡上走著……(四川 ·何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