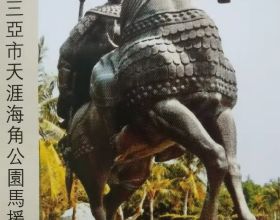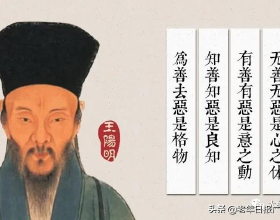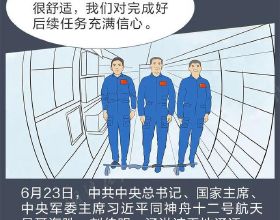唐人劉禹錫吟哦的“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我固執地以為指的便是湖南株洲淥口伏波嶺。
微雨的清晨,淥江像一個“濃睡不消殘酒”的女子,慵懶躺臥在暮春溼漉漉的天宇下,被天地間漫無際涯的蒼翠軟軟擁覆。我披裹堤岸上香樟漫溢而下的芬芳,沿北岸迤邐而行,將自己想象成唐代大曆四年(公元769年)二月踟躕江邊的杜甫,一串沉甸甸的詩句也隨之湧上心頭:“南嶽自茲近,湘流東逝深……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甕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
遭逢時艱,身世飄蓬,杜甫筆下的《過津口》不免抑鬱而沉悶,與我此刻探幽訪古的閒適自然不可同日而語。“詩家不幸淥口幸”,猶如沙鷗一般漂泊的詩聖能踅入淥口,慼慼然徘徊江岸綠蔭下,卻是淥口的大幸。簇新的村居高高低低,恬然散落江岸。嫋嫋升騰的炊煙間,我似乎見著了從盛唐淌溢而來的一縷詩意在漫漶,也似乎明白了居株洲鄙野的淥口,多年前何以突兀而出,成為遠近知名的“中華詩詞之鄉”。
緩步遐想時,岸邊突現一處蔥綠掩映的深潭,潭的另一側緊挨石壁陡崖。同行友人望著不高的崖頂,欣然說,伏波嶺到了。我心內一震,四野漫溢的文氣似乎陡然消隱,一股森然劍氣撲面而來。
中學時代,偶然讀到孫中山挽蔡鍔的句子“萬里間關馬伏波”,翻檢資料後,我頭一回知曉了“西破隴羌,南征交趾,北擊烏桓,累遷伏波將軍”,世稱“馬伏波”的東漢名將馬援。《三國演義》中殺得曹操割須棄袍的蜀漢五虎將之一“錦馬超”,便是其後裔。掩卷沉吟,不免神往於馬援馳騁疆場、立功萬里外的壯闊人生。
到株洲工作後,得悉馬援曾屯兵郊縣淥口的伏波嶺,似乎自己與他瞬間有了某種交集,親切感與自豪感油然而生。遺憾的是,伏波嶺近在咫尺,我卻懶怠起來,一直不曾登臨探訪。直到今天總算成行,真切立在嶺下,感受著森森撲面的劍氣。
我與友人輾轉尋路,踏上青樹蔭覆的青石板臺階,又拾級而上,置身於嶺上草木的蔥碧間,似乎自己的腳印已與兩千多年前馬援的某個腳印重合,臉上一時端肅起來。
伏波嶺確乎不高,與同處湖湘大地的南嶽衡山之峻拔、雪峰山之嵯峨不能比,上山的臺階不過幾十級,腳力未軟已登極頂,最多算是隆起的小丘。披風嶺上時,卻也一望空闊。腳下的淥江汩汩滔滔,在不遠處匯入湘江,又翻滾著浪濤,蜿蜒北去;四面群山逶迤,起起伏伏,像東海驀然倒灌而來,捲起一堆堆刺破蒼穹的巨浪;煙雨迷離中的淥口古鎮盡收眼底,它似乎有馬援的大將之風,“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嫻靜若閨中處子,安謐端坐群山之間與晨風之下。
轉過身來,便是劍氣漫溢的原點——伏波廟。廟宇也不大,紅牆青瓦,古樸雅緻,屋頂兩側的山牆格外醒目。門前挺立兩株衛兵似的大樹,亭亭如蓋。廟內馬援的塑像威嚴而立,目光如炬。我與他默默對視良久,內心頗為激盪,似乎終於見著了久仰的偶像。馬援當年“伏波”的一幕幕也穿塵封冊頁而出,耳邊似乎隱隱有了“鏦鏦錚錚,金鐵皆鳴”的聲響。
東漢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今屬越南北部的交趾郡發生叛亂,光武帝劉秀聞報,急拜善戰的馬援為伏波將軍,率軍千里南征。馬援旌旗南指,一舉平叛。往返時,或許見淥口“雄關控北流”,他便在這裡屯宿。邑人為紀其事,將屯兵的無名山丘命名為伏波嶺,又集資建廟宇,供奉香火,千年不絕。
馬援為後人景仰的不止平叛之功,還有其“馬革裹屍”的家國情懷。他曾慨然說:“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耿耿丹心,驚天地泣鬼神。
毛澤東對此感佩不已。早年赴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就學前,他抄送給父親一首詩道別:“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詩中意境與馬援的話千載相通。多年後的20世紀60年代,一位將軍不願去艱苦的非洲工作,毛澤東得悉後說:“我建議我們的高階幹部都讀讀《後漢書》裡的《馬援傳》。”
巧的是,毛澤東也曾登臨淥口伏波廟。1926年,淥口附近農民運動如火如荼,伏波廟成為農民協會的辦公場所。此後,毛澤東頂著料峭寒風,來到淥口考察農民運動,隨即登上伏波嶺,在廟內召開了工農商各界骨幹座談會。當他在劍氣漫溢的廟宇中慷慨陳詞,鼓動農運骨幹奮起革命時,或許想到過馬援的“窮且益堅”與“馬革裹屍”。在毛澤東下嶺後不幾年,楊得志、晏福生、劉先勝、楊梅生等人先後別離鄉關,走上革命之路,最終成為共和國閃爍的開國將星,也將馬援的英雄氣散逸到更高更遠的地方。
步出伏波廟,天空又飄起了雨絲。已闢成公園的伏波嶺上,樓閣、雕塑、翠柏與滿地奇花異草挨挨擠擠,在雨中靜默而陳,伏波嶺似乎更為矮小與侷促了。但須臾間,它在我眼前陡然峭拔起來,且似乎愈來愈高,聳入九重雲霄。我知道,這是因了一代忠勇的名將馬援……(張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