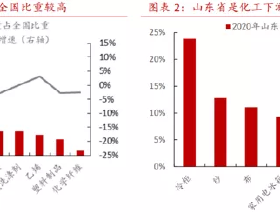埃德加·斯諾以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身份為人所熟知,他對中國人民、中國革命有著深厚的感情。1936年6月至10月,他訪問陝甘寧邊區,成為第一個採訪紅區的西方記者,寫下了那部著名的紀實性作品《紅星照耀中國》(又譯《西行漫記》)。1937年,該書一經出版便在世界範圍內引起轟動,銷量超過10萬冊,隨後多次再版。漢學家拉鐵·摩爾曾評論說,“書中介紹了人們聞所未聞的或者只是隱隱約約有點兒感覺的情況。那本書裡沒有什麼宣傳,只有對實際情況的報道。原來還有另外一箇中國啊!”然而,較少為大眾所瞭解的是,在《紅星照耀中國》之前,斯諾還曾花費大量心血,以英文編譯出版了《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一書,向西方讀者介紹一個他感受到的真實的中國。
1928年,埃德加·斯諾以記者的身份首次來到中國,開啟了他與中國的緣分。與當時大多數來華的外國人一樣,斯諾初到中國時,也曾認為中國人“低人一等”。但是很快,一次採訪讓他改變了態度。1929年,中國西部發生了極其嚴重的旱災,赤地千里,老百姓顆粒無收、食不果腹,許多地方鼠疫橫行。斯諾來到受災最為嚴重的內蒙古薩拉齊進行採訪,在那裡見到的慘烈情狀,讓他對中國人民產生了極大的同情。在他的相關報道《拯救二十五萬生靈》一文中,斯諾寫道:“我目睹了成千上萬的兒童死於饑荒,那場饑荒最終奪去了五百多萬人的生命。一路上,滿目淒涼,全無生機,就像剛剛發生過一場火山爆發。甚至樹也被剝光了皮,村子裡絕大多數的泥磚蓋的房子坍塌了。屋子裡僅有的一些木料也被拆去變賣幾個銅板。”受到極大觸動和震撼的斯諾,開始反思和批判外國人對待中國人的態度,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譴責生活在上海的外國人對西北的旱災無動於衷;此後,在《中國人請走後門》《僑居上海的美國人》等文章中,他多次就西方人對中國人的歧視、對中國的掠奪進行批判和諷刺。
此時的斯諾,已經擺脫了西方殖民者的歧視心理,開始瞭解一個真正的、現實的中國和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中國人民。而他也意識到,想讓中國人民獲得更多來自西方的支援和幫助,就要打破西方對中國符號化的刻板印象,讓真實的中國為更多西方人所瞭解。於是,他想到了文學。當時在西方能夠讀到的關於現代中國的文學寫作,往往為了投合外國讀者而刻意書寫異國情調,乃至誇大落後和陋習。這些作品,在西方讀者中加深了對中國人神秘、愚昧、麻木的偏頗認識。因此,斯諾覺得翻譯也許是更好的形式。他認為,只有中國人寫給中國人看的中文寫作,才能夠反映中國真正的世相世態和中國人民的真情實感。他想透過翻譯這些作品,把當代中國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介紹到世界,讓西方讀者瞭解“當代上層和下層的中國人,彼此之間真正是怎樣工作、行動、戀愛、玩耍”。他相信,在中國“正在進行時”的文學創作中,必然有“足以幫助我們瞭解正在改造著中國人的思想的那種精神、物質和文化的力量”。
彼時,中國文學的語言和樣式正在發生著偉大的革命。以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為開端的白話文運動已經如火如荼地開展了十年,新文學高歌猛進,魯迅、茅盾等最重要的新文學作家紛紛登場,創作出了一批優秀的白話新文學作品。但是,西方世界卻對這一變革所知甚少。究其原因,是因為西方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瞭解,主要依賴於西方漢學家,中國人在國際上既沒有語言的優勢,更缺乏話語權。然而,大部分漢學家對於中國文學和文化的興趣,僅限於豐富燦爛而又神秘強大的中國古代文明,而對於在貧弱落後的近現代中國土地上生長出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他們則興趣寥寥。同樣在中國生活過的義大利學者哈羅德·阿克頓曾批評當時的西方漢學界“對(中國)死的文學比活的文學更有興趣”。
而斯諾與一般的西方漢學家不同,他以記者身份來到中國,關心的正是當下的中國。他看到了中國的知識界、文化界正在發生著的非常重要的變革,認為這一變革正在並且必將發生深遠的影響:“世界上最古老的、從未間斷過的文化解體了,這個國家對內對外的鬥爭迫使它在創造一個新的文化來代替。千百年來視為正統的、正常的、天經地義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從而使一系列舊的信仰遭到摒棄,而新的領域在時間、空間方面開拓出來了。到處都沸騰著那種健康的騷動,孕育著強有力的、富有意義的萌芽。它將使亞洲東部的經濟、政治、文化的面貌大為改觀。在中國這個廣大的競技場上,有的是對比、衝突和重新估價。今天,生活的浪濤正在洶湧澎湃。這裡的變革所創造的氣氛使大地空前肥沃,在偉大的藝術母胎裡,新的生命在蠕動。”
因此,斯諾決定把白話新文學中那些優秀的、反映中國現實的作品譯介到西方去。最開始的時候,他以為這只是一個簡單的蒐集整理工作,只需要把已經翻譯成英文的現代文學作品收集起來,簡單加工便可。但當他著手去尋找白話新文學的英文譯作時,他驚訝地發現,這一領域近乎是一片空白——“重要的現代中國長篇小說一本也沒譯過來,短篇小說也只譯了幾篇,不顯眼地登在一些壽命很短的或是讀者寥寥無幾的宗派刊物上。”為什麼沒有白話新文學的譯介呢?他向許多外國朋友提出了這一問題,得到的答案是,當代中國沒產生什麼偉大的文學,沒什麼值得譯的。
斯諾並不認同這樣的回答,他認為翻譯當代中國文學作品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其文學性,更在於社會學的意義:“幫助我們瞭解正在改造著中國人的思想的那種精神、物質及文化的力量。”
“有幾個外國人之愛中國,遠勝於有些同胞自己”
斯諾著手開始編譯《活的中國》的時間,大概在1930年至1931年。如斯諾自己所言,與魯迅和林語堂的見面堅定了他對這一工作的信心。魯迅“胸襟寬廣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林語堂“狂蕩不羈的詼諧”使他愈發感覺到,晚近中國文學界一定有重要的作家,寫下了值得被全世界瞭解的作品。
有趣的是,當時的斯諾並不怎麼懂中文。不過,他很快就得到了幾位中國作家的幫助。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姚克。
姚克即姚莘農,是當時滬上著名的編劇、作家,畢業於教會大學東吳大學,中英文俱佳,是魯迅的知友。二人從魯迅作品入手,首先翻譯了《吶喊》中的幾篇作品,先是在美國《亞細亞》等雜誌上零散發表,後來收入到《活的中國》中。這一工作受到了魯迅本人的熱情支援和幫助。在編譯的過程中,斯諾曾多次拜訪魯迅,討教關於中國新文學的一些問題,魯迅給予了熱情的解答,在編譯的過程中,魯迅感受到了斯諾對中國真摯的熱愛,他評價說:“S君(即斯諾——筆者注)是明白的。有幾個外國人之愛中國,遠勝於有些同胞自己。”
在斯諾、姚克合作編譯魯迅作品的過程中,還誕生了一個重要的副產品。1933年5月,斯諾想要一張魯迅的單人照,在《活的中國》出版時使用。姚克為此拜訪魯迅,魯迅拿出一些舊照片來。因為新書出版以後要給外國人看,魯迅也很重視,兩人挑了半天,卻沒能從舊照中挑出一張反映魯迅精神氣質的。於是,姚克便和魯迅一起到上海南京路上的雪懷照相館拍攝了幾張人像,其中有一張魯迅的單人照。這張照片最早與斯諾撰寫的《魯迅評傳》一起,刊登在1935年1月出版的美國《亞細亞》雜誌上,以後又刊登在1936年底英國倫敦出版的《活的中國》一書的扉頁上。魯迅逝世後,萬國殯儀館供人弔唁的巨幅遺像,就由這張單人照放大而來。
除了姚克,參與具體編譯工作的年輕人,還有當時正在燕京大學讀書的蕭乾和楊剛。
編輯《活的中國》時,斯諾正在燕京大學新聞系擔任兼職講師,他“一無教氣,二無白人優越感”,平等、隨和的態度,讓學生們倍感親切。斯諾和他的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當時住在海淀軍機處八號的一座中式洋房(現北京大學西南門附近),那裡很快成了一批嚮往進步的青年學生“真正的課室”“呼吸一點新鮮空氣的視窗”。斯諾夫婦常常邀請青年學生來家中做客,跟他們一起閱覽國外的新書,熱烈地交流看法和觀點。蕭乾和楊剛都是軍機處八號的常客。在交往中,斯諾瞭解到二人經常為報刊撰稿,就邀請他們加入到了《活的中國》的編譯工作中。
蕭乾曾寫有《斯諾與中國新文藝運動——記〈活的中國〉》一文,詳細記述了他在《活的中國》編譯的過程中與斯諾的交往。
據蕭乾所言,當時頗有一些旅居中國的外國人,借地利之便,向西方兜售中國的文學和文化,甚至假充漢學家。他們挑一兩本中國著作,以低廉的價格,請一位“中國先生”口述翻譯,自己記錄下來,稍加整理便在海外出版,就算是親自“翻譯”了一本中國作品,絕口不提那位“中國先生”,一應收入更與中國人無干。而斯諾完全不是這樣,他尊重參與工作的每一位中國人,認可他們的貢獻,自己也絕不貪功。《活的中國》出版之時,他以編者而非譯者署名,序言中,他坦陳自己並不怎麼懂中文,多次感謝姚克、蕭乾、楊剛等合作者,並希望支付他們豐厚的報酬。1935年,蕭乾畢業當天,斯諾夫婦邀請他來到軍機處八號為他慶祝,並送了他一牛皮箱袖珍本的經典外國文學作品,蕭乾說,“那是我生平第一批藏書”。
蕭乾還記述了斯諾夫婦參與一二·九運動的情形。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斯諾夫婦始終同情中國學生的抗日活動,在一二·九運動中,他們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以外國人的身份保護學生,同士兵搏鬥,他們的家也成為受傷學生的臨時避難所。事實上,斯諾夫婦對一二·九運動的貢獻遠不止於此,他們利用自己身為記者的職業優勢,為這次學生運動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援。1935年12月9日運動爆發的當天,斯諾即向外國媒體傳送報道;12月10日,他在《每日先驅報》發表《三千北京示威者力促反抗,城門關閉,“我們是日本殖民地嗎?”》一文;12月12日,在斯諾建議下,龔普生、龔澎等學生在燕京大學臨湖軒召開外國記者招待會,介紹運動情況;一二·一六遊行的第二天,斯諾也在《每日先驅報》發表報道。除直接執筆撰文、發文外,斯諾夫婦還多層次、多渠道地聯絡英美媒體,斯諾本身就是紐約《太陽報》《每日先驅報》等媒體的駐華記者;他們還不斷加強與《密勒氏評論報》《芝加哥每日論壇報》《亞細亞》雜誌、合眾社華北分社及北平路透社的聯絡,引導國際輿論同情和支援學生運動,給當局施加壓力,也推進運動持續發酵。
“他不要文字漂亮的……他要的是那些揭露性的,譴責性的,描述中國社會現實的作品”
這樣一部面向西方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應當選擇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才能夠代表中國呢?魯迅當然是毫無爭議的。《活的中國》全書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魯迅的小說”,第二部分是“其他中國作家的小說”。“魯迅的小說”選譯了《藥》《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風箏》《論“他媽的”》《離婚》七篇作品,並有一篇魯迅生平。
第一部分收錄魯迅作品之後,第二部分應當收錄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則成了一個有難度且富有爭議性的問題。為此,斯諾廣泛徵詢了當時眾多文壇人物的意見。除了魯迅、林語堂,還有茅盾、鄭振鐸、顧頡剛、巴金、沈從文等。雖然如此,斯諾也很堅持自己的原則和評判標準。蕭乾曾寫道:“他不要文字漂亮的——當時《現代》雜誌上頗登了一些描寫大都會生活的‘流線型’作品,他一概不感興趣;文字粗糙點沒關係,他要的是那些揭露性的,譴責性的,描述中國社會現實的作品。”
按照斯諾的標準,第二部分的選文歷經多次調整,最後選擇了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茅盾的《自殺》《泥濘》、丁玲的《水》《訊息》、巴金的《狗》、沈從文的《柏子》、孫席珍的《阿娥》、田軍的《在“大連號”輪船上》《第三支槍》、林語堂的《狗肉將軍》、蕭乾的《皈依》、郁達夫的《紫藤與蔦蘿》、張天翼的《移行》、郭沫若的《十字架》、失名的《一部遺失了的日記片段》、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線》共14位作家的17篇作品。因為斯諾揭露、批判的標準,在這個陣容當中,左翼文學佔去了大多數。此外,斯諾還請楊剛和蕭乾各提供了一篇“命題作文”。楊剛出身豪門,毅然與過去的身份和階級決裂,走上革命道路,斯諾認為她是極有代表性的中國新女性,邀請她寫一篇自傳體的小說。楊剛直接用英文寫成兩篇,斯諾選了其中《一部遺失了的日記片段》一篇,應楊剛的要求,以“失名”的筆名收入《活的中國》。而蕭乾,則是翻譯了他寫所謂“救世軍”在北京貧民窟收買靈魂的《皈依》一篇。蕭乾原本覺得自己資格不夠入選,多有推託,但斯諾表示,他要的不是名家,而是作品的社會內容,他認為這篇作品,批判了當時所謂“西方文明”對中國老百姓的精神荼毒。
在《活的中國》最後的附錄裡,有一篇署名為“尼姆·威爾士”的文章,題為《現代中國文學運動》,實際作者即為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為了撰寫這篇文章,她採訪了包括魯迅在內的眾多作家,用翔實豐富的材料廓出中國新文學發展的簡要脈絡,和選集中所收的作品互為觀照。雖然,因為對中國新文學瞭解不夠深入,其中的不少觀點存在可商榷和有爭議之處,但是,對於幫助西方讀者更好、更深入地讀懂《活的中國》中的作品,瞭解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大致樣貌仍然頗有裨益。
“倘若事先能夠充分地估計到編譯這個集子需要嘔多麼大的心血,耗費多麼大的精力的話,我絕不敢這麼‘貿然’進行的”
為了《活的中國》的編輯和出版,在前後五年的時間裡,斯諾花費了大量的心力。他說:“倘若事先能夠充分地估計到編譯這個集子需要嘔多麼大的心血,耗費多麼大的精力的話,我絕不敢這麼‘貿然’進行的。請讀者們相信,我寧願自己寫三本書,也不願再煞費苦心搞這麼一個集子。”
不僅僅在選篇目時三易其稿,對於翻譯工作,斯諾也有著嚴格的要求。斯諾不太懂中文,所以當時採取的方法,是“中西和譯”,即由姚克、蕭乾等中方譯者先從原文粗翻成英文,再由斯諾在英文的基礎上進行修改。與當時普遍流行的追求逐字逐句精準翻譯原文的“直譯”不同,斯諾的翻譯觀是從讀者出發的。他把《活的中國》的假想讀者,設定為對中國一無所知的人。要讓他們讀懂,就要求譯者對原作所描寫的事物有清楚的認知,再用盡可能準確生動、通俗易懂的英語傳達給讀者。特別是一些涉及中國風土人情的內容,因為需要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識,對於不瞭解中國的外國讀者來說,尤為難以理解。斯諾對這部分內容,尤其小心,遇到不懂的,一定要跟中方譯者“刨根問底”,弄個清楚。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還採用了一種在翻譯中不太常用的方法,他把譯者的注加入原文中去,以幫助讀者理解。
此外,斯諾對文字的緊湊性要求很高。他提到了中國短篇小說的一個常見問題——節奏拖沓。他在序言中寫道:“中國作家所得的報酬少得可憐,平均每千字只有三四元(中國幣),很少超過五元。因此,除了最出色的作家,一般都傾向於儘量把作品拖長。他們往往夾進一些辭藻漂亮但是與情節無關的對話或敘述。這樣,為了應付糧店老闆就犧牲了作品的興味、連貫性、風格的統一和形式的緊湊。”斯諾認為,對於習慣了說書傳統的中國讀者來說,這種無關主旨的渲染鋪陳不算太大的問題,但是對於習慣閱讀短篇小說的西方讀者而言,容易引起他們的反感,因此,他進行了許多大刀闊斧的刪減。斯諾的這種“文字經濟學”,對後來蕭乾的翻譯風格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看到了一個被鞭笞著的民族的傷痕血跡,但也看到這個民族倔強高貴的靈魂”
作為最早向英語世界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的選集,《活的中國》一經出版,便受到了中外媒體的關注。《時代》《密勒氏評論報》《太平洋事務》《中國評論週報》等中外媒體紛紛刊發書評。《時代》雜誌稱“《活的中國》讓西方讀者認識了許多陌生的中國作家,如魯迅、茅盾、丁玲以及柔石等”。《太平洋事務》認為,該選集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國社會檔案”。而後,《活的中國》經歷了多次再版和轉譯,不僅在普通讀者中傳播,還成為學習中國語言和中國文學的教材。20世紀40年代,美國國民議會國際關係委員會就曾推薦《活的中國》作為高中課堂教學使用。
翻譯家王際真曾經描述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他們認識中國主要是透過電影和偵探小說,中國就意味著陳查理(Charlie Chan)和傅滿洲(Fu Manchu)以及其他面目模糊卻相當熟悉的人物,也意味著中國炒菜和唐人街商店店面上印刷的毫無意義的象形文字。”斯諾想透過《活的中國》展現給西方的,恰恰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他要“讓歐美人從文藝作品中看見真實的、在急劇變化的中國,別再懵懵懂懂地以為中國人還拖著辮子,中國女人還裹著小腳,中國的統治者還是滿清的皇帝”。
在《活的中國》中,斯諾透過有意識的篇目選擇,塑造了立體的、有層次的現代中國形象。它是苦難深重的:既有封建軍閥、地主階級的“內憂”(魯迅《祝福》等),又有日本侵略、西方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的“外患”(沙汀《法律外的航線》等),還有封建思想的麻痺和毒害(魯迅《藥》等);它也是正在覺醒著的,中國民眾正在從麻木、矇昧的狀態走出來,做好反抗的準備(丁玲《水》等);它還是正在紅色革命影響下的,中國共產黨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有著堅定的理想信念,正在成為中國人民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希望(丁玲《訊息》等)。
必須承認的是,《活的中國》並不是完美的。斯諾並非方家,他的選篇、翻譯都帶著強烈的個人色彩,其中許多地方也許並不符合文學研究的專業標準,比如魯迅的《風箏》《論“他媽的”》、林語堂的《狗肉將軍》甚至都不是小說。但是,這無損於它在讓西方瞭解中國、塑造中國形象方面的卓越價值。透過閱讀《活的中國》,西方讀者“可以瞭解到這個居住著五分之一人類的幅員遼闊而奇妙的國家,經過幾千年漫長的歷史程序而達到一個嶄新的文化時期的人們具有怎樣簇新而真實的思想感情。這裡,猶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嶺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國的心臟和頭腦,偶爾甚至能夠窺見它的靈魂”。
對於斯諾自身而言,編譯《活的中國》,是一個對中國的認識更加深入、思想逐步轉變的過程。透過閱讀中國新文學作品,他了解了更廣大地區中國人民的生存狀況;他對中國的理解,從觀察表層的現象,發展到了深入理解中國人民的思想、體會中國人民的感情,“看到了一個被鞭笞著的民族的傷痕血跡,但也看到這個民族倔強高貴的靈魂”。這也激發了斯諾的思考——這樣一個苦難深重的民族,如何能夠走向光明的未來?誰能夠啟迪民眾的思想?誰能夠帶領民眾,推翻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究竟是怎樣的存在?他們能否成為領導中國人民實現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力量?
帶著這些思考,斯諾踏上了陝北之行。在陝北、在蘇區,他最終找到了笞案,把答案寫在了《西行漫記》裡,向全世界澄清和解答了關於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的一系列問題,諸如“中國共產黨人究竟是什麼樣?”“他們的領導人是誰?”“中國的蘇維埃究竟是怎樣的?有沒有得到農民的支援?”“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軍事和政治前景如何?”等等,讓全世界認識了一個真實的中國共產黨。因此,蕭乾說“《活的中國》是《西行漫記》的前奏”。
(作者:劉月悅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