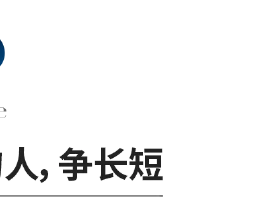我終於成了城裡人,拿早些年的話來說,吃上了商品糧。按理應感到高興才是,可我心裡,除了一絲欣慰,卻難以忘懷——城裡人是那麼的令人鄙視!且說一次我和父親去城裡賣魚吧。
(網路配圖,與本文無關)
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事了。父親養了一大池塘的草魚,眼看有一大筆收入了。一個暑假的大清早,路面還是朦朦朧朧的,父親叫上一個鄰居,加上全家,網兜了四籮筐草魚上來。只見這些魚你一蹦我一跳地掙扎著,勁道可足呢。
“發財了!”鄰居羨慕得不由自主地說,“個頭大,又勻稱,一定能賣個好價錢。”
你還別說,一股遮不住的喜悅早已爬上我的眉梢,父親和母親也暗喜,可嘴上卻說:“就發財了?曉得能賣幾個錢?”
看看這四個籮筐的魚,青青的背脊,白白的肚身帶著泥土黃,條條魚有兩三斤重,最大的怕有四五斤重呢。拿桿秤粗略地秤了一遍,大概一百七八十斤。
稍微分勻了一下四隻籮筐,抬上腳踏車,每輛車貨架邊掛兩隻,用皮條扎牢,再插上秤桿和一大把稻草。
“好了!快去趕個早!”母親和鄰居催我們快出發。於是,我和父親各背上一個挎包,謝過鄰居,跨上車子上路了。
迎著晨曦,揣著幾絲喜悅,我和父親騎在公路上,只聽見輪胎著地的沙沙響,偶爾魚兒蹦幾下,算是打個節奏。一刻鐘後,圩鎮到了,沿路有了三三兩兩的腳踏車同行。再騎二十來分鐘,到了糖廠,路邊的小吃攤前擁著一些廠裡工人來買早飯的,旁邊一些賣蔬菜的攤前人影稀少,顯得略早。
進城的路還剩下了三分之一。這時,有一兩個販子把我們攔下來問價錢,我們也不知道城裡的行情,就按最近聽說的兩塊七八說:“兩塊八一斤”。那販子一副不屑的神態說:“兩塊五好了,我全吊(吊,方言,意為批發)。”接著說:“你這些魚太大了,沒人要的。”這口氣讓人感覺不懷好意,但是我們滿不在乎,沒有受到絲毫打擊,滿懷信心,繼續前行。心想:到城裡面零賣,說不定能賣到三塊一斤呢,這麼大的魚,別人不一定有。
不遠處,又一撥販子把我們攔住,給個吊價兩塊三。我和父親聽了直搖頭。見我們沒有停下來的意思,賊笑著,扔下一句:“到裡面你能賣一半的價錢就不錯了!”
我們繼續朝城裡騎著,父親有點惡恨地說:“這些個刀殺的死販子,好像我們這魚不是養的,是撿來的,一個比一個狠!”我心裡也很不是滋味,似乎被褻瀆侮辱,又像被當頭一棒,寄希望到城裡能賣個公平合理價。
離城還有兩分鐘路時,又迎來一個販子,心平氣和地問一塊八賣不賣。我們根本不予理會,他抬了價格說:“一塊九好了,再高就不可能了。”說完又補充一句:“你們這些魚看上去還不錯的。”
“算了吧,我們還是進城裡去賣吧。”父親說。
“哼——”那人冷冷地笑了一聲。
進到城裡的農貿市場,我們還沒來得及放下來,一大夥人圍攏過來。我和父親心中升起了一線喜悅,卻不免又發毛,這麼多人,我們應付得過來嗎?城裡人,狡猾著!
當我們解下籮筐,擺放停當,環視一圈,發現十大來人,裡一層外一層的,幾乎每人手上都一條魚,有的用中指從魚嘴裡勾穿下巴拎著,也有的自己抽取了幾根稻草拴住下巴,半拎半抱著,摸摸嘴巴,捏捏肚子,觀望著我和父親。——可我們還不知道價格!
“老俵,兆魚兒怎麼點賣?”(兆,城裡話,“這”的意思)
“老師傅,兩塊七好了,我要茲條了。”(茲,城裡話,“這”的意思)
“還說兩塊七?兩塊六啦,你看,喂得這麼飽!”
“等一下,大家等一下,我問一下行情價格來。”
“別問了,就這行情,還怕我們騙你不成?”
……,大家七嘴八舌的。
忙亂之中,我們發現,有人家的魚,斤把左右,喊三塊一賣三塊,於是,父親要價三塊,哪曉得圍著的這些人不肯,沒人付錢,也沒人鬆手,都成了動口的“君子”了。
過了一陣子,有幾個人說價逐漸集中起來:“哎呀,不要糊弄人家種田老俵了,什麼兩塊七兩塊六的,種田老俵養幾條魚也不容易的。這樣吧,我們幾個兩塊八,你老俵也不要叫三塊了,好不好?”
父親心地善,一下子就被他們這話說得軟了,再加上幾個買魚的主動拉著父親的秤就秤開了,等不及父親作決定,也就順著他們開賣了,兩塊八一斤,秤了幾條,我收了錢,三五幾個人拎著魚走了,也有幾個人空手走開。
接下來,圍著的人群少了一圈,剩下的這些人並不急著上前秤魚,卻也不放下魚,有的把魚拎得高高的細細察看,有的一手拎著一條,另一手又在籮筐裡挑來撿去的,有的這裡站站那裡瞧瞧,抓起又放下,……。
“老俵,我要的這條魚稍微小一些,兩塊七,好不好?”一個戴著大大的茶色眼鏡的女子用一種懇切的語氣說。“魚小又不多收你錢,照價格算就是了。”父親與他們辯論開來了。見父親沒有妥協,這個茶色女人沒買,走了,其他一些人跟著放下魚,陸續走散了。
這時我和父親都長喘了一口氣。父親說:“這些城裡佬真是鬼啊,吃虧的總是我們這些種田的老俵啊;不過,這麼零賣,總比吊給剛才路上的販子好。那些販子,價格壓得低,暗地裡還要摳我們多少秤都不曉得。”
我,說白了還是一個小書生,沒有賣過什麼東西,耳朵聽著父親說話,心裡卻感到一絲不安。剛才到底秤了多少魚?我收了多少條魚的錢?父親來之前在家裡就與我約好,由我收錢,他秤魚。因為我是家裡的老大,讀書、幹活都比較自覺,現在讀高中了,早已是附近幾個村子都知曉的一顆讀書種子,父親對我十分信任。剛才的場面已經過去,不管發生什麼情況,都已無法改變,只希望是我的多慮。
看看不遠處的另一個賣魚攤,買的人雖然不多,隔三差五地來一兩個人買,卻總有生意;魚雖小一些,斤把左右一條,價格卻好,三塊不動。我不由得納悶,感到剛才真是傻,人家賣三塊,自己的魚大反而兩塊八,作賤!
“爸,你看,人家的生意做得不緊不慢,魚小,價錢還比我們好。我們是不是賣便宜了?”我沒把握地問父親。
“真是搞不懂這些城裡佬吃什麼!魚大骨刺少,炸起來吃多帶勁。可這些城裡佬不喜歡,偏要吃斤把左右的魚,都是刺。”父親抱怨地說完,又解釋說,“他們這些人要吃新鮮,一餐一條。真是吃個吃靈!”
真是沒辦法,眼巴巴地望著別人穩穩地做生意,自己這邊,問問價錢、挑挑摸摸的人多,買的人少,稀稀拉拉地賣了幾條魚。
趁著不忙,父親招呼著賣,讓我去整個市場轉一轉。一圈走下來,整個農貿市場賣魚的有三五幾家。有一家的魚比我們的魚還大很多,顏色偏深,明顯是深水庫的魚,在那裡切塊賣。其他幾家的魚都比較小,一兩斤左右的。
大約過了半小時,一大撥人擁了上來,又是推推擠擠的一陣。父親忙著秤魚,辯著價,也收錢;我睜大眼睛盯著拎魚的人,緊緊看牢拎走的魚秤了沒有,多少重,應收多少錢,付了錢沒有。可惜我只有兩隻眼啊,根本轉不過來。有幾個人挑好魚,秤好,算好錢,卻不付錢,再次對魚上下打量,有說魚不好的,有換一條再秤的,有說太貴的,嚷嚷兩塊七兩塊六的,說魚已不新鮮了,也有拎著魚站著觀望的。即使付錢,有的人剛把錢交到我手上,即說錢多給了,要回去再數一遍。看著他又數了一遍錢,說沒錯,再遞來,我立即收入挎包,連忙去盯其他那些拎著魚不肯秤重又不願放下的這幫人。手忙腳亂的,好不容易應付過去這一撥。這一陣子裡,很不情願地便宜賣了,兩塊七,也有一兩條賣的兩塊六,拗不過啊。
我和父親心裡清楚,越到後面,魚的活力不好,我們又不像城裡人有水有氧氣泵養著。
“網兜出來的魚,最後不論什麼價格都要賣出去,只有賣出去才是錢,不然,就只有把死魚帶回去自己吃了。”父親怕我不理解,還安慰我一兩句。
我點點頭,覺得他也在安慰自己。
趁稍停下來,我環視周邊一圈,居然在我們站腳邊的草地裡有一條泥黃色的魚,在蹦!我肯定這是我家的魚,忙跨了三兩步去撿回來。這魚力氣這麼大,蹦到一米開外了,這些可惡的城裡佬還胡說八道說不新鮮,亂呱!
現在,魚只剩下一半左右了。魚是賣了近一半,可錢呢,我可不敢在大庭廣眾下數,只好小心看好挎包,換個地方或者回家再數。
稍微空閒些了,我又抽身瞧了一躺市場裡其他賣魚攤。父親讓我去觀察,人家不容易發現是同行。這一次環顧,又有新發現!我看見,他們用腳盆養著的魚中也有我家同樣大小的池塘魚,只是不多,一兩條的,混在他們其他斤把左右大小的青色魚中,顏色、大小反差大,十分顯眼。一個戴著茶色眼鏡的女攤主正想招呼我,我立即轉身離開。回到父親身邊,我把我的新發現輕聲地告訴了他,他淡淡地說,用腳盆養著魚的,肯定是販子,哪個種田的人會帶著腳盆來賣魚?販子只要有錢賺,什麼東西也會販來賣的。
接下來,來買魚的越來越少。父親解釋說城裡人買菜的時間過了。我們便只好見有人來買,就儘量賣出去,價格就稀里嘩啦地一降再降。中午時分,最後幾條魚以一塊五的價賣了,心痛啊,也沒辦法,總算賣完了。父親嘆了一口氣,對我說:“收拾籮筐,出去找個地方買點東西填填肚子。”
我們收拾停當,帶著幾絲興奮,出了市場。來到一個稍偏僻的角落,我們清點了一下戰果。我收到一百六七十塊錢,父親收到一百來塊,加起來總共兩百七八十。
不到三百塊?不會吧?!一共一百七八十斤魚,就平均兩塊一斤,也應該有三百五六塊。我頭腦一嗡,立即愣住了!父親也站立不動,半張著嘴,沒有表情。
“走,我們一邊走,一邊回憶一下,”還是父親先回過神來,推起腳踏車,說:“真是這樣的話,回家吃午飯好了。”我也沒了主意,感覺天都要塌了,喘不過氣來。
“我忙著秤魚,你是不是對有些人沒收到錢,沒看牢,讓他給溜走了?”
“很可能!他們一來一大夥人,弄得我們手忙腳亂的。要不然,魚怎麼沒了?”
“趁我們忙,他們難道有人在往外傳魚?”
“難說!說不定許多魚被傳走了!”
“剛才,你數錢沒數錯?”
“不會數錯,相差大了。數了幾遍。”
“你有沒有把錢放到褲兜裡?還是挎包被人割了,有漏?”
“沒有,包現在完好的。”
“我想啊,有幾個人明明自己先數好錢,給我之後又要回去再數一次,這裡會不會有問題?!”
“他第二次數錢後,你沒再數?”
“沒有再數,看著他數第二遍的。”
“他數第二次的時候,可能抽走了幾張,你沒看到。”
“嗯。誰想到他們有這一招!再說,我也不能光顧著他一個人呀。”
……
“你不是在我們站腳的後邊撿回來一條魚嗎?那條魚會是自己蹦出去的?”
“難怪後來別的賣魚人家腳盆裡有與我們相同的魚哦!怎麼你開始轉去沒有見到?而且數量就那麼少數幾條?”
……
一路上,我和父親你一句我一句地回憶著,可不管怎麼回想,錢還是那麼兩百七八,簡直惡夢一場!早知如此,還不如一開始就一次性吊給販子!——轉念一想,販子除了壓價,就不會摳秤嗎?還真是應驗了那個死販子說的“到裡面你能賣一半的價錢就不錯了”。
種田人啊種田人,你能有什麼辦法呢?
一段時間來,父親陷入沉思,我也內疚著不敢吭聲。我們默默地騎著腳踏車,聽著路面沙沙聲。儘管影子已開始向東偏了,可我和父親都沒有說肚子餓。我自嘆自己根本就是個傻子,讀書再多,也還是被他們這些可惡的城裡人耍得一塌糊塗。
不知過了多久,父親說:“這事可不能讓你媽知道哇!”我應了聲“好”。父親接著說:“不是我們要騙你媽,是告訴她的話,她可能受不了。還有,你弟弟那裡也不能說的。他不懂事,會傳話給你媽的。”
回到家,父親首先開口,向母親訴苦道:“哎呀,今天的魚兒不好賣,城裡的魚真是個多啊!”
“是啊,根本賣不動。”我附和著說。
母親沒再作聲,忙招呼我和父親吃午飯。她知道,父親出外面一貫是趕回家吃飯的,從來不進飯店。(2014年6月18日,約45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