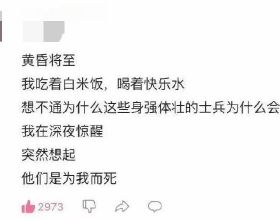01
畢業那年,我24歲,正趕上家裡拆遷。
拆遷款剛到帳,我爸就和大多數上一輩人一樣,有些“飄”。原本,我已經拿到西安一傢俬企的offer,卻被我爸擋住了。
他說私企不穩定,要拿錢給我“辦”一份工作。
我的學校不好,是西安某三流大學,像我這樣的學歷,能安排到哪裡去呢?
大概過了半年左右,我記得是5月份時,有個同村的大(關中方言,指叔),開著他家的桑坦鈉,送我來到了X縣,停到了縣城油庫旁一棟老樓跟前。
這座老樓有些年月了,灰色的外牆牆皮,已經像風乾的樹皮一樣翹起來。大門口懸掛著一個白底黑色的牌子:“X縣城管綜合執法大隊”。
我大從他的黑皮包裡,掏出一張列印好的A4紙給我。是一張入職申請單。
他一邊指點,我一邊填寫,隨後就帶上畢業證和戶口本,敲開了城管大隊辦公室的門。聽我大說,我一個人進去就行。
接待我的男人是個禿頂,他一臉意味深長地上下掃了我兩眼,然後把我帶去了三樓大隊長的辦公室。
初次見面,大隊長還是帶著些警惕心的。
他先讓我把辦公室門閉上,然後嚴肅地看著材料。
我趕緊按照我大教我的,提了中間人的名字,說是他介紹來的。這時大隊長才表情鬆弛下來,點了一根菸對我說:
妹子,歡迎你加入我們,你直接去一樓督察隊,找X隊長報道就行。
原以為驗完資料,下一步還會安排筆試、面試、心理測試等流程,萬萬沒想到,當我把資料遞給X隊長後,他直接就給我安排工作,說我的工作是內勤,平常主要負責更新臺賬、報資料、寫督辦等,並安排一個年輕男同事帶我。
對於這種錄用方式,我有點懵圈,又不敢當面問。後來,趁著保潔大姐幫我收拾辦公桌的間隙,我跑到衛生間給我大打了個電話。
面對我的疑惑,他輕描淡寫地回了一句:
安心上班,其他事都安排好了。
X隊長把我交代給那個男同事之後,人就不見了。
這個男同事看起來文質彬彬,寡言少語,他拿起桌上一沓資料放到我面前,讓我先熟悉,然後就自顧在電腦跟前敲鍵盤了。我這時候偷偷瞥了一眼,這個約30平米的辦公室,佈置了6個座位,其中離我最近的那個,桌面上已經滿滿落了一層灰。
第一天,就這樣摸魚到下午快5點左右,男同事背上挎包,說下班走了。這個時候,我才注意到他穿了一件鬆鬆垮垮的老年背心。他略顯滄桑的背姿,倒是和這件背心很搭。
後來我才得知,這個男娃也是被家人“安排”到這裡上班的。本來單位提供住宿,但男娃每天都要坐班車回西安,因為他女朋友在城裡。
當晚,一個大姐帶我住進了單位宿舍。我躺在床上給家裡人說了情況,父親在電話裡很興奮,他對我能被安排到這種正式單位很滿意,還說擇日要在村裡擺酒席云云……
然而幾天後,我就瞭解到一個扎心的真相:
我被安排的,是勞務派遣形式的臨時工。
怕老父親傷心,我沒告訴他。
02
第二天,我早早來到辦公室,先裡外打掃了一下衛生,然後拿起抹布給大家擦桌子,給每個同事接熱水。
快9點的時候,一個留著光頭走路有點羅圈腿的大哥先來到辦公室。他用陳年老煙嗓混合著地道的當地話和我打招呼,然後哥長哥短的讓我別忙活了。
過了半個小時左右,同事們陸續到齊,包括那個桌面有一層灰的位子,原來也是有人的。光頭大哥趁勢熱情地向大家介紹我,這時我才發現對我的背景情況瞭如指掌。
過了會兒,X隊長推門進來,朝辦公室裡瞥了一眼,順手丟給我一件城管制服。
三五分鐘後,X隊長讓光頭大哥開著執法車,帶我們科室的人出去巡察,同時也讓我跟上出去“熟練熟練”。
我有點怯場,就自覺坐到了巡查車最後面。結果X隊長把自己副駕駛的位置讓出來,非要我坐前面。路上,X隊長給我介紹科室其他人的姓名、職務,我才知道,光頭大哥就是我們科室的老大。
第一天上班的巡查沒什麼實質性工作,就是街頭巷尾開車閒轉。碰見有胡亂擺攤的,用擴音器驅趕一下。
很快到了飯店,光頭大哥把車停到一個麵館門口,請大家在裡面吃了碗軟面。臨走的時候,老闆硬給我們每個人塞了一瓶冰紅茶。我不好意思,推辭不要。光頭大哥給我遞了個眼色,我就收下了。
城管是不是像新聞裡那樣都是凶神惡煞?說實話,之前我對這個職業印象也不好。但隨著巡查多了,我發現這個世界並不是非黑即白的,很多事,很多人都不是標籤化的,很難一句話說清。
比如有些攤販也很蠻橫無理,和管理人員打游擊,導致工作很難奏效,我們經常受訓捱罵。就比如我們負責的片區,明明劃分了指定擺攤的區域,但有些攤販就是佔道經營,好好說不聽。
更有甚者,有些攤販是當地的地痞無賴,面對勸導不僅不配合,而且動輒便舞刀弄槍要跟我們同事動手。還有攤販經常給你下跪裝可憐,抱大腿哭天喊地,要麼直接躺在地上打滾……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有個賣瓜果的婦女因為佔道經營被我們的同事收了秤砣,她就帶著年幼兒子來大隊鬧事,剛開始工作人員對她好言相勸,但她不僅不承認錯誤,還對工作人員出口成髒。
最後,這女人不知為何突然情緒失控,竟然脫了褲子,當眾在我們的服務大廳撒了一泡尿。
我目睹這一幕,簡直三觀盡毀。據我所知,在我們大廳工作的同事,很多都是正式編制考進來的大學生,也不知道他們看到這樣的場面,會作何感想。
在這種情況下,粗暴執法也時而出現,我曾看到同事驅趕攤販,滿嘴髒話,有時還簡單粗暴收繳物品。大家似乎沒有好的辦法,“震懾”違規攤販下不為例。
實際上,下罰單也往往是形式,只要攤販來大隊承認錯誤,往往我們也是口頭教育為主,不會實質性罰款,畢竟執法物件多是底層老百姓。
後來我想,市容頑疾背後的複雜現實,可能單靠城管工作無法化解,這大概是一些城管隊員在壓力下失控,而一些攤販行為也每每讓人跌碎眼鏡的原因所在。
比如這個縣城南街曾是當地紅燈區,經常有站街女出沒。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有次執法過程中,抓到一位40多歲女子,南方口音,渾身胭脂水粉。
按照流程,這種情況我們要轉交公安機關處理。
但是這個女人當場就跪下了,眼淚嘩嘩說自己有多可憐。她自述出門從事這個行當,全是為了供老家孩子上學,還把手機裡孩子的照片包括各種獎狀給我們看。
最後,我們動了惻隱之心,口頭警告之後,讓她寫了保證書按了手印,把人放走了。
沒過多久,我們又在那條街看到了這個女人的身影……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她講述的是不是真相;如果是真相,這種問題又該怎麼解決。
03
入職到城管大隊大概兩星期左右,我就逐漸適應了節奏。
我們科室基本上全是不帶編制的臨時工,包括那個光頭大哥也是退伍轉業過來。
臨聘人員薪酬很低。那是2016年,我們每個月1700-2000元就封頂了。
在這裡,有些人是圖個清閒,有些人是圖離家近,而我單純是為了給父親“臉上增光”,因此薪酬與我們而言,反倒覺得很無謂了。
但讓我不能理解的是,我發現單位裡,還有一些家庭和出身都很不錯的男青年,明明會有更好的前程,但他們卻也屈身這裡,願意做一名沒有靈魂的小城管。
後來光頭大哥給我指點迷津,這些娃們家把工作只是當渠道,核心目的是透過這個工作,打通社會各路人脈,擴充交際圈,來維護背後的“事業”。
就比如說,我們的X隊長,是個愛好熱鬧的人,平常下班沒事時,他就讓光頭哥去“安排”飯局,然後私下通知我們聚一聚。我們每次吃飯的地方都不固定,但是每次招待流程都大同小異,這些飯店老闆會提前預留好包間,桌上擺上酒水、各種特色菜。我其實很佩服這些久經世事的生意人,每次被人白吃還賠笑敬酒。
還有個男同事,每次單位夜班排班都有他,我開始還覺得意外,後來才知道他親戚在當地經營渣土車車隊,他夜間值班有很多事情要忙,至於中間具體有什麼內情我不好過問。肉眼可見的是:他上班才兩年不到,開的車從F3換成CRV,最後換成了一輛A6。
諸如此類的事情還有一些,限於篇幅和隱私,就不一一表述了。
當然,也有人不是這種“多面人設”。
我們大隊有個X縣本地人,就是厚道人之一。我記得有一年臘月29才發的工資,我和他兩個人在辦公室值班。當他看到工資到賬的簡訊,就倚在辦公室牆角唸叨說:一會去割5斤肉,再去勞保店給我老爸老媽一人買一件棉大衣,一條棉褲,再給娃買一雙紅皮鞋,娃跟我要了很久了,這下爸可以滿足娃了。剩下的錢,我還要買幾個紅包,給親戚娃還要發壓歲錢......
看著這位大哥臉上的滿足表情,我背過身子,眼淚落了下來。
好景不長,因為該縣撤縣設區,我們的大隊編制也被打亂,曾經的管轄區域和組織隊伍全部要重構,我們的督察隊也迎來了被解散的命運。我因為沒有關係和背景,被分配到了“活難幹,事最多”的街道中隊。
新科室的領導,也是部隊轉業人員,是長安區人,個頭很高,梳個大背頭,許是同鄉的關係,他對我尤其照顧。
但新領導在工作上卻很嚴厲。比如說,當時他帶著我們去街頭拆除違建和廣告牌,每項工作幹完後,他都安排我做好宣傳。在他的高壓“鞭策”下,我這個曾經特別排斥寫作的人,開始學著撰寫新聞稿,編輯美篇等等。在那個西安各個區縣“打擂臺賽”的時期,我的多條美篇稿獲得縣委、市委領導的關注。
說句實在話,那段時間雖然工作壓力劇增,但是與此前無所事事的遊蕩和吃喝玩樂相比,我更喜歡這種因為忙碌和壓迫帶來的獲得感、充實感。此後,我又相繼學會了寫紅標頭檔案、回覆督辦、對野廣告使用“呼死你”系統等等很多技能,這些都可以算作我的人生財富吧!
兩年之後,因為個人感情變故,我瞞著父親向單位提出辭職。
我還記得當我第一次把辭職信交給大隊長的時候,他很斷然地拒絕了我,說了很多勸勉的話。然而第二次我再提的時候,知道我心意已決,大隊長就二話不說在我的離職申請表上籤了字,蓋了章。而後,我給大隊交還了制服、徽章。
正式離開城管大隊的那天,很多老同事都來送行。大隊長還開著自己的私家車,一路把我送到汽車站。臨上車的時候,他對我說:以後在西安有啥事就給哥說,不要受欺負!
聽了這話,我咬牙憋回自己的眼淚,然後扭頭上了班車。我想我所經歷的,不只是穿過了一身制服,而是看到那制服下面,依然是與這社會其他行業無二的,一個個真實的鮮活的人。他們都是這紛雜人世的,一面鏡子。
文章來源:秦鑑,作者:拾落,圖片來源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