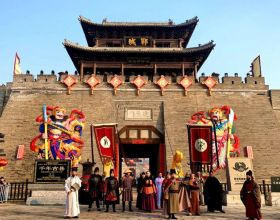白秀英為什麼要從繁華的東京汴梁,來到偏遠的窮鄉僻壤——鄆城縣“賣唱”?這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白秀英與父親白玉喬反其道而行之,從京城來到鄆城,實際上是追隨新任鄆城知縣時文彬而來,她與知縣是姘居關係,也就是縣令的二奶或者說是小三。當然,外人知道這個內幕的不多,畢竟她父女倆來到鄆城縣沒幾天,眾人對他們父女倆還不太熟悉。
說書藝人想多賺錢、求發展,都是奔向大城市、經濟發達地區,比如而今的京上廣深,唱歌的、學表演的、搞文化藝術的都從四面八方向大城市雲集,很少有人從北京到一個普通的縣城來發展,除非個別特殊情況。但是,又有幾個人來分辨這些事呢?又有誰能看清這背後隱藏的不為人知的秘密呢?
說實話,白秀英雖然有知縣撐腰,但她還是很懂江湖規矩的,畢竟是在“道”上混的,成天跑碼頭吃江湖飯的,焉能不懂這個最基本的道理。所以,白秀英一到鄆城地面,就去縣衙分別拜會了本縣知名的、有頭有臉的人物,這其中當然包括步軍都頭雷橫,但不巧的是,雷橫當時出差未歸,所以他不認識白秀英,這為後來的衝突埋下了第一個伏筆。
雷橫第二個不應該的地方是,他看戲(實際上是聽書)不帶錢,究其原因是他驕橫慣了,沒有出門帶錢的習慣。雷橫是鄆城縣緝捕都頭,出門辦事算是公差不假,但也不應該分文不帶。這隻能說明,雷橫優越感太強,長期免費吃喝慣了,出門從不帶錢。你看他執行公務,在破廟裡看到吃醉酒的劉唐長相醜陋,就懷疑他不是好人,趁其醉酒將劉唐綁起來吊打,然後卻並不急著回去交差,反而去東溪村晁保正(晁蓋)家裡混吃混喝。晁蓋是村長,見到雷橫到來是畢恭畢敬,不僅酒肉管夠,臨行還贈送10兩銀子。由此可見,這些事情雷橫平時可沒少幹,到哪裡都是免費吃喝,臨走還有錢物相送,真是又吃又喝又拿。
雷橫犯的第三個錯誤是,他在街頭巡邏,按說也是在工作時間內,卻聽到李小二說有個新來的唱戲人,才貌雙全,又是從京城下來的,不僅戲唱得好,容貌也是萬里挑一。雷橫一聽,兩眼放光。於是,邏也不巡了,將手下幾名士兵遣散,他則直接跟著李小二來到勾欄,要親眼看看這個新來的戲子。來也就罷了,可以找個偏僻的角落,坐下來仔細看、認真聽,卻不該一屁股坐在最顯赫的位置——前排正中。這個位置可不是普通人隨便就能坐的,含義不言而喻。
好戲開場,白玉喬先致開場白:“各位看官,老漢乃東京人氏,名叫白玉喬,現已年邁,只有女兒白秀英,歌舞吹彈,混個溫飽。我父母倆普天下行走,服侍各位看官了!”在眾人的一片叫好聲中,白秀英出場,她圍場轉了一圈,道了幾個萬福,開口就是例行開篇引子:“新鳥啾啾舊鳥歸,老羊羸瘦小羊肥。人生衣食真難事,不及鴛鴦處處飛。”胡琴聲想起,白秀英開口便唱。聲如珍珠灑落,委婉動聽,全場一片歡呼。
白秀英唱的是兩宋、蒙元時期很流行的宮調,是一種又說又唱、說唱結合的曲藝形式。其實,白秀英是個全面型人才,不但能說會唱,還精通歌舞表演,算是個多面手,否則知縣大人也不可能看上她。白秀英當天唱的曲目叫《豫章城雙漸趕蘇卿》,這是宋代浙江杭州說唱藝人張五牛和山東曹州雜劇名家商正叔所創作的,講述的是一個悽美的愛情故事(看來愛情是個久遠的、永恆的話題),跟《杜十娘》、《賣油郎獨佔花魁》的情節差不多。蘇卿,即蘇小卿,廬州(今合肥)唱妓。雙漸,乃一個窮書生,二人偶然的機會相識,私定終身,蘇小卿遵守承諾不再接客,而雙漸也發奮讀書,後來高中進士,被派往臨川為官。雙漸久不來接蘇小卿,老鴇將其賣給了茶商馮魁。馮魁帶蘇小卿回鄉,途徑金山寺,蘇小卿在牆壁上題詩,用來提醒雙漸。後來雙漸苦尋蘇小卿,偶然間也來到金山寺,看到了牆壁上蘇小卿所寫的詩,便火速感到豫章城,找到了蘇小卿,最終有情人終成眷屬。
白秀英唱罷一段,按慣例討要賞錢,這是走江湖的藝人獲得收入的渠道,雖沒有明文規定,但卻是約定俗成。前來聽戲的客人,哪有不帶錢的,即便是有,也是極少數。俗語講:掙君子錢,受小人氣。走江湖的藝人,吃的是百家飯,掙的是君子錢,受的是小人氣。白秀英討要賞錢,是其父女倆賴以生存下去的根本,是合理合法規的,也是大家都認可的,這沒有錯。白秀英唱到緊要處,被父親打斷,白玉喬打了諾,對著臺下說道:“雖無買馬博金藝,要動聰慧鑑事人。看官喝個彩就過去了,我兒且下來,向客人討個彩頭。”白秀英於是端起盤子,邊走下臺邊道:“財門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過,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過。”白玉喬道:“我兒且走一遭,看官們都等著賞你呢!”白家父女倆行走江湖,又是在京城混過的,自然是行家裡手,白玉喬的話裡話外,都帶有強烈的暗示,那就是:給錢的都是聰明懂事的!反過來的意思就是,不給錢的就是愚笨不懂事理的。這些話說出來,當盤子端到你面前,你如何好意思不給錢呢?再說了,來看戲哪有不賞錢的?古代不興賣票,藝人的收入就是靠打賞,這些道理是老祖宗留下來的規律,看官們哪有不懂的道理。
但今天卻恰恰有個“不想”打賞的客人,誰?就是插翅虎雷橫!其實,客觀公正地講,雷橫當時確實是身無分文,不管他是忘了帶,或者是從來不帶,亦或者是吃霸王餐吃油嘴了,從來都不需要帶錢,再或者像他本人解釋的那樣——所帶錢不多,剛才在街頭買了點東西,現已身無分文,不論哪個理由,反正身上是掏不出一文錢!這點要替雷都頭分辨一下,絕不是白秀英所認為是那樣,想聽霸王戲,不想掏錢。試想在那種場合,在眾目睽睽之下,就算是再無賴,也沒有不掏錢之理呀!面子上也過不去啊!再說了,現場還有不少人認識他,都叫他雷都頭,這臉皮往哪擱呢!
所以,雷橫站了起來,摸遍了全身,掏不出一文錢來。他紅著臉,對白秀英說:“今日身上確實帶錢不多,剛才買了些許東西,現在沒有分文,待明日一併賞你。你看如何?”此時的白秀英,臉上依然帶著微笑,她說:“官人,頭醋不釅二醋薄。既然官人今天坐在首位,自然是要帶頭出了標首啊!”雷橫急了,說:“並不是我捨不得銀子,只是今天一時忘了……忘了帶錢出來。”白秀英道:“官人既然是來聽曲取樂的,怎麼能夠忘了帶錢出來?分明,分明是官人在推搪。”雷橫搓著雙手,說:“這樣,明天我再來,賞你個三五兩銀子不打緊。可恨的是,今天身上真、真沒錢。”雷橫說罷扭頭就走,他也無法再待在現場。白秀英見雷橫要走,忙喊道:“哎,官人,今日尚且一文都沒有,還提什麼三五兩銀子,你在這推三搪四的,不是叫俺們望梅止渴、畫餅充飢嗎?”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如果雙方就此打住,都各自退讓一步,就不會有下面的風波了,白秀英不會丟了性命,白玉喬也不會被雷橫一頓暴打,牙齒被打落,口鼻流血。走了,走了,一走百了,雷橫就算是受了蔑視和恥笑,也是他有錯在先,嚥下這一口惡氣再說。
但此時此刻,臺上的白玉喬見女兒第一炮就啞火,沒有要到錢,開口便道:“閨女,都怪你自己不長眼,也不瞧瞧他是城裡人、鄉下人,你說你向他討個什麼錢,快去找幾個曉事明理的恩客,讓人家出個標首。”雷橫本來打算走了,聽到此話,怒火上來,回頭責問道:“我怎麼不曉事、不明理了?”白玉喬道:“你要是曉得這子弟門庭的規矩,恐怕狗頭上就要長角了!”雷橫聞言大怒,道:“你這個老東西,你竟敢罵我?”白玉喬道:“便罵你這個三家村使牛的,打什麼緊,罵你怎麼了?”這時臺下有人道:“這是本縣雷都頭,使不得,使不得。”白玉喬如果此時再剎住車,也還來得及,但他依然是口出惡言,道:“什麼都頭,簡直就是個牛筋頭。就罵你怎麼了?”雷橫此刻再也無法忍受,他掙脫大家的拉扯,一個箭步跳上臺,左手抓住白玉喬,右拳一個直勾,將白玉喬打落於臺下。
白玉喬滿嘴是血,牙齒掉了2顆,白秀英趕緊跑過去,扶起父親,哭喊著說:“爹,爹,你怎麼樣了?你沒事吧?”雷橫跳下臺,指著白玉喬大聲道:“今天看在眾位街坊鄰居的面子上,就先饒了你這一回,回家先把你的破嘴縫上。”白玉喬微微諾諾,好漢不吃眼前虧,他牙齒漏風,含糊不清地說:“是,是,回家縫上。”雷橫說罷,扭頭就走,李小二跟在身後緊追。(未完待續)